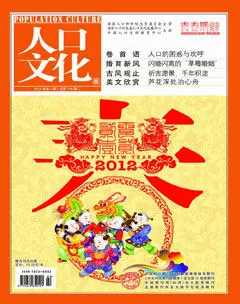蘆花深處泊心舟
梁惠娣
慢慢地走向蘆花深處,仿佛是走進了白色的海洋,走進了詩般的迷離,走進了夢般的幻境。連那一輪圓圓的旭日,也變得暗淡失色了。
清晨,在山野間閑走,一不小心,誤入了蘆花深處。
蘆葦在煙雨朦朧的南方,是常見的植物。此時,正是勁風游走的季節,風過處,留下瑟瑟的寒意。
此時的田野,野草一身枯色,像是隱士,稻子,正是成熟飽滿的金色年華,勞苦功高的模樣,山上的樹木,不肯褪下隔年的舊衣,一身老氣橫秋的蒼綠,那些叫不出名的野花,像掙扎在社會底層的人,毫不起眼,精明的蔓,攀附著一切,展示著自己高超的交際藝術……唯有蘆葦,妙齡女子一般,婷婷裊裊地走出來,渾身散發著勾魂攝魄的美。
展目野外,田埂上,河溝邊,山腳下……隨處可見蘆葦的身影。此時的蘆葦,蘆葉黃了,蘆花白了。大片大片潔白的蘆花,一團團一簇簇的,像花絮,像飛雪,也像輕盈的羽毛風一吹,它們便朝著一個方向曼妙地搖曳仿佛一群舞姬在舞蹈,婀娜多姿,風情搖落。那是最優雅的舞蹈。
慢慢地走向蘆花深處,仿佛是走進了白色的海洋,走進了詩般的迷離,走進了夢般的幻境。連那一輪圓圓的旭日,也變得暗淡失色了。
《詩經·蒹葭》里的千古名句:“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就是蘆葦。那河岸邊蒼蒼萋萋的蘆葦,大概是離愛情最近的草了。他“道阻且長”地追尋她,而她,總是“在水一方”。那是最最糾結的愛情了。
那遍野的蘆花喚醒了我久遠的童年記憶。小時候,喜歡蘆葦,喜歡舉著它雪白的花束在風里跑,笑聲跟花絮一起飄得很遠很遠,摘了蘆葉,放到嘴邊可以吹出“吱吱啾啾”的哨聲:也會拿了小刀到蘆葦叢中,削一截蘆桿,做成蘆哨,放在嘴上一吹,“嘟嘟嘟”的哨音清脆悠揚,也有農人挖了蘆根,曬干了,那是一味難得的中藥:古代窮人還用蘆花代棉絮做過冬的衣服,人稱蘆衣。《太平御覽》和《孝子傳》里,有一個故事:“閔子騫幼時為后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父后知之,欲出后母。子騫跪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遂止。”古代“蘆衣”曾是“孝子”的標志。
一株芊芊蘆葦,一束揚絮蘆花曾如何地醉倒了那些善感的文人騷客,搖曳進他們的清麗詩行里。讀蘆花詩,讀出了一點興味來。詩人寫蘆花,總會與漁人扯在一起,如:宋人司空曙賦詩曰:“釣罷歸來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梅妻鶴子”的林逋說“最愛蘆花經雨后,一篷煙火飯漁船。”宋人趙訥軒也有:“白鳥一雙簾外去,蘆花風靜釣舟閑。”朱繼芳有句:“漁翁家在何許,慣宿蘆花不歸。”明代袁宏道也說:“釣竿拂曉霜,衣薄蘆花絮。”清代邑人鄭蘭枝也有:“芳塘如鑒正清兮,漁筏隨風看不迷。幾朵蘆花浮水凈,半竿山曰落湖低。”蘆花中傳出的笛聲也是異常悠揚動聽的,如宋人董嗣果《聞笛》“船上何人笛,吹入蘆花林。”笛聲依約蘆花里,白鳥成行忽驚起。是潘閬所作:清人納蘭性德也作:“人淡淡,水蒙蒙,吹入蘆花短笛中。”一株蘆花,竟引發了詩意無限。
蘆花也是充滿畫意的。清代著名畫家邊壽民,是“揚州八怪”之一,號“葦間居士”,晚年他回鄉定居,結廬于城東粱陂橋畔的蘆蕩里,名居所為“葦間書屋”。據考,他的廬舍就是用蘆葦搭建而成的,可見他對蘆葦非同一般的喜愛。他不僅住蘆屋,更以善畫蘆雁而名聞海內。他的蘆雁圖,成為后人爭相收藏的墨寶。他畫的鴻雁惟妙惟肖,呈現出翱翔、盤旋、嗚叫、顧盼、戲水等各種姿態,置于水云蘆荻之中,顯露出清逸,恬淡的意象。他給自己的蘆雁圖作題畫詩《秋葦蘆雁圖》:“瑟瑟黃蘆響,嘹嘹白雁鳴。老夫住葦屋,對景寫秋聲。”鄭板橋用詩評價他的畫云:“畫雁分明見雁鳴,縑緗颯颯荻蘆聲。筆頭何恨秋風冷,盡是關山離別情。”
到了現代,著名畫家林風眠更將蘆雁畫出了自己的風格。其一幅《蘆雁圖》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畫中蘆葦向右搖蕩盧雁則向左疾飛,空中更有烏云逼至,整個畫面給人以生命的詠嘆感與心靈的震懾感。
傍晚,再到山野間漫步,依然是不自覺地走進了蘆花深處。想起南唐后主李煜的《望江南》里有句:“蘆花深處泊孤舟。”一個“孤”字,總歸是蒼涼了些。而我,愿意將心化為一葉小舟,隨著風,蕩到蘆花的海洋里,然后,靜靜地停泊下來,那樣,是“蘆花深處泊心舟”了。
(編輯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