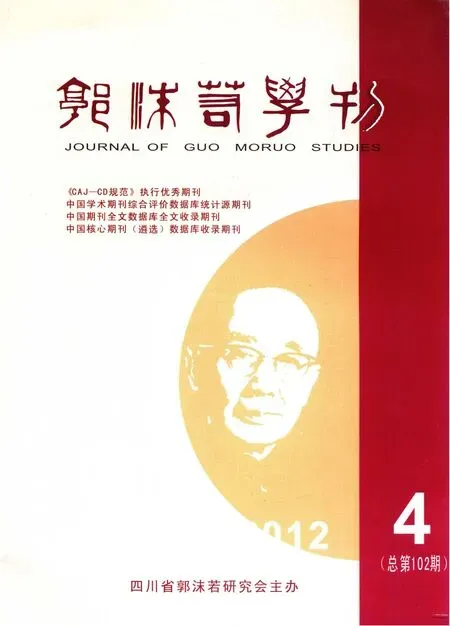郭沫若三首題畫詩
李 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 郭沫若紀念館,北京 100009)
郭沫若在美術鑒賞方面造詣很深,已為論者多次提及。“他雖然不是畫家,但是他懂畫、愛畫甚至還會繪畫,他在這方面有深湛的藝術修養”[1];“作為作家、詩人、學者而兼書法家的郭沫若,對中國傳統繪畫有著精辟獨到的鑒賞力。”[2]他跟齊白石、傅抱石、李可染、關良等美術大師都有親密的交往,寫了不少題畫詩,“頗多佳篇,甚具特色”[3]。這次我們發現的《金剛橋畔》《豐年圖》《題道綱先生畫》等三首題畫詩,《郭沫若全集》《郭沫若題畫詩存》等未收,相關研究資料未提,屬學界尚不知道的郭沫若佚詩。
一
1943年《經緯月刊》第1期刊出了郭沫若的《金剛橋畔及其他》,照錄原文如下:
金剛橋畔及其他
金剛橋畔
文元同志畫歌樂山下金剛橋畔之實境,足徵抗建中民眾生活
——作者志
一道蜿蜒破天險,
復興國難見民勞。
山川到處增顏色,
莫道英雄始是豪。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渝
豐年圖
——文元同志畫此農家風物索題
——作者志
農村生活原邦本,
人民勞止竹森森;
盡他寂寞無相問,
幸爾春牛共一岑。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文元,即張文元。金通達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國當代國畫家辭典》第276頁介紹他說:“張文元,男,漢族,1910年生于江蘇太倉。幼年家貧,自幼繪畫,當過油漆畫匠、小學美術教師、報社編輯等。1935年起在上海《時代漫畫》《論語》等刊物上發表作品。1936年《大觀園》等作品參加‘第一屆全國漫畫展覽’,1937年與沈逸千等在上海舉辦‘抗敵畫展’,同年在武漢參加馮玉祥主辦的《抗戰畫刊》的編繪工作。1943年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第一次個人國畫展覽,1945年3月參加葉淺予組織的‘漫畫八人聯展’,同年底返滬,任全國漫畫家協會理事,并舉辦‘川滇風物與漫畫’個人展覽。1949年從香港至北京參加第一次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回滬后任職于新聞日報社,任上海市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并與米谷等創辦《漫畫月刊》。1957年后任寧夏日報社美術編輯。1979年任寧夏美術家協會副主席。1980年秋調到上海解放日報社工作,1986年退休。擅漫畫、國畫。所作國畫,以山水為主,多寫西北地區山川風貌,筆墨厚實,色調濃重,常作潑墨。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張文元1943年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第一次個人國畫展覽展出六十余幅作品。郭沫若參觀了這次展覽。《金剛橋畔》與《豐年圖》大概即為這次展覽所題。《金剛橋畔》的“作者志”說:“文元同志畫歌樂山下金剛橋畔之實境,足徵抗建中民眾生活”。描寫“實景”是張文元國畫的一個突出特點。觀看展覽的蘭石說,這些國畫中大部分以四川風物為背景,表現“抗戰后方動態”。比如《嘉陵江之秋》、《街頭小景》等,將“汽車輪船兵士店鋪一向搬不上宣紙的畫材都搬了上去”[4]。馮玉祥也參觀了這次展覽,他對其中一幅畫有比較詳細的描述:“兩紅球,高懸起/看情形,已緊急/老和少,男和女/肩挑擔,手提包/滑桿和轎子/走的有秩序/救護隊/如山立/紅十字軍預備齊/擔架放在地/護士們為人謀福利/甘愿犧牲她自己/最苦的是婦女們/右手抱兒,左手攜女/還要提東西/倭寇最可恨/必須快快打出去”[5]。紅十字軍、護士在中國是進入現代社會后出現的,紅球高懸是抗戰時期的空襲警報。中國傳統國畫絕不會表現上述題材。張文元將其繪入畫卷,體現了他善于描繪抗戰實景,敢于創新的藝術勇氣。
郭沫若對于用國畫表現抗戰實景的創新精神頗為贊賞。在《金剛橋畔》與《豐年圖》中,他用白描的手法將畫面內容勾勒出來。尤其是“山川到處增顏色”、“春牛共一岑”等,充滿了田園風趣和樂觀精神。抗日戰爭在1943年已經進入了最為艱難的時期,長期抗戰使得民生日用極為匱乏,廣大人民掙扎在饑餓與死亡的邊緣。張文元的國畫,郭沫若的題詩都充滿了太平景象,這不是畫餅充饑,而體現了藝術家和詩人堅忍淡定的風度。從中大概也可見出中國人民為什么能夠在殘酷戰爭中堅持下來之一斑吧。
二
1943年5月28日重慶《時事新報》第4版,刊出了郭沫若的一首七言題畫詩,名為《題道綱先生畫》。茲錄全詩如下:①
人間逸處即仙家,
桃李枝頭正著花。
鹿鶴人間隨處有,
仙人何□緲云霞。
我們查閱各種辭書,名為“道綱”的畫家僅有張大千的弟子翟道綱。我們推測,翟道綱就是《題道綱先生畫》中的道綱。
筆者所見翟道綱的畫有兩幅,一為《青綠山水》局部,一為《翟道綱畫仙洞隱居圖》。前者選入汪毅編著、四川美術出版社2008年版《張大千的世界 大風堂的世界》。此畫前景為泛著微瀾的湖水,設灰白色;中景為青綠山,左邊的樹開白花,中間有青松;青山向左后方與右后方延伸;在畫面右后方的青山環抱中有一方銀黃色的地面,立有三位仙人與一只仙鶴。落款為:“仿劉松年設色道綱翟浩繪”。劉松年為南宋畫家,設色典雅,擅畫帶有茂林修竹的西湖勝景。《翟道綱畫仙洞隱居圖》為泰和嘉成(北京)2011年春季藝術品拍賣會瑯嬛墨緣——蜀中徐氏舊藏專場以人民幣58240元拍出。該畫正中,在松柏及小灌木的環繞下,有茅屋一間,屋前有一仙人伏案展卷,后有童子侍奉,屋后有小橋小山。從《青綠山水》局部與《翟道綱畫仙洞隱居圖》來看,翟道綱作品的突出特點是喜畫仙人,并伴有鹿鶴等。
郭沫若在該詩中提到的仙家、鹿鶴等,正是翟道綱畫中常出現的題材。所以我們推斷,《題道綱先生畫》中的道綱先生,正是張大千的弟子翟道綱。
《張大千的世界 大風堂的世界》對翟道綱有簡要介紹:“翟道綱(1903-1951),名浩,字道綱,四川崇慶(今崇州)人。”“自幼戲弄丹青,1923年畢業于四川美術學院,后拜張大千為師,隨師學畫10余載,并于1947年至1949年在成都金牛壩侍師左右,得大風堂神韻,翟道綱曾先后在西昌師專,成都南虹美專任教數年,擅長畫山水,人物,花鳥,精書法,治藝注重師古,師自然,講求筆墨意趣,強調作品的抒情性。1945年,1946年分別在四川崇慶、成都青羊宮舉辦《翟道綱書畫展》,受到美術界前輩的好評,認為其作品勃茂、渾厚、雄奇、酣暢,具有時代感和抒情性。”
在這首題畫詩中,郭沫若對翟道綱的畫頗有批評。“人間逸處即仙家”,是說人間也有仙家。“桃李枝頭正著花”,意為春滿人間即仙境。“鹿鶴人間隨處有,仙人何□緲云霞。”中間一字我們沒有認出,但大概意思是說,相比于風餐雨露,虛無縹緲的仙人,人間處處都有值得表現的對象。可見,郭沫若對于翟道綱作品喜表現“仙家”而非人間頗有微詞。
從這三首題畫詩中,我們歸納出郭沫若國畫觀之一斑:相比于凌虛蹈空之作來說,他更喜歡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除這兩首詩外,郭沫若的另一首題畫詩也能作為證據。抗戰時期,郭沫若為關山月畫作題詩:“生面無須再別開,但從生處取將來。石濤河壑何藍本,觸目人生是畫材。”[6]“但從生處取將來”,反對因襲模擬;“觸目人生是畫材”,則張從現實生活中取材,這跟本文所討論的三首題畫詩相呼應,共同表現了郭沫若對于不同題材的國畫的態度。
注釋:
①標□為字跡模糊,未能辨出者。
[1]龔濟民.郭沫若的題畫詩[J].郭沫若研究(第1輯),1985.
[2]郭平英.交相輝映市花魂——記郭沫若與傅抱石的友誼[J].新文化史料,1999(6).
[3]白堅.郭沫若題畫詩淺探[J].郭沫若研究(第3輯),1987.
[4]蘭石.張文元先生的繪畫[N].新蜀報,1943-03-13(4).
[5]馮玉祥.題張文元作空襲下之戰都詩[N].新蜀報,1943-03-13(4).又刊《時事新報》3月13日第4版.
[6]郭沫若.題關山月畫[N].新華日報,1945-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