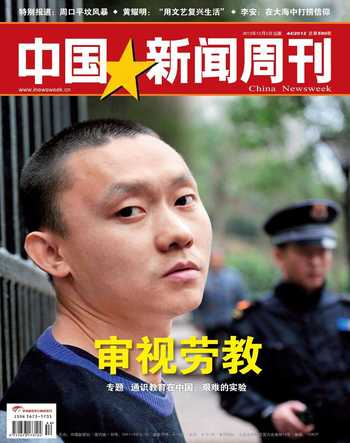洋務新政的加減法
馬勇
1860年,中國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艱難歷程,史稱“洋務新政”,或“同光中興”。經過三十多年發展,中國的經濟構成發生巨大改變,近代化的工業基礎逐漸成型,一個新的社會階級、即中國資產階級也在緩慢成長,中國的政治架構尤其是法律制度經過三十年調適,也在向世界靠攏。
就在中國按部就班前行時,士大夫階層和軍方鷹派覺得中國已經了不起,發誓像列祖列宗那樣開疆拓土,弘揚國威。于是,中國在洋務運動三十四年時改變了韜光養晦的既定政策,為朝鮮與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幾個月,大清國“同光中興”的神話消失得無影無蹤。
中國三十年高速增長依然不敵同期發展的日本,戰爭結束后國人痛定思痛,以為都是先前“中體西用”惹的禍。此后短短十幾年,大清國成為歷史,中國發展根本轉向。無法假設中國在1895年的轉向是好還是壞,只是回望歷史,中國放棄洋務新政實在可惜。
根據清廷在1860年代確定“中體西用”路徑時的看法,中國之所以不必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全盤西化,脫亞入歐,并不是中國不愿學習西方,而是因為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自己的政治架構,中國所缺在近代科學技術,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后中國沒有適時跟上。所以,中國不需要在政治架構上大動干戈,中國的發展只需要做加法,不需要或者說很少需要做減法。中國應該增加自己文明形態中所不具有的西方元素,但中國沒有必要像日本那樣與傳統訣別,從頭開始。
中體西用的理由在那時是充足的,中國人在整個洋務運動時期充滿自信,所以當日本使者1870年代向中國方面傳遞明治維新思路和做法時,中國人并不認為日本的做法值得中國仿效。
事實也確實如此。中國的洋務運動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力量謀取發展,短短幾年時間,中國就能有效消化西方高科技,轉化西方高科技,并成為中國發展的有效力量。根據不完全研究,中國在1870年代初期,現代輪船制造業、軍械制造業等,已經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利用西方技術,趕上西方的制造能力,金陵機械制造局、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福州船政局、漢陽鐵廠、湖北織布局等一大批具有西方元素和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發展迅猛,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奇跡。
除了實業發展,洋務新政也注意與世界發展的一致性,創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管各國對華投資、交涉等事務;創設同文館,培養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派遣幼童出洋留學;派遣駐外公使分布世界各大國。應該說,中國在洋務時期有足夠理由自信“中體西用”的道路、理論和體制,因為畢竟短短三十年使中國面貌根本改變,創造了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奇跡,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奇跡。
然而,為什么經過一場并非毀滅性的甲午戰爭,中國人就集體無意識轉向,不再認同先前的堅守呢?
洋務新政不論具有怎樣的中國特色,就其根本目標而言,就是回應西方,與世界一致。中國沒有像日本那樣從一開始就轉身向西,沒有休克療法,沒有先進行政治改革,重建制度,再發展經濟和科技,而是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用加法,迅速增加中國的物質財富,用國家資本主義力量迅速拉近中國與世界的差距。
但是,中國并不是因為發展就要脫離世界發展的主航道另搞一套。清廷應該在洋務新政發展早期,至少在1880年代中國新一代知識人起來的時候給予清晰解釋。這一代知識人已經知道世界,知道西方富強的根本在體制,知道民主制度,知道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當此時,清廷如果有意識釋放對社會的管控,有意識釋放言論空間,有意識釋放對資本的管制,有意識在國家資本主義之外培植更多的非國家資本主義。換言之,1895年走向維新之后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方面的舉措,在洋務時期都能得到嘗試,那么可以相信,由清廷主導的洋務新政方才有真正意義的出路。
一個不敢充分釋放社會潛能的體制肯定不是自信的體制,一個不能充分容納各種發展方式的道路肯定不是自信的道路。同樣,一個置各種不同意見于不容討論地位的理論,肯定不是一個真正自信的理論。因此,當三十年洋務沒有經得起甲午戰爭考驗之后,人們不是對先前道路給予理性反省、善意同情,肯定其成功與意義,設法彌補不足,而是棄之若敝屣,重新開始。這是非常可惜的。
中國文明之所以博大,就是因為中國文明從來不拒絕外來的東西。其實,清廷當年已經在這樣做。
清廷在宣布中體西用后,并沒有畫地為牢。中國自1870年代開始,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乃至法律、體制,西學之用的范圍有擴大的趨勢。只是清廷統治者不愿這樣說,以為只有堅守祖宗老路才是正路。等到甲午戰爭結束,沒有人舊話重提,而是用最簡單的辦法棄舊圖新,從頭開始,這是中國歷史發展中最大的不經濟。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