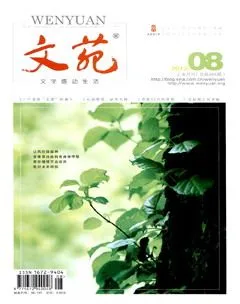沒有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
柴靜
▲1▲
“我是踩著尸體上船的。”高秉涵說。
十多萬人在金門的海灘上等船,來了兩艘,每艘最多能裝一萬人。他13歲,拖著一根棍子,瘸著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這是哪兒,也不知道要去哪兒,他離開山東老家逃難6個月了,他媽媽說,跟著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時候登陸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樣往上沖,剛開始沒有一個能進去,全都卡在門口,“擠不進去就往下踩,就這么踩著人上滿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個兵拿槍托往下拼命壓他的肩膀,準備踩著他上船,一個軍官一槍把士兵從他肩上打下來,救了他。“我上了船兩只腳都沒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沒有走路,是被推上去的。你不走都不行。”
有些沒上船的兵,拿著槍就對著船上的人打,機槍打過來,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個炮彈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彈,船就會沉了。
他躲在船艙的廁所里,里面擠了七八個人,“站的地方動都不能動啊,就是這樣到臺灣來了。”
這是1949年最后一艘開往臺灣的登陸艇。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紹唐,是清末最后一批公費留學生,在日本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是資深的國民黨元老派,后任東昌府知府。
高秉涵的母親叫宋書玉,與丈夫在山東菏澤農村創辦新式小學,發展鄉村教育。1948年,內戰激烈,一個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的父親是學校校長,在地方沖突中被槍殺,姐姐失蹤,后來才知道是去了延安。
母親擔心13歲兒子的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塊袁大頭,一根父親死亡時身上的繩索,一張初中新生入學證明,讓他在父親墳前磕了三個頭后,離開家去投奔設在南京的流亡學校。
母親送他到東關外上車,馬車上是木板,兩個車輪是汽車胎,一二十個同學,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那時石榴剛熟,外婆摘了一顆,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經熟得裂開了口,小孩子看著鮮紅晶亮的石榴籽,忍不住低頭吃了一把,這一口的工夫,同學推他:“你媽喊你。”
他一扭頭,車已經拐過彎,再也看不到他母親了。
77歲的高秉涵說:“我這一輩子再也不吃石榴。我看到石榴,就傷心。”
▲2▲
他把褲腳卷起來,小腿上全是黑色的傷疤,上面沒有肉,只是一塊一塊黑色的皮。
他說:“都被蟲子吃完了。”
當時南京學校解散,學生們一哄而散,他無處可去,不敢返家,跟著人流走,走了六個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汽車、騾馬、傷兵、難民……軍隊扎營做飯時,他扯一個芭蕉葉,窩一點粥喝,前面排著兩個士兵,剛盛的熱粥,突然有人喊“共匪來了”,第一個士兵荒促轉身,一缸熱粥全潑到了他腿上,第二個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也潑了上去。沒人顧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著逃。
天氣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個人,部隊都走過去了,難民都走過去了。他一個人走,下著小雨,山上猴子野豬叫,他拿著個木棍,披著個蓑衣,都是棕葉做的,腿已經腫得爬滿蛆蟲了,沒有鞋子,拿破布在腳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見五指的晚上,有一個土地廟,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覺,他就往邊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還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邊的人的耳朵,那是一個人的尸體。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個兵,背著個紅十字的包,高山邊是懸崖,彎彎的路上有水流。“他拉著我,說小朋友過來,我給你把蟲子沖掉,拉著我腿就沖,沖完以后,他就給我用救急包包住。我仔細看他的帽子,是個星星,是共產黨。”
一個禮拜后,傷口流的膿,加上人的溫度,救急包都變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殼揭不開,他又遇到一個帽子上有太陽的士兵,用刺刀給他挑開,里面都腐爛了。
我問他,這一路上你想起你媽嗎?
他說,不想,只想活著。我活著,就是為了她。
他孤身一人到了臺灣,無親無故,沒人顧他的死活,睡在火車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搶吃的。他說:“那時候沒有將來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
他能夠生存,是他母親在包袱里放進去的初中新生錄取證明。
那是一張棉紙,稀軟綿薄,居然沒有破損。逃難中他把所有的家當都丟了,有一次扒上了軍車,車上的軍官讓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說,現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過河的時候,兩個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濕透了,但這張棉紙居然一直完整無缺,他怎么也記不起來,想不明白。
靠著這張紙,高秉涵在鐵路局當小販的時候,才有機會考上臺灣“國防管理學院”的法律系,1963年畢業后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
我問:“您剛到臺灣生活,那么孤獨的時候,逢年過節怎么過?”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個人。大聲哭,對著淡水河口對著大陸痛哭一場。我平常不掉淚,掉淚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淚,我就大聲叫。”
“叫什么?”
“叫娘,大聲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說普通話,只有說這句時,還是濃重的山東口音。
▲3▲
他審的第一個案子是金門逃兵案,一個姓鄭的士兵在值崗時冒險抱一只輪胎穿越金門海峽想游回廈門的家,第二天一早終于登了岸,舉起雙手對走過來的持槍者說:“不要殺我,我是回來看我媽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沖回了金門。
這個逃兵當年并不是軍人,他是廈門漁民,出門給半身不遂的母親抓藥時被強抓入伍。明知危險,這個被強征入伍的漁民還要逃亡,因為他駐崗的地方,天氣晴好時能看到自家村莊的屋頂。
按照當時臺灣《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七條,他被判處死刑。
我問高秉涵:“你給這個人下死亡裁決的時候,你有沒有在內心問過自己,假如換作你在他那個位置,你會怎么樣?”
他想都沒有想:“我比他還逃得快,還逃得早。”
姓鄭的士兵對他講,希望能夠早一點槍斃,他說早一點槍斃,他的靈魂可以去看他媽了。臨刑前,這名逃兵把十幾年前買的藥交給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帶給自己的母親,如果不能,就把藥裝進瓶子里,寫上“鄭賀氏”漂去海上,也許能夠漂到家鄉。這些藥片已經近乎粉末,高秉涵拿著藥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變成一個……我是殺死一個回家探母想媽媽的人的劊子手。”
兩岸開放之后,高秉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廈門,想找到這個逃兵的母親,替這個逃兵行孝。但那位母親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1979年,高秉涵寫了一封信,委托同學,經由英國,到美國,終于寄到:山東菏澤西北35里路小高莊,宋書玉。信中寫:“娘,這么幾十年,我還有這個毅力,還要活著,就是為了最后能夠活著見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著回來。”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來自故鄉的第一封家書。他的信到的時候,母親已經去世一年了。弟弟說:“自從你離開家以后,我們家里幾乎沒有笑聲。除夕晚上這一餐,媽媽幾乎沒吃過飯。都是淚流滿面,在媽媽旁邊,餐桌上放一個碗放一雙筷子,留給你,‘春生,不管你活著沒活著,過年了,你就陪媽媽再吃一餐吧。”
母親去世后,在她枕頭底下有兩件東西,一個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個是為他做過的小棉襖。當年給高秉涵做這件小棉襖時,母親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給我聽:“冷風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兒需寒衣。”
“你怎么老記得這幾句呢?”我問。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媽媽,寒衣就是代表媽媽是不是?冷雨、冷風代表大時代洪流的沖擊。我需要溫暖,需要媽媽。”
這個快八十歲的老人,說“媽媽”時,是娃娃才有的聲調。
▲4▲
他寫了15本日記,記述他童年印象中的萬事萬物:白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歡吃的花、隔壁二狗爺家的黑狗,門口槐樹上的喜鵲,童年最好的伙伴糞叉子——之所以叫糞叉子,因為他最愛偷吃桑椹,一臉的蜜汁,風一刮一臉土就糊上了,總有蒼蠅圍著烏黑的嘴轉,被奶奶打得雞飛狗跳……
日記被同鄉們翻得都快散了,后來毀于洪水。去往臺灣的老鄉里,很多沒有受教育,沒有工作技能,也沒有娶妻生子,有幾位開了“北方饅頭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點鄉土滋味,就這么生存。
上世紀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經移民阿根廷的菏澤老鄉回鄉探親,路經臺灣,帶了一些家鄉的泥土和小吃來,三公斤的土,分給一百多個菏澤老鄉,只能一家一調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識貨”把“寶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來鎖到保險箱里,另一半分七次沖水喝下。“水是從我嘴里面進去了,但是水一剎那之間又從我眼里出來了。掉的淚何止七壺呀。元朝有一個作曲家,說是斷腸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無歸期的人才會斷腸。”
28年了,在他家冰箱里,還放著那包山東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裝的胡辣湯。
1987年10月15日,臺灣當局宣布開放臺灣居民到大陸探親,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鄉,在村口,他一個人呆了半個小時,走不進去,“我怕,怕進去。那種心情,用文字沒辦法形容,近鄉情更怯,老祖宗真是偉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個老人就問,先生你找誰呀,他說:“我找高春生。”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幾十年前死到外地了。”
這時他才認出,說話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問“糞叉子”還在嗎,過一會兒遠遠看著有人拄著拐棍一點一頓來了,喊“春生哥”,他摟住已經鬢發皆白的童年玩伴,說“糞叉子,我不嫌你臭”,兩個老人笑淚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親人也都已經離開了村莊。他看到老樹猶在,捋了一把樹上的榆錢,晶綠的銅錢一樣,只有口中這一點新鮮的苦澀滋味沒變。這個13歲離家,年過花甲的老人,最終站在母親的墓前,大哭一場。
▲5▲
高秉涵是同鄉會會長,年紀最小,老友一個個逝去。從1992年開始,他把這些故人的骨灰從花蓮公墓一個個接回,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個七八斤重,他只有44公斤體重,一年帶兩只,放在拉桿箱里,上飛機運回大陸。安檢的人員以為他運的是毒品,要他開箱檢驗,他次次都要解釋。
送回大陸的骨灰,很多已經沒有親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樹或者玉米田,一邊撒一邊跟他們說話:“我把你交在這兒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邊上村里人說,這老頭,神經兮兮。
我問:“這點念想就那么重要嗎?”
“在我們來說,沒有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因為我們流浪過,曾長夜痛哭過。所以我們人生跟一般人感覺不太一樣,也是心靈的一個皈依吧。”
他為長孫女取名佑軒,庇佑母親之意,小孫女取名佑荷,如果還有小孫女出生,想叫佑華,我問一個普通人為什么要有家國的情懷,他說:“就等于一個小狗,來到一個新的,里面有電器設備冷氣,很漂亮一個狗窩,你放心,到晚上那個狗要去它原來的狗窩。為什么?它聞聞味道,那個不是它的味道。”
他說:“家國,就是一個人的窩。”
他把母親用過的藍綠鑲金的胸針,滴玉小耳環,已經粉化的眼鏡,用來搗蒜的小缽子,都裝在小盒子里,留在身邊,他用手輕輕觸著胸針上面的青銹,怕蹭掉。
地下室的側墻上,母親穿過的湖藍色綢衣,一直掛在墻上,衣襟胸口處有當年留下的一粒斑點,他連洗都不舍得,怕丟掉一根絲。
他說:“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頭頂頂我母親那個衣服,這樣等于在她懷里一樣。”
摘自作者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