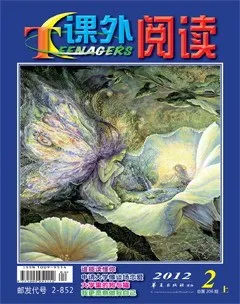沒了手的爸爸
當白雪公主吃毒蘋果的時候,她的爸爸在哪里?當灰姑娘被欺侮的時候,她的爸爸在哪里?
陪女兒看迪斯尼的卡通《獅子王》。
“真高興,終于在迪斯尼的卡通里出現爸爸了。”走出影院,我興奮地說。
“不對!不對!迪斯尼卡通里都有爸爸,只是沒有媽媽。”小女兒立刻叫了起來。
妻也附和:“是啊!沒有爸爸,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哪來的后母?睡美人有國王爸爸、木偶匹諾曹有木匠老爸爸、《美女與野獸》里的美女不也是為了救她爸爸而留在古堡嗎?所以迪斯尼的電影里,主角多半死了親媽,剩下保護不了孩子的飯桶老爸!”
我怔了一下,答不上話,想到《睡美人》里對付不了巫婆的國王爸爸,和許多其他故事中后娘的嘴臉。
可不是嗎?當白雪公主吃毒蘋果的時候,她的爸爸在哪里?當灰姑娘被欺侮的時候,她的爸爸在哪里?
迪斯尼制造了一堆無能的父親,難怪我忘記了他們的存在。
許久以前在報上看過一則有趣的新聞。臺北某幼稚園的主任為了解孩子心目中的父母,特別收集了一百多幅小朋友的圖畫,發現里面大多數的父親沒有手。
“在孩子心目中,父親是缺乏接觸的人。”幼稚園的主任說。
父親真是不太跟孩子接觸的嗎?我想起女兒小時候,洗澡全由我負責。有一回生病吐奶,我甚至急得用嘴去吸她被奶堵住的鼻孔。
但也想起有一次到朋友家,看他的女兒尿布濕了,朋友要去幫忙,卻被他急忙趕來的母親拉開,十分嚴肅地說:
“男人,怎么能做這種事?這是女人的事!”
難道舊社會父親那種不茍言笑,不太跟孩子打成一片的樣子,竟是所謂的“風俗禮教”教出來的嗎?
記得大學時代,一位老教授說過:“男人就像公鳥,當母鳥在窩里孵蛋的時候,公鳥的責任是出去找東西吃。所以男人不能待在家里,他的天職就是出去工作。男人太愛孩子,會影響事業的發展。”
他這段話影響了我好久,可是有一天看到一幅精彩的圖片,我的觀念改了。
圖片上是冰天雪地的南極,成百上千只企鵝直挺挺地朝著同樣的方向站著,好像千百塊“黑頭的墓碑”,立在風雪中。
我好奇地看說明,才發現那是正在孵蛋的帝王企鵝。它們把蛋放在雙腳上,再用肚腩和厚厚的羽毛包覆著,使那些蛋在攝氏零下四十度的風雪中,仍能維持在零上三十七度。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孵蛋的全是企鵝爸爸。
在雄企鵝孵蛋的五十多天,雌企鵝會去遠方找食物。她出走的兩個月當中,雄企鵝不吃任何東西,就這樣直挺挺地站著,因為只要它們離開幾分鐘,那蛋就會被凍壞。而當小企鵝被孵出,媽媽還沒回來時,企鵝爸爸則吐出自己的胃液,來哺育孩子。
我也在生物影片里,看見一種俗名耶蘇鳥的涉禽,照顧幼鳥的工作,完全由公鳥承擔。影片里兩只小鳥在水里玩,公鳥則在一邊守望,突然看見鱷魚游過來,雄鳥立刻沖到小鳥身邊,張開翅膀,蹲下身,把小鳥一左一右地夾在腋下,飛奔而去。
我還在美國奧杜邦生物保護協會出版的書里,看到一種叫蹼腳鷸的鳥,完全由雄鳥負責孵蛋、帶孩子。
書上解說:因為這種鳥跟其他鳥不同,它們的羽毛不是雄鳥華麗,而是雌鳥華麗。雄鳥體形也比較小,既適合在小小的巢里孵蛋,又有保護色,所以夫妻的職責就互換了。
合上書,我心想,連鳥類都知道夫妻看情況來調整角色,為什么在人類社會,許多人反而認為只能由媽媽照顧小孩?要知道,男人不但會很愛孩子,而且當妻子不讓丈夫“動手”的時候,也是剝奪了孩子和父親相親相愛的機會。
記得小學時候,有一篇課文:
天這么黑,風這么大,爸爸捕魚去,為什么還不回家。
記得林煥彰有一首詩:
我很辛苦,夜以繼日。肚子餓了,也不敢買東西吃。我打街上走過,看人家的孩子,圍著面攤吃面;看人家的孩子,跑進面包店買面包;看人家的孩子,擠在糖果店里買糖果……我邊走邊想:回家以后,我該給我的孩子,一些些零用錢,偷偷地擺在他們的書包里。
我邊走邊想……
記得在四川,一位卡車司機對我說:
“我可以用偷的,用搶的,甚至不得已,用殺的,也要讓我的孩子過得好。”
記得《中國之怒吼》那部抗日影片中說:
為了我們的子子孫孫,我們要戰斗下去。
更記得,我的一位大學男同學,年輕時豪氣干云,滿懷理想,稍不順意,就大發雷霆。二十年后,再見到他,安靜了,即使上司借故找他麻煩,他也低頭忍下來。
“沒什么!沒什么!掙碗飯吃嘛!多累、多氣,回家看孩子一笑,就都煙消云散了。”
我常從辦公室的窗口,看馬路上匆匆來往的男人。下班時,許多人像是用頭拉著身體向前走。我就想,他們的頭又是被誰拉著走呢?
是家?是孩子?
每次在電視新聞里,看見戰場上滿地的尸體,絕大多數是男人的。我都想,他們當中,有多少,會是孩子的父親?他們的孩子,有多少,會真正想到,父親是為家而殺人,也為家而被殺?
今天,我要對每個“沒為父親畫手”的小朋友說:
不要以為父親不常抱你,是不愛你。他的手可能正在弄黑黑的機油,他的手可能正在掏臟臟的下水道,他的手可能正在電腦的鍵盤上打得酸痛,他的手可能正在急著多掙些錢——給你。
他的手,甚至不知道疼惜他自己!
所以,不要等他伸出手擁抱你。你應該先伸出手擁抱他,說一聲:
“爸爸,我知道你的犧牲。爸爸,我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