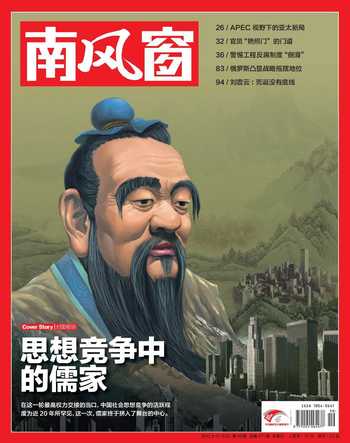回首天外,思入風云
陳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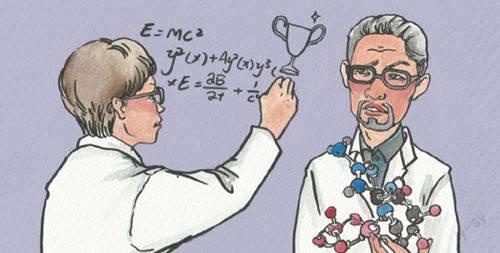
“基本物理學獎”
對于物理學界來說,這個悶熱的夏天一點都不沉悶:首先,日內瓦的大強子對撞機(LHC)宣布了—或者應該說是“通報”了希格斯粒子的發現。跟著,石破天驚、名不見經傳的米爾納(Yuri Milner)先生宣布頒發“基本物理學獎”(Fundamental Physics Prize)給9位理論物理學家,每位300萬美元,也就是諾貝爾獎足足3倍。這樣的豪擲自然引起了巨大轟動和好奇:米爾納到底何許人?
他本是俄國猶太人,出身高級知識分子家庭,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畢業,和薩哈洛夫友善,但物理學研究不成功,在蘇聯解體前夕赴美進賓州著名的華爾頓商學院取得工管碩士,后來得到葉利欽總統任內一些新貴特別是曾經顯赫一時的首富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賞識,于是以其特殊的俄羅斯投資關系在美國金融界闖出名堂,至終在硅谷投資社交網站成為億萬巨富。一言以蔽之,這就是俄裔物理學研究生轉行下海發了大財,現在以重賞方式來表揚心目中的英雄,和完成當初夢想。
那么,是些什么人值得如此獎賞呢?筆者離開理論物理領域數十年,孤陋寡聞,在9位得獎者當中曾經聽聞大名的僅3位:以研究超弦理論著名的韋頓(Edward Witten),提出宇宙早期急速脹大理論的古夫(Alan Guth),還有一位捷泰耶夫(Alexei Kitaev)則是最近才從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的孔良那里聽到的,只隱約知道他研究代數幾何學在基本物理理論上的應用,但獎項宣布則贊揚他在量子計算上的貢獻。根據正式宣布,其他6位的工作也都是在粒子和宇宙學這兩個基本理論領域,所以,以上3位可以說是具有相當代表性的了。
看來,9位得獎者的共通特點,就是都以高深抽象的數學為手段,來鉆研、發展最深邃奧妙的基本理論,至于這理論是否以已知原理為基礎,或者已經有實驗結果證驗,卻并不重要。創獎人米爾納強調,此獎就是要鼓勵、獎賞純粹的基本理論家,即使最后他們的理論得不到證驗,或者證明與事實不符,也沒有關系。這可以說是它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在理念上的根本分別。
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科學大獎,自然會引起無數猜測和議論,特別是創獎人已經宣布,以后每年都會繼續頒發同樣獎項,未來獲獎者由過去得獎者共同決定。那么下一屆得獎的,將會是些什么人?是否仍然由超弦和宇宙學專家壟斷呢?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亦即所謂“黑洞物理學黃金時代”,出現過多位引領風騷的人物,即發現旋轉黑洞和帶電黑洞的科爾和紐文,提出“宇宙隱蔽假說”的彭羅斯,當然,還有提出黑洞熱力學和輻射理論的霍金。他們的理論工作雖然都是從廣義相對論引申出來,但仍然極其美妙和驚人,倘若不是因為黑洞無法直接和仔細觀測,因而他們得到的結論也無法確切證驗,那么大有可能早都已經一個個去過斯德哥爾摩領獎了。如今他們垂垂老矣,是否也還有領得這巨額獎金的機會呢?那就得看首批領獎那9位先生的胸襟、見地和智慧了。
不過,對于“基本物理學獎”來說,這并不很重要,真正重要也令我們感到十分好奇的是:從長遠來說,真會有那么多卓越的純粹理論家不斷涌現(照首屆頒獎數目推算,最少也得有百人上下),都是值得如此宣揚和獎賞的嗎?他們中間會出現能夠真正作出重大發現(而不僅僅是美妙數學理論),如牛頓、麥斯威爾、愛因斯坦、海森堡、狄拉克那樣的人物嗎?否則,這個獎即使仍然能夠延續下去,恐怕也難免逐漸失去原意,蛻變為一個數學大獎了吧?
更何況,它到底能夠延續多久,現在恐怕也還言之過早。首先,至今我們還未曾聽到米爾納先生為此捐出巨款正式成立基金會,以使得頒獎可以獨立于他個人意愿以外長期進行。同樣重要的是,他宣稱把挑選未來獲獎者的權力交給已經得獎者,但這是沒有組織、結構,而且每年不斷在擴大、變化的一個群體,他們能夠充分負起客觀地審核和決定得獎人的責任嗎?不會淪為一個只求瓜分巨額獎金而且為此吵鬧、斗爭不已的同行、朋儕小圈子嗎?我們只能夠希望,米爾納先生這個破天荒的壯舉并非出于一時沖動,而有更長遠計劃和周密思慮存乎其間吧!
歐洲科學的兩大傳統
這個獎的未來發展和對于物理學的影響現在不大容易看得出來,但它背后的理念卻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值得一談。事實上,以猜測、猜想(speculation,這在中文沒有妥帖的對應詞)來思考宇宙基本結構是西方文明的大傳統。希臘第一位哲人泰勒斯提出,水是宇宙的“原質”,即基本資料或者運行原理,那就是這傳統的開端。跟著,畢達哥拉斯創立神秘教派,它的核心觀念就是把數學推理與宇宙結構的猜想結合,而且將此作為可以獲得永生(那可要比任何數目的獎金都誘人得多)的宗教原理。從此發展下去,特別是經過柏拉圖和他的學園大力宣揚和推波助瀾,就發展出光輝燦爛的古希臘科學,像歐幾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都是這傳統孕育出來的大學者。
到了托勒密的時代,希臘科學已經發展了700年之久,但此后則如花到荼,盛極而衰,開始沒落。這自然有許多不同原因,但現在為絕大部分史家所公認的一個主要原因,則是它過分注重猜想與理論,而忽略實際觀察,所以走進死胡同,無法有進一步的突破。托勒密秉承柏拉圖的構想,以為天體運行軌道必然是圓形的組合,就是這偏見的最佳說明。1400年后,哥白尼也仍然未能破除這偏見,直到開普勒,才由于丹麥天文學家第谷極其精密的天文觀測,“被迫”打破這桎梏,發現天體運行軌道其實是橢圓形而非圓形組合。
這樣,十六七世紀歐洲科學的新發展出現了兩種完全不一樣的精神,其一是繼續發揚古希臘的數學與理論傳統,其二則是沿著在中東發展的伊斯蘭科學傳統,注重觀測、實驗和計算。牛頓的大發現,正就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精神互補、結合所產生的成果。他將平生巨著命名為《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卻又將自己的方法稱為“實驗哲學”,所反映的正就是這個難能可貴的結合。在他之前的培根偏重于觀察、實測,笛卡爾偏重數學與冥思苦想,兩者在科學上的成就遠遠不能夠和他相比,也就是這個道理。因此,毫不奇怪,在18、19,乃至20世紀上半葉,物理學的無數發現、進展都是“兩條腿走路”,理論與實驗并重,甚至實證、觀測顯得更有力量,更重要。
然而,數學之深奧、精妙和玄思冥想所能夠發揮的力量實在不容低估:在上述近300年的大潮流中,也仍然有好幾個單純從數學和理論出發,而獲得大發現的例子。這包括麥斯威爾從數學自洽性出發改寫電磁理論,和發現電磁波;愛因斯坦發現廣義相對論,也就是比牛頓萬有引力更根本、更正確的重力理論;以及楊振寧發現規范場理論。這些例子說明,直到今日,如古代哲人般回首天外,思入風云,仍然可能是探究宇宙奧秘的途徑,而畢達哥拉斯那奇特的宗教—科學信念,也就是古希臘的“純理論沖動”,還是有其價值和重要性,不容完全抹殺和忽視的。
不過,這個說法卻還不能夠完全適用于“基本物理學獎”。為什么呢?因為上面幾個大發現雖然是高度理論性和依賴數學思維,然而出發點卻無一例外,都仍然是已知的、經過詳細證驗的物理原則。也就是說,它們的發現有如撐桿跳,運動員雖然凌空飛越6米高度,但所撐的那根桿子卻必須牢牢地扎在地上。沒有桿子而憑空騰躍,那就只能夠翻越徒手跳高的兩米了。在許多重要理論物理學家看來,不講求實證基礎的超弦和其他相類似理論,就像舍棄撐桿而試圖翻越6米高度,是異想天開而不可能成功的—甚至成功與否,也是沒有辦法驗證、判斷的。
但“基本物理學獎”正是反其道而行,要尊重、獎勵這些不講求實證的純粹理論家,這可以說是一個“回歸希臘”,甚至“回歸畢達哥拉斯”的呼召。它有意義嗎?它會如2500年前那樣,造成龐大影響,乃至帶來一個新運動,新傳統嗎?我的感覺是,大多數物理學家恐怕都不會看好。但科學發展的途徑有時候是極端奇特,甚至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因此,我們還是應該靜觀其變,而不必急急忙忙下結論—畢竟,米爾納有他的理想、財富和自由,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