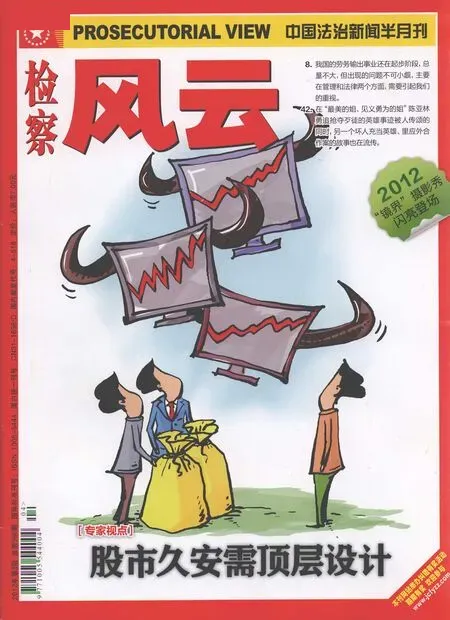綠色轉型與危機救贖
文/朱敏
綠色轉型與危機救贖
文/朱敏
“十二五”綠色轉型與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賴于激發“企業家精神”,給社會營造一個創新創業的良好氛圍;救贖危機必須尊重法治信念、構建博愛與契約精神
政經觀察家
朱敏
哥倫比亞大學中國企業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經濟導刊執行總編,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著有《中國經濟缺什么》《轉型的邏輯》等。
中國經濟怎樣才算“綠色轉型”?以我的理解,就是轉到讓人們不光“吃得飽”,還要“睡得香”。作為財富創造者,雖然不乏在收益豐盈的狀態下將收獲的財富投入慈善事業或社會公益、讓更多人分享其快樂的企業家,但蕓蕓“飽食者”之中,有幾個人敢說:自己睡得香,晚上還能美夢連連?
“睡不香”還算好的,“睡不著”就更麻煩了。中國不在少數的企業家現在處于“睡不著”的狀態,這就非常麻煩。沒錢的時候煩,煩肚子餓;賺錢的時候也煩,要動手動腦;有錢的時候可能還更煩,煩的是沒有財富安全感,煩的是從身體到心理存在著一種亞健康,煩的是各種各樣的危機,尤其是企業永續經營、可持續發展的危機,或者二代接班的困惑,出現迷惘、麻木、焦慮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因此就面臨“轉型”。
經濟社會的轉型,在我看來,從結果上講,核心是企業家的生態問題得到改善。換句話說,經濟轉型的核心,首先要實現企業家的心智與精神狀態的健康轉型。
“企業家精神”與喬布斯的非物質遺產
究竟如何綠色轉型、健康轉型?可能會有很多路徑,并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但是所謂經濟社會的轉型,除了發揮正確政策的正確引導以外,這時候我特別想強調一個觀點:還要充分信任企業家、尊重企業家,營造一個陽光的企業家成長氛圍,自主發揚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及企業家的創業精神。而且,也只有發揚“企業家精神”,我們才能在經濟舞臺上各司其職唱好這出“主角”的大戲,跟上新時代浩浩蕩蕩的經濟潮流。恰恰在這一點,在我們急功近利的氛圍內,是最容易被忽視的。
實際上,“企業家精神”不光是對經濟轉型的中國經濟非常重要,對全球來講都非常重要。最早強調“企業家精神”的經濟學家就是熊彼特,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學術領域里面的發現,那就是: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長期擁有活力,根本就在于創新。而這個創新的來源,究竟在哪里呢?這可能就涉及到剛才說的“企業家精神”,他著重強調的正是這個。與此同時,他也創造了一個“創造型毀滅”的詞語,來描述市場活力來源和經濟發展規律。他率先把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引入到經濟學當中,最早闡述了創新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值得一提的是,“企業家精神”不僅僅是產生于像微軟、摩托羅拉這些富有能量和規模的大公司,實際上,甚至像諸如大學宿舍、地下車庫等等毫不起眼的地方,也可以產生“企業家精神”。

中國明確提出的目標,可能是10年之后,也就是2020年,要成為一個創新型的國家。我們對創新的投入其實也非常巨大,在產業扶持、人才引進等政策上,可以說是不遺余力地支持。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實際上創新是一個結果意義上的東西,而非手段,如果只靠大量的資源資金的投入,既是不夠的、也是浪費的。問題其實還是存在于機制上面。更本質來講,可能有更為鮮明的一個觀點,那就是創新其實是無法人為地、主觀地造出來的,創新應該是市場需求與“企業家精神”結合的產物。當我們蜂擁搶購蘋果iphone手機,驚嘆于技術的創新和神奇的創意,我們應該深深地知道一點,它是如何拿捏市場的需求;同時,我們千萬不要忽視喬布斯們留給世人的非物質遺產,只有它——“企業家精神”,才是那只“看不見的手”背后另一只無形的“幕后推手”,控制著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優化配置資源,它才是市場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原動力”。因此,企業家無疑是市場當之無愧的主體、理所應當的主人。可惜的是,并不像“看得見的手”投入的資源、資金、和產出的GDP那樣易于量化,“企業家精神”很難量化。盡管如此,仍有不少學者在嘗試做基于實證的數理研究,為“企業家精神”獲得更多認同提供理據支持。
“企業家精神”是誘發和促進制度變遷的基礎因素,也是技術創新的巨大動力,我們應著力從制度安排上來培育“企業家精神”。尤其在當下“中國特色的凱恩斯主義”如此強而有力的情勢之下!談到這里的時候,我們還有一個傾向或誤區,就是有些人坐井觀天,認為全球金融危機凸顯了中國特殊制度的優越性,認為自己沒有受到正面沖擊,而且比美國等國家更能應對自如。實則不然,這需要我們進一步商榷。不妨打一個比喻:你看到別人游泳時不小心嗆水,就為自己沒去學游泳而竊喜。這種價值判斷本身,我不認為是一種健康的心態。殊不知,你沒嗆水是因為你不會游泳,是由于你落后啊。中國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沒有受到正面沖擊,道理不也是這個嗎?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國家,都不能把自身缺陷和不足作為優勢總結。在全球化大潮里,“游泳”的本領你是必須學會的。
回過頭來,我們要說,企業的永續經營,經濟的長足發展,終究都要靠“企業家精神”,才能永葆活力。我之所以這么強調“企業家精神”,實在是因為國內對這一塊的重視不太夠,我們的所謂創新一直處于自上而下的供給狀態,往往不是從現實的或潛在的市場需求出發。我們也呼吁能夠從創新制度、創新體制上改變,使我們的政策盡可能朝向市場需要的導向出發,真正服務于企業家,激發“企業家精神”,從而使“看不見的手”背后這只無形的“幕后推手”源源不斷地優化資源配置。
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十二五”綠色轉型與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賴于激發“企業家精神”,有賴于營造一個創新創業的良好氛圍。
對誠信的重視程度,反映社會成熟度與制度文化
在“企業家精神”缺失的制度環境背后,我們仍然要進一步檢討社會文化層面的因素。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發布的“中國企業經營者成長與發展專題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企業家有時出現或經常“煩燥易怒”的占70.5%,“疲憊不堪”的占62.7%,“心情沮喪”的占37.6%,“疑慮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強”的占28.6%,“悲觀失望”的占 16.5%。看起來,即便企業家群體,已積累了超出常人難以想象的財富,他們確實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樣幸福。
孔子云:“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內心的平安幸福和信仰、信念等是相關的。而近些年一波接一波的名人失信悲劇,令人不得不審視:企業家的誠信與信仰,如今究竟是怎樣一種程度?
應當說,當下社會的功利氛圍是中國迫切需要改變的。即便有些企業家的所謂“裸捐”行為,仔細看你會發現,實質上不是慈善,而是捐給了公安、稅務等政府部門,相當于一種利益的保護和交換,而且這種“慈善”加重了中國人的不信任感。還有一些地方,警察為了當地的企業竟然跑來北京抓人,也是利益的驅使。
近兩年來,包括炒得沸沸揚揚的唐駿“學位門”以及“李一事件”、“曹操墓風波”,還有更為熱鬧的國美黃光裕和陳曉“股權之爭”,以及由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引爆的慈善風波,等等,其實這些事件也好、風波也罷,都體現出很嚴重的誠信危機。對于國美權爭,說實話,陳曉的行為并不怎么光彩,他不管黃光裕有什么罪,作為職業經理人也應履行職業操守,不能玩內部人控制,把企業據為己有。放眼整個中國職業經理人的問題,就是誠信危機,企業界也是如此。比如新華都集團,至今還在雇傭唐駿,讓人很難想象。
對比一下,在美國,人們常常是不惜巨大代價來捍衛誠信。惠普公司前經理人馬克·赫德僅僅是因為用公款泡妞就被開除。據說此君很有能力,擔任CEO期間,惠普股價增長了一倍多,業績大幅上升。以經營收額為標準,四年前惠普超過了IBM,進而成為全球第一大科技公司。在他離職前,業界對他頗多溢美之辭。但是,一紙性騷擾的指控,就此斷送了他的惠普生命。惠普提前終止合同,公司賠償了他1220萬美元遣散費和其他一些利益,消息公布后,惠普股價重挫9.3%,大約縮水100億美元。
惠普為什么舍得犧牲如此巨大的代價,讓一個戰功赫赫的“將帥”走人?這就叫“寧失一帥,不失一信”。惠普董事會表示,赫德違背了“惠普商業行為準則”。因為董事會對他整個人的誠信品質,產生了信任危機,就沒有辦法再用這個經理人。即使付出巨大的代價,也不足惜。從這件事,你可以看到,一個成熟的社會是多么地看重個人誠信。而這背后,也是一個法治社會里信用體系的高度健全。可見,制度文化對社會成熟的影響有多重要。
在美國,騙人的成本非常高,就像有的中國偷渡者以諸如政治庇護為借口,很容易獲得綠卡,不過雖然好騙,一旦發現你撒了謊,懲罰會很重,騙子的日子就不好過了。而在中國,騙人的成本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比如唐駿,事后依然穩坐泰山,甚至認為“有能力騙到所有人就是成功”。我想這正是誠信問題,背后本質是信仰的缺失、倫理的淪喪。
救贖危機須尊重法治信念、構建博愛與契約精神
信仰是道德的源泉、慈善的源泉。其實憲法也賦予了我們公民的合法信仰自由,只不過多數國人的信仰還有些流于形式,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有的往往成了以祭神拜鬼來尋求一種心靈上的寄托;而且,社會大眾對所謂成功人士的個人崇拜也很嚴重,“成功學”盛行。
美國憲法基本上是按照三權分立的思想實施的。原因是他們相信人都是有原罪的,總統是靠不住的,必須有法律制約。而中國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總想出現清官,想要好皇帝。美國人從來不相信有好皇帝,不管你是什么人,總是有罪的,如果不加以任何約束,最終一定會變壞。于是,美國人按照完全不同于中國的信念路徑建構了美國社會。
而在中國,至今在最深層的理念上的啟蒙還未真正完成。“五四”啟蒙的是民主與科學,后來經濟學家楊小凱發現“民主與科學”并不是終極目標,更重要的是“自由與共和”,即保障每個公民的自由權利。再之后他發現,自由和共和的背后是信仰。在另一位經濟學家趙曉看來,當前中國轉型,缺少兩樣屬于文化倫理層面上的東西:一樣是博愛精神,它有別于傳統意義上的仁愛。仁愛視對象不同會有愛在程度上的等差,也會因對方的不善導致以惡制惡、冤冤相報的結果;而博愛是無條件的,不管是親人還是朋友,甚至陌生人,更甚至是傷害過你的人,都要愛他們,所謂“愛你的仇敵”,這樣,惡的循環就可以在此終止。要構建和諧社會,就要以博愛之心對待所有人,以此構筑強大堅固的文化基礎。另一樣就是契約精神。無論是工商文明(市場文明)還是憲政文明,誠信都最為重要,高度的市場文明和憲政文明需要建立在契約精神基礎上。契約精神的構建,應貫穿在整個中國轉型之中。
誠信和信仰,已然成為今天國人的短板,這雖是相當痛心疾首的事實,但至今并沒能形成一個基于共識的“解決方案”。既然只有經歷基于契約精神和博愛精神的現代性轉換,中國才有望跳出歷史上治亂循環的周期律,真正實現偉大的崛起與進步。
應該說,過去30年對中國而言,人力資本的釋放是進步的源泉,但這還屬于欲望的釋放,缺乏精神的釋放。釋放欲望,就像是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帶來中國經濟活力的同時,也加劇了精神社會的混亂,所以需要通過制度機制上的變革來加以平衡。
中國經濟發展,確實不能再單一追求GDP了,需要反思我們的轉型。中國現在處在工業化轉型期社會危機的前沿,財富分配不均、兩極分化,其結果會“撕裂”社會,加大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從而把中國社會搞得四分五裂。近年來,我們看到了在幼兒園殺害兒童的事件,以及富士康的13跳,還有包括多處政府機關發生爆炸等在內的一系列非常極端的事件。這些已經不是冤有頭債有主的報復,而是針對整個社會的報復,他們對現有政治秩序、經濟秩序、社會秩序都持否定態度,追求制造反對效果的最大化。
危機往往也是轉機,要破解當下中國經濟、中國社會、中國人心的霧中迷局,需要的還是大智慧、大魄力。對于未來,我們仍需謹慎。
編輯:陳暢鳴 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