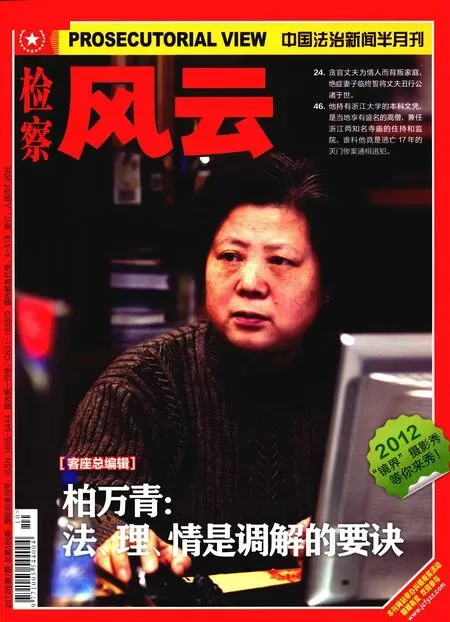“智”解中國轉型困局
文/朱敏
“智”解中國轉型困局
文/朱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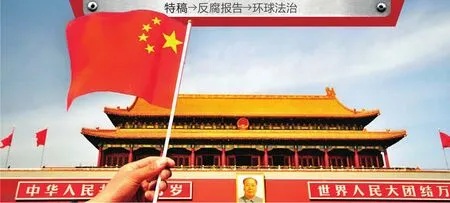
中國之棋局,理應基于學界與民間共識所設。但共識究竟何以最大程度地“凝聚”?這是個涉及反思中國百年轉型、認識中國社會機理的文化制度命題,唯有以“智”迎解。

朱敏
哥倫比亞大學中國企業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經濟導刊執行總編,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著有《中國經濟缺什么》《轉型的邏輯》等。
適逢全國“兩會”期間,又是追問“中國經濟何處去”的時候。何以解局?沒準可從方方正正卻意蘊無窮的漢字中得出一點的啟迪。比如說“智”字,也就是“知”“日”,譯成現代漢語,理應做“洞悉時機”之解。一個人倘若身陷困局,智與不智,全在乎能否審時度勢,相機抉擇,進而化弊為利。可見,智者是真正意義上的識時務者,是不失時機地深化改革者。
近幾年來,全球經濟形勢突逢巨變,隨時局拐點洶涌而來的,是人們對變法之希冀,對改革之訴求。曾經問及經濟學家魏杰“對中國經濟有何預判”,這位清華教授回答得頗具謹慎樂觀意味:中國經濟會有一個新生。言猶未盡,透著知識界對改革契機與時代進步的殷殷翹企。
尊重市場,繼續改革,無疑是中國這個最大的新興經濟體,應對驚濤駭浪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戰略選擇。觀諸眼下,中國之棋局,理應基于學界與民間共識所設。但共識究竟何以最大程度地“凝聚”?這又是個涉及反思中國百年轉型、認識中國社會機理的文化制度命題,唯有以“智”迎解。
人性的復蘇源于對傳統經驗認知的祛魅
任何“共識”,都應以不偏離普世價值為底線。而符合基本人性、社會經濟內在邏輯的價值理念,又都具有普遍性和開放性,須有一套與之匹配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的制度和體制,作為其保障。
盡管從歷史進程來看,在一些相對封閉的區域里,比如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占主導的古代中國,往往會由于人為的、非人性化的、基于制度性的強制因素,而使人們內心這種符合基本人性的價值理念受到壓抑或蒙蔽。這種壓抑或蒙蔽,一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則會使身處其中的人們形成根深蒂固的經驗認知和思維慣性,以為受壓抑或蒙蔽的狀態,及其所依托的一些觀念是“合理的”,進而,對“外來的”,也就是來自該封閉區域之外、處于非蒙蔽狀態或啟蒙狀態的這種價值理念,反倒不以為然,甚至有所抵觸。但是,我們非但無法因此否認這種價值理念的普遍性,反而,應該說,對傳統經驗認知的“祛魅”、對壓抑和蒙蔽這種價值理念的制度進行有效改良,顯得更具重要性,同時更具迫切性。而改良的前提,是文化制度層面的思想啟蒙。
第二件事是熊老夫人提到,以前自己最擔心熊老的脾氣會影響到他和學生的關系。按說熊老對學生可謂“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對于這樣的好老師,學生怎能不感恩圖報呢?但是老夫人深知熊先生和學生們的關系還有另一面,那就是熊老對學生十分嚴厲,不留情面,即便嚴先生成名后依然一如往昔,往往讓已經成名的弟子在熊家的客廳里惴惴不安。要說被揭了面子心生惱怒的時候也不是沒有。時間久了,夫人不免在背后想,嚴先生他們對熊老是敬多一點,還是畏多一點呢?問熊老,熊老卻微笑不語。1969年熊老去世,嚴濟慈先生立即趕到中關村,不顧政治上的風險,在熊老靈前痛哭哀悼,老夫人才理解熊老對自己的學生,有著怎樣的信任和了解。
然而,在中國,至今在最深層的理念上的啟蒙,遠未真正完成。
中國歷史上并不缺思想家,不過,不得不承認的是,真正領先性、創造性的思想,似乎集中于先秦時代,而自秦漢“大一統”、“獨尊儒術”以降則鮮有獨創者,多是由“圣人”為“萬民”設計的倫理規范,以及“被規范”之下的人們轉而投入的“奇技淫巧”。由于統治思想中缺少基于普遍人性的價值理念,就更遑論真正促進創新、保障創新的激勵機制了。“三綱五常”、“皇權至上”等系統化的倫理規范,通過自上而下地強制推廣,成為中國帝制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也淪為“王道”、“霸道”的馭人之術,極大地遏制了商業發展和科技創新。
正因缺失基于普遍人性的價值基礎,浩蕩兩千年的中國歷史,才長期成為一部以王侯將相為主角、“你方登罷我上場”的改朝換代史,人人盼“明主”而不知有“民主”。
直至近代,東西方文明交鋒之后,中國被迫門戶洞開。從而,中國發現自身在科技和軍事上已大為落后,殊不知,其本質是制度和觀念的落后,故采取最實用的“拿來主義”,本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初衷,開啟洋務運動,卻因對舊意識形態抱殘守缺,所謂“祖宗之法不可變”,從而使這場改良止步于“器物”層面。這種“中體西用”、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思維,終究未能扭轉晚清頹勢,帝國大廈傾塌于辛亥炮火之中。
時不與我。20世紀的中國,在救亡與內戰的反復交織中,學習西方工業技術、思想、制度的近代化進程(實質是“現代性轉換”),逐漸偏離辛亥樹立的共和精神,乃至演化為一場確立意識形態的革命史……
國民精神現狀之由:啟蒙中斷與被扭曲的心靈
近年來,國內由經濟社會問題引發的論爭、乃至批判之聲,不絕于耳。比如,涉及發展戰略層面,就有著不同的論調,其中不乏對外向型發展模式的質疑,對市場經濟的批判,對工業化、城市化的反思,對所謂西方“陰謀論”的警惕……不一而足。究其本質,不外乎民族主義對全球化的“抗爭”,或曰“左”“右”之爭,與上世紀初“五四”運動后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頗為近似。這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歷史的延續。二者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從“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語可知,“問題”與“主義”本身并非二元對立。吊詭的是,近代中國最終上演了“救亡壓倒啟蒙”的戲劇性一幕。其后,因循“蘇聯模式”而建立的政治經濟體系,乃至政治動員之下愈演愈烈的全民運動,更是徹底中斷了思想啟蒙的進程。文革后,由于既不能直陳“主義”本身存在的謬誤,也無法置國計民生的“問題”于不顧,在兩難境地下,發起真理標準大討論。這種暫時擱置爭論、邊解決問題邊找尋主義的政治智慧,既為發展與探索贏得了寶貴時間,也為塵封的思想啟蒙,打開了一扇窗。
隨后開始了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領域進行的市場化改革,不啻是對不堪回首的極端理想主義所釀災難的修復。市場經濟制度,是通過改革國有企業、發展外向經濟、放開中小企業、建立資本市場、健全法治體系等逐步確立起來的,在此過程中,隨著對外開放及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自由平等、公平正義、憲政民主、有限政府等價值觀念,越發深入人心。
換言之,當下種種亂象,歸根結底,是出自制度性強制所扭曲的心靈之亂。比如,契約精神本是市場經濟的靈魂,但今日中國,經濟社會卻遭遇了誠信短板與信仰危機。近幾年,我們在戰略層面上一直擔憂的糧食安全問題沒有出現,但食品安全卻成了人人自危的社會問題: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火腿腸里加瘦肉精,還有令人發指的地溝油…… 諸如此類問題,所折射出的不僅是監管缺失、企業家社會責任缺失,也不僅是奶農、養殖戶的見利忘義,而是整個社會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
對國民精神狀態來說,最大的困擾,亦莫過于信仰的黯淡或錯位。
誠信和信仰,已成當今國人的短板,這雖是相當痛心疾首的事實,但至今并沒能形成一個基于共識的“解決方案”。唯一的出路,恐怕在于:看清原則、找準方向的基礎之上,從中國的現實出發,找到一種能為各方普遍接受的價值理念,用這種價值理念去意識形態化,并以此為基,進行政治體制的深層變革。但現下,意識形態領域所呈現“一元統治,兩極對立”的非兼容狀態,使得形成具有普遍性的價值理念,異常困難。
利益分化、社會結構多元化是市場競爭之果,與此伴生的,是價值觀的多元化。改革開放之初,為緩解發展和穩定之“問題”,只好先不爭論“主義”,此后的官方理念對意識形態的處理愈加模糊,仍是對“不爭論”的延續。按說,動態和諧的多元化結構,必從具有普遍性的價值理念基礎上,較為自然地孕育而出,但隨著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中間階層的日益萎縮,食利階層對社會公正的不斷破壞,逐漸演化出今日“左”“右”對立的兩極化,與官方主張的一元意識形態愈發無法兼容。
于“左”而言,早已脫離現實的極端理想主義,不過是改革者利用其話語權,預先設定的一種經過理論上演繹推理、但實質上只服務于少數權貴階層的真實謊言,他們失望于經濟體制改革產生的負效應,并寄望于用曾經的理想主義,揭穿今天的偽理想主義;
對“右”來說,不變革政治體制、僅復制經濟體制的新版“中體西用”,同樣只是一個服務于權貴階層的陷阱,他們悲哀于自己成為上一輪改革產生負效應的代罪羔羊,并寄望于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來進一步證明經濟體制改革的正確性;
而對執政黨和政府而言,即使理想主義意識形態事實上已被虛化,但面對“左”“右”兩派的同時詰難,出于維護執政地位之本能,在“左”“右”之間作出任何選擇,都將是冒天下奇險。因此,只能繼續通過實施制度性強制,來填充意識形態的空洞,不斷擴充早已臃腫的隊伍,進而維護意識形態在“量”上的優勢地位……
但在這種意識形態非兼容結構中,存在一個非常隱蔽、卻常常被忽視的食利階層。他們非“左”非“右”,雖早已背棄理想主義,卻或化身為“左”來攻擊社會不公,或喬裝成“右”為改革辯護,或干脆以公權力自居、以穩定為名對意識形態采取“不爭論”態度,從而,通過在“左”“右”之爭中“和稀泥”漁利。今天,造成意識形態非兼容問題、阻礙普遍性價值理念形成的,正是從官商結合模式和政府競爭模式中不斷獲利的權貴資本集團,其所依托的正是基于行政權力越過邊界、對市場和民眾施予的制度性強制。(詳見《檢察風云》2012年第5期本欄《“穩中求進”的詩外功夫》)
身處歷史的拐點新一輪價值啟蒙的前夜
面對諸種困局,改變政治層面基于制度性強制、經濟層面基于自愿協商、社會層面則是強制與自愿并存的“非兼容結構”,朝著經濟、社會、政治全面基于自愿、協商的“動態和諧結構”轉型,走上真正的現代強國富民之路,漸成高層與社會各界所追求并渴望達成的共識。
在此過程之中,圍繞如何轉型而展開的爭論,又逐漸演化為“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翻版。
歷史上的“問題與主義”之爭,起初雙方對待民主與科學等基本理念,并無明顯分歧,只是在涉及改良與革命的路徑選擇后始現分野。今天的“左”“右”之爭,雙方對非兼容結構的表象,在認知上也無分別,但對造成這種非兼容結構的根源,其判斷卻截然不同,與之對應的路徑選擇,更是水火不容。
誠然,在“左”“右”兩種思潮交鋒下折衷產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曾一度被譽為理論上的偉大創新,并被視為中國摘取“世界工廠”桂冠的頭號功臣。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特色 + 社會主義 +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在政治、社會、經濟上的非兼容結構,而越發令“左”“右”為難——經濟社會領域深層次矛盾的逐漸顯露,究竟意味著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破壞了社會公平,還是意味著一元化模式阻礙了社會進步?究竟是重拾極端理想主義,再來一次改造社會結構的革命運動,還是順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而變革體制?
綜合中國百年歷史與現實來看,對轉型實質的認識分歧,以及與之對應的路徑選擇,正是近代以來“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核心來源,也是新一輪“左”“右”之爭的關鍵所在。我認為,路徑選擇的價值判斷,亟須破除“以成敗論英雄”、“以成敗論歷史”的實證思維定勢,而應關鍵看所選路徑本身,是否符合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邏輯與普遍人性內在需求的一致性。
無論是宗教統治的蒙昧時代,還是權力獨裁的封建時代,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強制性,無不阻礙著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正如盧梭在兩個多世紀前所說:“人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姑且不論共產主義可否成為人類絕對自由的終極形態,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一元化(作為手段的“結構社會主義”),又豈能成為通往自由平等(作為目標的“功能社會主義”)之路?在邏輯上,這顯然是難以自洽,甚至自相矛盾的。類似“以階級斗爭為綱”、“兩個凡是”等基于制度性強制的一元論,及其主導下的社會情境,已不堪回首;與此同時,自由競爭、憲政民主、現代法治等符合人性價值的基本原則,為經濟社會的動態穩定發展與財富持續創造“保駕護航”,從而在世界范圍內被普遍確立。
倘若說,不談常識,空談主義,確是清談誤國;那么,避談常識,或先給常識貼上意識形態標簽,再高舉極端理想主義大旗,則很容易成為玷污理想主義的借尸還魂。今日“左”“右”之爭,僅僅是新一輪價值啟蒙的前夜,尚未上升到路徑選擇的技術方法層面。唯有基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邏輯與內在需求的常識性啟蒙,方能讓人類歷史已經走過的彎路不再重復,讓爭鳴通過啟蒙,回歸到常識框架內。
變革的實施,有賴于思想的啟蒙、共識的凝聚。這令我想起馬立誠先生贈我的一部大作。他這本書寫的是“中國歷朝改革變法實錄”,名曰《歷史的拐點》。書委實不錯,作為無法割裂的歷史延續,當代中國改革大業與先行者們的諸多改革不論是發動時機、戰略選擇,還是機會把握、推進難點,乃至變革哲學等諸方面,都能從中觀照出對應的因子。該書不光對歷史的梳理使人耳目一新,對成敗的拷問亦可謂振聾發聵。在封面上,印有幾行醒目的話:
“中國傳統歷史上有個謎團:十幾次改朝換代獲得了成功,而十幾次大的改革卻大都失敗了,以至于有人說國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卻拙于制度創新,真的是這樣嗎?”
編輯:陳暢鳴 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