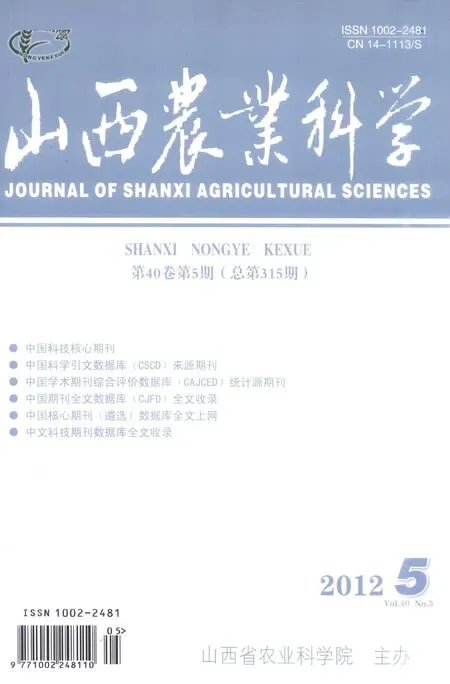城郊區農村土地流轉調查:以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為例
殷海善,秦作霞,辛有德,胡愛秀
(1.山西省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經濟研究所,山西太原030006;2.晉中市榆次區郭家堡鄉,山西晉中030600)
當前,農村家庭承包土地的流轉已經成為農村經濟生活的重要現象,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以一省一縣整體行政區作為研究對象的比較常見,而以具有共同流轉特征的村莊作研究對象的比較少見。不同的村莊由于各自的自然條件、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不同,從而使土地流轉呈現不同的特征,因此,以村莊作為研究對象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城郊區受到城市經濟的輻射,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同于盆地和偏遠丘陵區,其土地流轉具有獨特性。對城郊區農村家庭承包土地經營權流轉開展研究,有利于對農村家庭承包土地流轉的全面認識。筆者以問卷調查、訪談調查,對山西省中部一個中等城市的郊區農村開展研究。
1 調查村莊的基本情況
晉中市是山西省一個地級市。榆次城區是山西省晉中市的首府,是一個擁有40萬人口、建成區約40 km2的中等城市。榆次區現管轄行政村272個,農戶7.94萬戶,耕地面積3.78×104hm2。其中,郭家堡鄉地處城鄉結合部,占地面積為80.4 km2,轄有17個行政村,現有4.34萬人。
郭家堡鄉城市化程度較高,全鄉65%的面積處于城區范圍,85%的國土納入城區規劃范圍,大多數村莊不同程度地融入城區,成為典型的“城市里的村莊”。該鄉工業經濟發達,擁有鄉鎮企業379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9 700余元,遠高于山西省農民年人均純收入4 300元的平均水平。
城市化程度高、工業經濟發達是城郊區農村不同于偏遠山區、盆地區傳統農業區的2個特點。調查范圍為5個村莊,其中,甲村為城中村,乙村和丙村為工業園區附近村莊,丁村和戊村為距離市區較遠的純農業村莊。從地形地貌來看,戊村為丘陵區,其余村莊為平川。調查方法:承包人、年齡、承包耕地面積以會計登記為準,土地流轉面積、現流轉經營人、雙方的社會關系以座談方式取得。調查樣本為每村會計登記的前80~100戶,流轉發生指1997年第2輪承包以來承包經營戶戶主發生的改變。調查時間為2011年。各村的人口、耕地面積、區位情況列于表1。

表1 郭家堡鄉5個村2010年基本情況
2 土地流轉情況與特點
2.1 土地流轉數量偏少
由表2可知,城郊區5個村參與土地流轉的耕地面積占全村耕地面積的13.15%,轉出耕地的農戶占全村農戶總數的16.38%,這個流轉比例低于山西省其他縣的調查結果,如右玉縣土地流轉發生率在30%以上[1],說明在城郊區農村土地流轉不如典型農區頻繁。

表2 調查村莊土地流轉情況
2.2 土地流轉主要在親屬之間,以繼承為主
土地流轉過程中,原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與現土地使用權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表現為父(母)子(女)關系、兄弟關系以及叔侄、姑侄等親屬關系和僅為村民、鄰里、朋友的非親屬關系2類。
從表3可以看出,城郊區土地流轉關系突出表現為雙方具有密切的親屬關系,甚至土地流轉主要是在父母與子女之間進行,即土地流轉表現為明顯的繼承性。而且,距離城區越近,土地流轉在親屬之間發生的比例越高。這表明,在城郊區,土地流轉不是純粹的經濟行為,而是表現為摻和了鄉村血緣關系和熟人關系特征的社會行為。
根據《土地承包法》和相關文件,土地流轉形式包括轉讓、轉包、入股和互換等幾種,其中,土地轉包是當前土地流轉的主要類型[2],繼承本不是《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規明文規定的土地流轉形式。本研究僅把繼承作為土地流轉事實上的一種形式。在調查的城郊區村莊,常見的轉包、轉讓、入股、合作社等非常少見,互換僅在丘陵區村莊戊村存在,絕大多數村莊的土地流轉以繼承為主,在親屬之間流轉。

表3 土地流轉雙方社會關系情況
2.3 土地流轉以無償為主
因為土地流轉發生在親屬之間,是無償的,土地使用者不需要支付貨幣代價,原土地承包經營者沒有獲得土地流轉收入。土地流轉出讓方基本沒有或者只有較少的土地流轉收益,是榆次區農村土地流轉的常態[3],這與土地流轉政策和文件強調土地要有償流轉不一致。
土地無償流轉大體有幾種原因:(1)農村土地流轉雙方為具有血緣關系的親屬,土地流轉存在親屬之間相互幫扶,不完全是一種經濟行為。(2)由于土地流轉發生數量少,沒有形成土地流轉市場和土地流轉價格。即使有個別農戶在非親屬之間流轉土地,也不一定支付土地流轉金。在丙村,見到1戶山東省移民,因沒有親屬,所以將土地無償流轉給1戶村民。(3)土地經營權人可以得到農業補貼和土地征地補償,土地不能荒廢是廣大農民的普遍認識,讓其他人耕種有照看土地的意思,得到農業報酬是照看者的權力,因此,照看者不需要支付土地流轉金。(4)由于當地村民非農就業普遍,已經形成公開的勞動力市場與價格,村民普遍認識到獲得農業生產收益是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合理回報,而不是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收入。
3 土地流轉的影響因素
3.1 征地補償和農業補貼強化了村民重視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意識
目前,我國正進入快速城鎮化階段,土地征用是城郊區的常見現象。調查的5個村莊土地征用數量很多(表4),如已經融入城市的甲村,公園建設、部隊占用、城市道路等非農用地較多;如距離城市較遠的乙村和丙村主要是工業園區占地;而丁村和戊村主要是環城道路占地。城鎮化帶來的土地征占對郊區農村和農民影響巨大,最明顯的表現為土地征占使相關農民獲得了一筆巨額的征地補償收入。如城區修建環城路征用某村土地的補償為120萬元/hm2。這是村民從土地經營權上獲得的一筆財產性收入,不需付出任何成本。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城郊區將迎來城鎮建設的新高潮,土地征用補償將會更加明顯地影響農民的土地利用行為。
土地經營權人獲得的第1筆財產性收入是農業補貼,包括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在實際運作過程中,農業補貼的發放對象是擁有一定耕地面積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而不是流轉后的土地使用權人。2010年,晉中市玉米的農業補貼為每公頃915元,一戶擁有0.3 hm2耕地能夠獲得300元農業補貼收入。因為有農業補貼,有的村莊在2005年以前流轉出去的土地又被土地承包經營人要回來,因此,還發生了土地流轉糾紛事件[4]。

表4 調查村莊農戶的征地情況
由于征地補償和農業補貼,使得土地具有了財產性質。而且征地補償標準和農業補貼標準呈現逐年升高的趨勢,土地的財產價值持續升高,城郊區農民普遍重視土地經營權,不會輕易放棄土地,土地流轉比較困難。
3.2 玉米機械化生產減少了農業的勞動投入
山西省曾經實施過“玉米戰略”,城郊區多數村莊以種植玉米為主。調查表明,在灌溉條件下,玉米產量一般為11 250 kg/hm2,個別養殖戶因有大量農家肥,玉米產量可以達到15 000 kg/hm2,生產成本在6 000元/hm2左右,玉米價格約為2.0元/kg,純收益不低于15 000元/hm2。每戶0.3 hm2耕地,純收入在5 000元以上。這是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效益。
玉米生產以機械化為主,勞動投入很少。城郊區土地平坦,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水平很高。耕地、播種甚至收獲,已經實現機械化生產,而且是社會化的機械生產。所謂社會化的機械作業是指農業機械服務是通過市場提供的,而不是由家庭購買農機具提供的[5]。城郊區村民雖名為農民,但不需要擁有農業機械,不需要親自下地,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投入也越來越少。便捷的社會化機械服務使得農戶在缺乏青壯年勞動力的情況下,也能夠組織生產,從而在家庭主要勞動力實行非農就業的情況下也沒必要把土地流轉出去。
3.3 勞動力就近轉移和交通便捷,使得外出勞動者極易返家
城郊區非農就業機會較多,可以在市區就業,可以在工業園區和附近企業就業,還可以在20 km外的大城市就業,村莊的青壯年勞動力基本實現了非農就業。多數年輕人非農就業的月收入為2 000元左右,這樣的收入能夠讓村民過上有保障的穩定生活。同時,由于國家對農村道路建設的長期支持,農村的交通四通八達,在以電動自行車、摩托車和汽車為代步工具的情況下,返鄉時間不到半小時。這使得外出勞動力農忙時能夠及時返家支持農業生產,不影響農事。
3.4 土地種植樹苗,減少了勞動投入
為了獲得更多的土地征用補償,城郊區村莊出現了一種適應征地的“樹苗”作物,即農民不種玉米種樹苗,樹苗種類為紅棗、蘋果、梨等。一般經營性的樹苗,種植密度約為900株/hm2,而為征地種植的樹苗,密度達到15 000株/hm2以上。樹苗種植以后不需要進行田間管理,村民以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政府來征地。按照土地征用規定,土地經營者可以獲得青苗補償費。如果種植玉米,青苗補償費為15 000~30 000元/hm2;如果是紅棗、蘋果、梨的話,1棵樹在100元以上,1 000棵樹苗的青苗補償費在10萬元以上。一般情況是離市區和工業園區越近的村莊,征地樹苗越多。最典型的是已經融合到市區的城中村甲村,按村民的說法,99%的耕地成為樹苗地。而且,種樹苗這一致富信息傳播很快,有征地可能的村莊,征地樹苗發展很快。種植樹苗使得土地數年內事實上退出了農業生產,是耕地資源的隱形浪費。
4 探索城郊區土地流轉的方式
4.1 城郊區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是社會發展的趨勢
綜上所述,城郊區農民的收入以租房、經商、打工為主,農業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因此,重視土地、輕視農業是城郊區村民的一般心態。同時,城郊區土地非農占用是普遍情況,征地后農民家庭承包土地面積減少,承包土地作為一個生產單元的價值已經顯著降低,使得農業生產不能合理經營。例如,已經成為城中村的甲村,52.0%的家庭因為征地完全失去土地,11.0%的家庭擁有耕地的數量低于666.67 m2;工業園區占地的乙村,12.2%的家庭因為征地完全失去土地,56.7%的家庭擁有耕地數量低于666.67 m2。另外,城郊區地勢平坦,實現土地規模化的自然條件存在。為了防止土地棄耕或變相棄耕,充分發揮土地的生產資料價值,土地規模化、經營專業化成為城郊區農業生產的重要課題。
4.2 探索城郊區土地流轉的模式
一般來說,農民非農就業和市民化是土地流轉的前提,不依靠土地生活的農村,土地流轉較多[6]。然而在城郊區,由于土地征地補償導致土地財產化,農民不會輕易放棄對土地經營權的控制。試圖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來實現城郊區土地經營的規模化,或許是徒勞的。
城郊區的土地流轉,必須考慮到農民對土地財產權的要求。可以嘗試在村民保留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前提下,將土地以委托、股份等方式交給村集體、村民合作社來統一經營[7];或者鼓勵一部分愿意從事農業生產的壯年勞動者,以村民之間能夠接受的方式流轉土地發展生產大戶,實現規模化生產;或者在保留土地承包經營權和農戶經營的前提下,促進生產環節的社會化生產,如丁村由村集體統一服務農田灌溉和秋耕作業。有經濟實力和組織能力的村莊,村集體應積極組織代耕隊,承擔不愿意、不積極耕種農民的農田作業,發揮土地的生產功能。這種方式能夠充分尊重承包經營人的權利,又能夠實現土地的生產目的,是一種村民能夠接受的方式。但是,目前多數村集體缺乏經濟實力,建議國家對村集體和村民合作社規模經營給予政策以及資金支持,促進城郊區農業生產正常化和經營規模化的發展。
[1]殷海善,趙鵬.右玉縣家庭承包土地流轉調查[J].山西農業科學,2011,39(1):84-87.
[2]殷海善,周振華,楊晨,等.山西省農村家庭承包土地流轉研究[J].山西農業大學學報,2010,9(2):140-143.
[3]牛永珍.農村土地流轉問題及對策研究:以晉中市榆次區為例[J].山西農經,2010(3):9-13.
[4]史紅,侯興瓊.淺淡晉中市土地流轉[J].山西農經,2010(1):47-50.
[5]張冰,殷海善,劉宏柄.試論農民家庭小規模經營情況下農業現代化發展探討[J].山西農業科學,2010,38(3):287-290.
[6]唐福勇.貧富地區土地流轉差異大 [N].中國經濟時報,2002-05-21.
[7]李曉明,郭丹.黃土地迸發新活力:關于榆次區北田鎮朱村土地流轉的調查[N].山西日報,2009-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