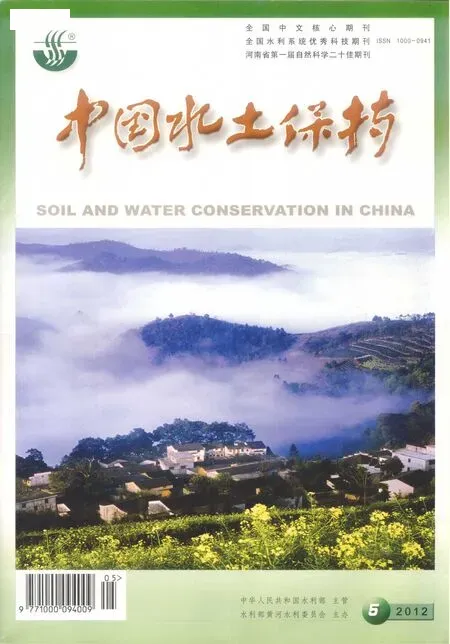聚丙烯酰胺促進沙化退化草場植被恢復效果研究
褚麗妹,葛 巖,惠靜夷,趙國蘋,呂子超,凡久彬
(1.遼寧省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遼寧沈陽110003;2.遼寧省國土資源調查規劃局,遼寧沈陽110032;3.沈陽市環境保護局渾南新區分局,遼寧沈陽110015;4.遼寧江河水利水電新技術設計研究院,遼寧沈陽110003)
東北黑土區農牧交錯帶由于其特殊的地貌格局、氣候條件和脆弱的地表物質基礎以及不合理的人類利用,草場沙化退化日益加劇。據統計,我國的草原平均每年以80萬hm2的速度在退化。內蒙古可利用天然草場退化面積已達60.8%,通遼市草場退化面積達44.0%[1-3]。在此趨勢下,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程度地實現農牧交錯帶沙化退化草場的植被恢復與重建,已成為保障我國生態安全和糧食安全的一個重要問題。作為土壤結構改良劑,高分子聚合物聚丙烯酰胺(PAM)具有增加土壤表層顆粒間的凝聚力、維系良好的土壤結構、防止土壤結皮、增加土壤入滲、減少地表徑流、防止土壤流失以及抑制土壤水分蒸發等作用[4-10],因此其在水土保持領域的應用也逐漸被人們所關注。將PAM用于沙化退化草場植被恢復與重建是切實可行而又前景廣闊的嘗試與探索。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區概況
試驗區位于內蒙古通遼市扎魯特旗北部的山地牧場,地處查干毛日小流域,屬東北黑土區農牧交錯帶山地草原區。長期以來,自然因素和人類對草場的不合理利用,導致該地區水土流失嚴重,草場退化、沙化,草原生態環境極度惡化[2]。
1.2 供試材料
PAM是具有超強吸水功能的高分子化合物,帶有眾多高度親水功能基團。研究所采用的是陰離子型、分子量在300萬~400萬之間的PAM,白色粉末狀。
1.3 試驗設計與分析方法
在圍封治理區域內布設小區,通過施用PAM改良沙化草場土壤,加速植被恢復。試驗為二因素完全隨機試驗,設A和B兩個因素:A因素為不同PAM劑量,設5個水平,分別為0(對照,A0)、30 kg/hm2(A1)、75 kg/hm2(A2)、120 kg/hm2(A3)、165 kg/hm2(A4);B因素為不同植被類型,設3個水平,分別為人工栽植檸條(B1)、人工撒播沙打旺(B2)、天然植被(B3)。按兩因素交叉分組布設15個小區,小區規格為40 m×15 m,設置在坡度為6°的均勻平緩坡面上,隨機排列。試驗觀測全部在封育期內進行,封育期為3年。每個小區設6個1 m×1 m的樣方,每個生長季及秋末測定草場植被生物學性狀及物種組成的變化。
2 結果與分析
2.1 植被高度的變化
試驗過程中分別測定了PAM對人工栽植檸條、沙打旺以及三種植被恢復區內所有牧草平均株高的影響,結果見圖1、2。

圖1 人工栽植牧草株高狀況
由圖1可以看出,隨著PAM劑量的增加,檸條及沙打旺株高大體上呈現先增后減的趨勢。當施用的PAM達到120 kg/hm2時,株高均達到最大值,此時人工栽植檸條株高比其對照高23.3%,人工撒播沙打旺株高比其對照高30.9%。從圖2中可以看出,不同植被恢復區所有牧草的平均株高大體上呈現出了相同的變化趨勢,當PAM劑量達到120 kg/hm2時,各植被恢復區所有牧草的平均株高均達到最大值。120 kg/hm2劑量PAM處理的檸條恢復區、沙打旺恢復區、天然植被恢復區所有牧草平均株高分別比其對照高72.3%、28.7%和64.9%。

圖2 各處理所有植被平均株高狀況
由表1方差分析結果可見,不同植被類型恢復區間植被平均株高呈極顯著差異,不同PAM劑量間植被平均株高呈顯著差異。表2和表3新復極差多重比較結果表明,不同PAM劑量間差異不顯著,但均與對照呈顯著差異。檸條恢復區與沙打旺恢復區差異顯著,二者與天然植被均呈極顯著差異。

表1 植被平均株高方差分析結果

表2 不同PAM劑量間株高多重比較

表3 不同植被類型間株高多重比較
2.2 植被蓋度的變化
施用PAM對草場植被蓋度的影響見圖3。從圖3可以看出:除天然植被75 kg/hm2劑量處理植被蓋度略低于30 kg/hm2處理外,其余各處理植被蓋度均隨著PAM劑量的增加呈現出先增后減的趨勢;當PAM劑量達到120 kg/hm2時,三種植被恢復區植被蓋度均達到最大值,此時檸條恢復區植被蓋度比其對照高20.0百分點,沙打旺恢復區比其對照高24.3百分點,天然植被恢復區比其對照高25.0百分點。

圖3 聚丙烯酰胺對植被蓋度的影響
表4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植被類型恢復區間植被蓋度差異呈顯著水平,不同PAM劑量間植被蓋度差異呈極顯著水平。表5和表6多重比較結果表明,檸條恢復區與沙打旺恢復區間植被蓋度差異不顯著,但這兩個植被類型與天然植被恢復區間植被蓋度差異顯著;PAM施用劑量在120 kg/hm2時的植被蓋度與30 kg/hm2時及對照的差異極顯著,說明劑量在120 kg/hm2時對植被蓋度的促進作用最強。

表4 植被蓋度方差分析結果

表5 不同PAM劑量間植被蓋度多重比較

表6 不同植被類型間植被蓋度多重比較
2.3 草場生物量的變化
不同劑量水平對草場生物量(干物質)的影響見圖4。結果表明:①各處理施用PAM后均有效地提高了草場生物量,且草場生物量隨著PAM劑量的增加先增后減,當PAM劑量達到120 kg/hm2時,各處理草場生物量增幅最大,其中檸條恢復區草場生物量增加43.18%,沙打旺恢復區草場生物量增加72.23%,天然植被恢復區草場生物量增加70.68%。②沙打旺恢復區的各個小區生物量好于另外兩種植被。沙打旺各處理的草場生物量平均比天然植被高6.8%~25.3%。

圖4 聚丙烯酰胺對草場生物量的影響
表7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植被類型恢復區間生物量差異顯著,不同PAM劑量間生物量差異極顯著。表8、表9多重比較結果表明,不同植被類型間,沙打旺與天然植被、檸條間差異顯著,天然植被與檸條間差異不顯著;不同PAM劑量間,120、165、75 kg/hm2間差異不顯著,它們均與30 kg/hm2差異顯著,且施用PAM的各處理牧草生物量均與對照呈極顯著差異。

表7 牧草生物量方差分析結果

表8 不同PAM劑量間牧草生物量多重比較

表9 不同植被類型間牧草生物量多重比較
2.4 草場物種多樣性的變化
2.4.1 草場植物種類的變化
草場植物種類變化情況見表10。從植物種數上來看,檸條恢復區對照處理第二年植物種數比第一年減少了3種,施用PAM的各處理植物種數增加了1~4種;沙打旺恢復區對照處理植物種數減少了4種,30 kg/hm2處理增加2種,75、120及165 kg/hm2處理植物種數減少了1~2種,種數減少幅度均小于對照;天然植被恢復區,對照處理種數減少了1種,其余各施用PAM的處理植物種數增加了1~4種。

表10 草場植物種數的變化 種
在圍封治理期限內,不同植被類型恢復區植物物種組成均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檸條恢復區出現了一些新的菊科、莎草科、十字花科以及豆科植物(全葉馬蘭、苔草、水田芥、黃芪、苦參等),部分菊科植物得以恢復(薄雪、鐵桿蒿等),禾本科隱子草及豆科胡枝子等牧草逐漸成為優勢種和建群種,小畫眉、馬唐等物種有所消退;沙打旺恢復區由于人為干預作用,所以沙打旺的優勢性在后一年度表現得較為突出,同時也增加了一些豆科、莎草科、菊科和毛茛科物種(黃芪、苔草、全葉馬蘭、鐵線蓮),胡枝子有所恢復,小畫眉、馬唐等物種消退;天然植被恢復區出現了一些莎草科、十字花科、菊科物種(苔草、垂果南芥、全葉馬蘭等),隱子草、大葉胡枝子、細葉胡枝子、冰草、石竹等禾本科、豆科及石竹科物種在種群中的優勢逐漸增大,小畫眉消退。總的來講,在封育期限內,一二年生植物侵入,群落物種豐富度增加,退化群落中的建群種、優勢種得以優先恢復。
2.4.2 生物多樣性指數的變化
為了反映草場施用PAM后不同處理間群落中的物種豐富度和個體在物種中的分布均勻程度,在調查種群的高度、密度和物種數量的基礎上進行了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SW)和以此為基礎的均勻度(JSW)的測度,結果見表11。

表11 不同處理植物多樣性變化
表11表明,治理期末檸條和天然植被恢復區PAM施用劑量在75 kg/hm2時物種多樣性指數及均勻度指數都高于其余各處理;沙打旺恢復區施用30和120 kg/hm2劑量時物種多樣性指數較高,30 kg/hm2劑量時物種均勻度指數較高。總的來講,天然植被恢復區物種多樣性及均勻度都好于檸條和沙打旺恢復區。對各處理SW進行方差分析,發現不同PAM劑量間SW差異不顯著,不同植被類型恢復區間差異顯著。經過新復極差多重比較,得到檸條恢復區與沙打旺恢復區間SW差異不顯著,而天然植被恢復區與二者之間差異呈顯著水平。不同PAM劑量間JSW差異同樣不顯著,但不同植被類型之間差異呈極顯著水平,此差異同樣是由于天然植被恢復區與另外兩種植被恢復區間的極顯著差異所致。
通過年際間變化分析可知,經過兩年封禁治理,除沙打旺對照處理多樣性指數和群落均勻度指數略有下降外,其余各處理多樣性指數和均勻度指數均有所增加,而且施用PAM比不施用PAM的多樣性與均勻度指數增加的幅度要大,但不同劑量間的差異并不顯著。
3 結語
(1)在有效劑量范圍內,聚丙烯酰胺能夠有效地促進植被的生長,加速沙化退化草場植被的恢復。當聚丙烯酰胺劑量達到120 kg/hm2時,草場植被恢復效果最為突出。
(2)在最佳劑量水平下(120 kg/hm2),與一般生態修復區相比,檸條、沙打旺和天然植被恢復區植被蓋度分別比對照高20.0、24.3和25.0百分點,牧草平均株高分別比對照提高了72.3%、28.7%和 64.9%,植被生物量分別比對照提高了43.2%、72.2%和 70.7%。
(3)聚丙烯酰胺能夠減緩退化草場植物種類的減少,甚至可促進其植物種類的增加。治理期間草場生物多樣性、均勻度都明顯增加。檸條恢復區生物多樣性指數增加了9%~26%,均勻度指數增加了7%~72%;沙打旺恢復區分別增加了1%~13%和12%~63%;天然植被恢復區分別增加了1%~44%和12%~63%。
[1]張生軍,楊改河,劉和林.北方農牧交錯帶水資源與生態環境問題初探[J].安徽農業科學,2006,34(9):1945 -1947.
[2]張漢雄,邵明安,張興昌.東北農牧交錯帶生態環境恢復與持續發展戰略[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4,18(1):129-134.
[3]何振強,徐慧,徐秀云.通遼市水土流失成因與防治對策[J].東北水利水電,2001(11):48 -50.
[4]吳學鋒,汪有科,吳普特,等.PAM對土壤物理性狀影響的試驗研究及機理分析[J].水土保持學報,2005,19(2):37-40.
[5]崔海英,任樹海.應用聚丙烯酰胺防治水土流失的研究現狀[J].水土保持科技情報,2005(2):25-27.
[6]夏海江,肇普興.聚丙烯酰胺對土壤物理性質的影響[J].水土保持研究,1997,4(4):81 -88.
[7]于健,雷廷武,Shainberg I,等.不同PAM施用方法對土壤入滲和侵蝕的影響[J].農業工程學報,2010,26(7):38 -44.
[8]楊永輝,武繼承,趙世偉,等.PAM的土壤保水性能研究[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25(12):120-124.
[9]李晶晶,白崗栓.聚丙烯酰胺的水土保持機制及研究進展[J].中國水土保持科學,2011,9(5):115 -120.
[10]李佳佳,李俊穎,王定勇.PAM對沙質土壤持水性能影響的模擬研究[J].西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32(3):9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