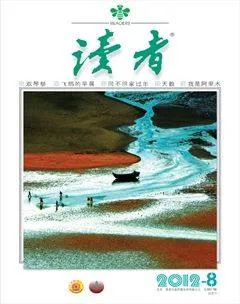回不回家過年
劉炎迅

過年回家,這是一個無需討論的選擇。
套用一下時下風靡的句子:當我們談論回家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
我們曾經談論的是團聚、年夜飯、鞭炮和“春晚”。而如今,這一切都變了。我們首先必須談論的是“春運”。這個中國特有的詞匯已經成為糾結的同義語。它變成當下過年回家路上的一道屏障。
跨越第一道屏障,當我們歷經艱難終于抵達故鄉的時候,突然發現,眼前的村鎮與記憶中的故鄉相去甚遠,“家”已經面目模糊。衰弱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等著歸人,而已經適應大城市的人們由此覺得故鄉越顯凋敝。
而當我們再進一步走入家門,與那些留守的親人團聚的時候,又不得不面對在這個大變革時代中人際關系的疏離。疏于來往的親戚間浮于表面的寒暄,從各地回鄉的人之間暗含機鋒的攀比,原本熱望的團圓場景都被淹沒在一場場雷同且漫長的宴會中。金錢和禮物最終變為回鄉者更大的負擔。
回家的路途上,似乎有著越來越多的阻礙。回家已經變得需要思量。
鄉關不再
梁鴻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后,她在2008年和2009年,用近5個月的時間深入河南鄉村調查采訪,完成了十幾萬字的紀實性鄉村調查《中國在梁莊》。梁莊是她的故鄉,她曾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
“故鄉是被拋棄的。”梁鴻說。
梁鴻走訪了各地的梁莊青年,想聽聽他們在異鄉的生活感受,但一見面,老鄉之間的話題一下子就落進故鄉里,聊了一天,都是在回憶梁莊的故事,張家長李家短。
在異鄉,談論家鄉成為一個情感按摩的工具。在人們百無聊賴的閑侃中,故鄉一次次被升華,成為具有抽象味道的情感釋放的地方。
但真正讓他們回到故鄉,也不愿意。
“農村現在是沒有吸引力的。我們都在建設大城市,年輕人離開故鄉來到城市,帶著夢想,追求大城市的幸福,他們中很多人期望在大城市定居,過上體面的生活,若干年后,這里會成為自己孩子的故鄉。”梁鴻說。
這樣的愿望要實現卻很難。
梁鴻的一個堂侄在北京打工多年,現在是某大學食堂的員工,一個月3000多元的薪水,在很多梁莊人看來,很不錯了,夠體面的了。
有一次,梁鴻和他吃飯,酒過三巡后,她侄兒有些激動,當梁鴻問他將來有什么打算時,他說,不回故鄉。他解釋說,回故鄉啥事也成不了,日子過著沒勁。
然后他就跑出去給還在梁莊的爺爺打電話,爺爺快90歲了,耳朵背,他就抱著話筒提高嗓門喊話,土里土氣的方言,完全放開音量,在旁人聽起來,像一場曠日持久的爭吵。從屋里跑到屋外,從屋外跑回屋里,電話通了十來分鐘。其實,這次通話,爺爺在那邊幾乎沒有說話,只是不停地嗯啊,間或發出衰老的輕嘆聲,孫子在這頭嘰里咕嚕說了好半天,掛了電話,眼圈都紅了。
“我就想給我爺爺打打電話,我就想聽聽我爺爺的聲音。”他說。
“不回故鄉”背后,其實依舊保留著劇烈的不舍和某種不甘心,“在外面混,大城市里打工掙錢,累,日子過得不易,但不這樣又能怎樣?誰讓故鄉窮,誰讓掙錢的地兒都在大城市里呢?”
我們都沒有了故鄉
專欄作家十年砍柴前不久寫了一本回憶故鄉的書——《進城走了18年》。書的封面上有一段話:“歲月偷走了青春,記憶依舊年輕,離鄉路上的那些風景,是永遠消逝的耕讀文明。”
十年砍柴是湖南人,本名李勇,18歲負笈北上,至今22年。
李勇說,自己大概每年要回一次故鄉,有時還一年回去好幾次。多數并不是春節,而是利用公差順道看看父母。
“我們三兄弟都定居在外省,只有姐姐姐夫一家在老家湖南陪著父母,父母也不愿意離開故土跟著兒子們度過晚年,他們堅信只有終點停在故鄉、停在老宅的人生,才是圓滿的。”
他最近一次回去,是2011年清明,哥哥也回去了,弟弟因為距離更遠沒有回。他們去爺爺、奶奶的墳上掛青——將紙幡插在墳頭上,將墳頭上長了一年的荊棘茅草割干凈。
李勇說:“一提起故鄉,我首先想到的是村門口的一眼井。”他對這口井記憶最深,它不僅是全村20戶人畜最重要的水源,而且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財產,在祠堂、族譜被迫消逝的數十年里,它是維系村里人的精神紐帶。
這口井離他家有30級陡峭的臺階,兄弟姐妹品嘗農家生存之苦,也是從這口井開始。對李勇來說,關于這口井的記憶還和爺爺的死聯系在一起。
讀五年級的時候,爺爺患腦溢血去世了。“我媽和我嬸子按照當地的風俗,拿著紙錢,到井邊點燃,然后大哭。”這叫“買井水”,告知井神,某個人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他不再喝這口井的水,感謝井水滋養了他的一生。
“后來我在想,這種儀式還有一個功能是告知,家逢喪事,不可能一家一戶告知,請幫忙。井邊一哭,這個消息傳出去了……”
李勇每次回去,都會聽父母講哪位爺爺或叔輩又走了,村里熟悉的人越來越少了,那些孩子們,他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認識他。
“他們的父親是和我一起長大的一代人,多數在外打工。”李勇說,整個村落,已不復是一個生態完整、充滿活力的系統,而是殘缺的、停滯的,安靜得可怕。連牛羊的叫聲都少了,童年時最常見的“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的景象很難見到了。
然而最令他感到無法忍受的是,這次回鄉,他發現村口的這眼井也幾乎被廢棄了。
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
在一些地方,比如蘇南,鄉村和縣城都在招商引資中變得工廠林立,當地居民也頗為富裕,年輕人可以在家門口的工廠上班,他們不需要背井離鄉。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能留住故鄉。接受采訪時,很多人感嘆,就算故鄉始終在身邊,也早已變得不一樣——城市大拆大建,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無論鄉村還是城鎮,都急急忙忙地改頭換面。新樓房新街道新超市新的河堤新的橋梁,原本熟悉的地方,反而有些陌生。一位接受采訪的人說:不夸張地說,現在回家,都要帶地圖了。
一位曾到蘇南昆山采訪的記者描述說,當地政府在“提前實現全面小康”的口號下,打算讓村民都住樓房,于是一個個村落被規劃整合成整齊劃一的新式小區,然而那些突然被迫搬進樓房的村民,住進新房的第一件事卻是拆掉煤氣灶,在貼著瓷磚鋪著地板的廚房里砌一座老式鍋灶,然后在墻壁上掏個洞,伸出一截鐵皮制成的煙囪,他們依舊習慣爐火從爐膛舔出來的感覺,那才有生活的意思。他們也會在高高的樓房的窗戶外,照舊例掛上一個竹匾,或者一面鏡子。
故鄉說起來很抽象,其實不過是一個個具體的生活細節,一個能夠讓人想起來覺得溫暖的地方,一個可以包容亦可供成長的環境。然而,多數當代中國人,卻只能悵望鄉關,不可回,無法回,抑或,回去,亦不是故鄉。但是,這一切障礙都只是最終顯示出的微小結果。難購的車票、有點陌生的故鄉、異化的人際關系,這些背后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中國仍然面臨著嚴重的城鄉二元化分割,以及東西部巨大的經濟差異。經濟、文化、醫療、教育等各種資源向一線城市聚集。由此,人們紛紛去北上廣等大城市尋找出路。而進城者的父輩們卻不能或不愿一同遷往城市。所以,一年一度的春節上演著一場場悲壯的長途遷徙。無論對于社會抑或個人,人類史上這樣的奇觀都耗費巨大,讓人們身心俱疲。
需要改變的是中國嚴重的資源配置不平衡。那些中小鄉鎮和城市如果能有更多的機會獲得資源與發展,人們對于自己的工作地就會有更多選擇的可能,不必千里迢迢奔赴少數幾座城市。如此,回鄉路才不會如此艱辛,家庭關系才會得以修補。回家,對我們來說將真的變得溫暖。
(謝林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12年第2期,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