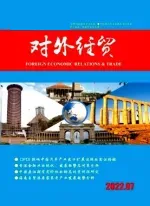國際貿易經常賬戶失衡問題比較研究
徐龍善
(黑龍江大學研究生學院,黑龍江哈爾濱150080)
在全球經濟高速增長期,在主要以出口來促進經濟發展的中國和以減少貿易赤字為目標的美國之間,很多學者將兩國在國際貿易經常賬戶收支不平衡看作是一種雙贏的局面。但在全球經濟表現出衰退的時候,學者們又把中國和德國國際貿易經常賬戶順差問題看作是對全球經濟發展的障礙。

圖1 中德經常項目收支占GDP比例的比較
從圖1可以看出,中國在國際貿易經常賬戶收支方面所走的道路與德國有些類似。在20世紀80年代,德國長期表現為國際貿易收支順差,在80年代中期經常賬戶收支順差占GDP的比例甚至達到過5%,與此同時,中國經歷了國際貿易經常賬戶收支逆差占GDP的比例為4%。德國在90年代期間國際貿易收支達到了基本平衡,部分是由于東西德的結合致使全國財務數據達到平衡。
與此同時,我國的國際貿易經常賬戶收支發生了巨大變化,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達到基本平衡到90年代后期國際貿易經常賬戶收支占GDP的比重達到2%和4%,值得注意的是在21世紀以后,我國和德國在國際貿易經常賬戶收支方面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兩國相繼從90年代初期的2%至2010年超過了10%。一個經濟總量很小的國家在全球的國際收支平衡中所扮演的是微乎其微的角色,國際貿易經常賬戶收支與GDP的比例具有獨立性。中國作為全球各國重要的國際貿易伙伴,在過去的30年已經充分驗證,中國在全球國際收支不平衡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圖2充分表明了我國和德國在全球國際收支方面的重要性。2004年之前,中國對全球國際貿易經常賬戶收支不平衡的影響幾乎為零,但由于在21世紀以后,我國的國際貿易順差迅速擴大,在2007年超過了德國,我國已經取代德國成為了全球貿易的主導者。我國從改革開放初期的經常賬戶國際貿易收支由僅占德國的1/3發展至在21世紀超過了德國。

圖2 中德國際貿易經常項目貿易余額(單位:億美元)
再從區域性看我國與德國在國際收支方面的差異時,我國與德國的情況卻迥然不同。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歐盟的國際貿易經常賬戶收支平均來說接近一個平衡的水平,如果把歐盟看作一個整體,德國的國際收支問題在歐盟內部可以得以消化,歐盟在全球的國際收支平衡中只是起到一個中立的作用,全球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主要是由以出口為導向的東南亞國家包括我國的長期貿易順差和美國長期貿易逆差引起的。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長期的貿易逆差、還有缺乏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導致美國的房地產和資產很難升值。而在歐盟內部,德國與其它歐盟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恰如我國和美國的關系,而由于其它歐盟國家長期的財政赤字最終導致了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
但值得討論的是,在中短期匯率制度的選擇和金融一體化程度影響一個國家的國際貿易收支和國際貿易經常賬戶收支不平衡的調整速度。在20世紀50—60年代,歐盟區建立之前,穩定的匯率其實是得益于當時金融一體化沒有像目前這樣發達,其后在歐盟區核心國家的良好的經濟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良好實施誘使歐盟區非核心國家的國債定價偏低,隨著在2000—2007年德國經常賬戶貿易順差的增加以及人們預測歐盟國家內部將進行良好的互相協調,種種因素促進了其它歐盟國家的貿易逆差,最終導致這些國家低息貸款,房地產及其它資產價值被放大。在經常賬戶長期逆差的國家,如果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允許銀行信用的迅速發展,這種金融體系將刺激資產的評估,增加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相反,由于我國對金融業的控制使我國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保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從而有效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我國由于長期順差所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用來購買外國國債,同時進行多元化的外匯儲備。同時由于順差所儲備的大量外匯可以用來外匯對沖,有效降低了外匯對沖的成本。但持續的長期貿易順差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對我國造成了不少負面影響。首先,隨著國際貿易順差額的迅速增加,雖然有效減少了對沖的外匯成本,但如何解決過多的對沖流動性成為央行的一道難題,并且央行在吸收外匯的同時,需要釋放同量的基礎貨幣,對我國物價的穩定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其次,央行要弱化由于基礎貨幣釋放過多而造成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央行貨幣政策的實施。
美國作為巨大的消費國是否可以保持旺盛的消費需求,同時全球經濟是否可以穩定增長,這兩個方面對中國和德國是否可以長期保持貿易順差至關重要,但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可以看出,未來我國和德國無法持續保持貿易順差。縱觀全球經濟,在理論上世界各國的經常賬戶余額相加在一起應該為零。因此如果將目光放在債務國身上,從美國對全球經常賬戶失衡可以看出債務國是全球經濟是否可以穩定發展的根源,金融危機后所有國家的發展態勢正在發生改變。金融危機發生前各國的發展狀態是不可持續的。2000—2007年間美國的國際貿易經常賬戶逆差占GDP的比重大約為4% ~5%,相反我國的國際貿易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重為8%~10%,石油輸出國等其它國家的國際貿易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重也相對大一些。
人口結構轉變將成為衡量一國的經濟是否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圖3和圖4可以看出,人口結構轉變將使我國和德國的國際貿易經常賬戶順差額減少。在未來的30年里,我國和德國人口老齡化率(65歲及超過65歲的人口占工作年齡18~64歲之間的人口的比率)在2010—2035年將分別增加24%和19%,而美國的人口老齡化率將增加14%。同時,德國人口的幼齡化率(年齡0~14歲的人口占工作年齡18~64歲之間的人口的比率)預計增長2%,而我國和美國的幼齡化率預計將分別下降2%和4%。人口結構轉變將通過消費、儲蓄、人力資本投資、勞動力供給和社會養老保障等方面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人口變化的趨勢會弱化我國和德國的貿易順差問題,將使在未來的25年內使我國和德國的經常賬戶順差與GDP的比率分別減少2.5%和3.5%。由于德國相對我國來說人口老齡化問題更為嚴重,由此帶來的影響可能要更大一些。而美國的人口結構轉變將使美國的經常賬戶貿易逆差與GDP的比例下降2%。因此,我國和德國的人口結構轉變將減少經常賬戶的貿易順差額。相反,美國會因此加大經常賬戶貿易逆差額。

圖3 中德美人口老齡化率比較
預測GDP的發展趨勢比預測經常賬戶國際收支的誤差要更大一些,但是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和其它新興國家的GDP的增長率要遠大于美國和歐洲國家,這對將來全球貿易失衡及我國和德國的經常賬戶貿易順差等有重要的影響。一個小國實行出口導向經濟增長政策,如果這個國家一直保持相對小一點的規模,它可以持續發展下去。但是像我國這種經濟大國,在長期保持經濟高速發展運行中很難持續GDP的高增長率,同時如果長期處于這種貿易順差將對我國的經濟造成巨大影響。

圖4 中德美人口幼齡化率比較
經過觀察各國數十年的經濟發展可知,除美國外,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經常賬戶長期逆差的條件下是否可以持續發展很大部分取決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我國可以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長期保持超過10%的GDP增長率,同時可以保持經常賬戶余額與GDP的比率保持在10%,一方面是因為國內的需求一直持續低迷,只有通過擴大國外需求才能解決國內生產能力過剩的問題,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在全球經濟中有像美國這樣在經濟項目中長期處于逆差的國家存在。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和西歐經濟一直萎靡不振,海外需求訂單大量減少,如果不實施經濟體制改革,擴大國內需求,我國的經濟發展必然會出現巨大問題。由于美國累積的巨額外債已經嚴重影響了美國經濟的正常運行,也對美國的對外經濟關系及美元的國際地位產生嚴重影響,所以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不具有持續性。隨著美國各行業處于疲軟狀態,美國已經開始減少消費,擴大儲蓄,美國的國際貿易經常賬戶長期逆差問題也會逐步改善。同樣,歐洲部分國家也已經開始施行緊縮的財政政策,歐洲各個國家包括民眾通過這次歐債危機也認識到一個國家如果長期保持這種國際貿易經常賬戶的逆差會給該國的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影響,所以如果經常賬戶赤字是由貿易逆差引起的,則當地的民眾必然會反對將這種國際貿易逆差擴大,從而應對工資下行的壓力。
我國已經開始著手經濟體制改革以應對國際貿易經常項目長期順差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如鼓勵我國企業出口附加值較高的產品,限制出口資源型的產品,限制國外流動性資本進入我國的投資領域等。同時我國需要從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向擴大內需轉變。中國近幾年的主要需求來自海外和國內基礎設施的投資,但隨著國際需求的減少和地方政府赤字的不斷增加,需要找到新的消費需求,促進城鎮化的穩步進行和區域的協調發展是擴大內需的關鍵所在。所有這些政策的實施需要以保障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民生是消費的主力軍,也是投資的方向。同時對于亞洲的新興國家而言,他們與我國面臨著相同的問題,這些新興國家同樣也注意到擴大內需的重要性,他們也同樣將會從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向擴大國內需求轉變,這會使包括我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收支經常賬戶順差減少,達到全球國際貿易經常賬戶收支平衡。在近幾年,我國經濟仍會受到歐美國家需求減少的巨大挑戰,而歐洲整體上會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的狀態。
[1]文博.中國經常項目賬戶不平衡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08.
[2]李健.我國外貿長期順差原因、影響和需要研究的課題[J].中國對外貿易,2006(9).
[3]廖立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增長效應分析[D].吉林大學,2011.
[4]嚴志輝.美元國際地位與美國經常項目賬戶赤字持續性研究[D].浙江大學,2009.
[5]朱玲.擴大內需的根本在于改善民生[J].北方經貿,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