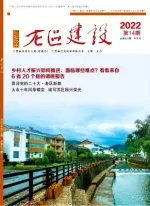九獅拜象的產生、演變及現存原因分析
鄧佐彬
“九獅拜象”作為一種獨有的大型民間燈舞,曾對營前地區的歷史造成了深遠影響,如今又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載入了史冊。“九獅拜象”究竟從何而來?經歷了怎樣的歷史演變才形成如今這般造型和規模?這些疑問都有必要進行較為詳細的解釋和論述。
一、營前與“九獅拜象”
營前鎮位于上猶縣西部,東接水巖,西與平富、五指峰接壤,南鄰崇義,北界水巖。距縣城46公里,距江西與湖南交界處40公里。2006年全鎮轄9個行政村,1個居委會,253個村民小組,有農戶6799戶,總人口30351人,其中農業人口28191人。土地面積65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11265畝,山地61254畝,水域2456畝)。營前有廣義和狹義上的定義,廣義上的營前指營前地區,是一個文化概念,包括三鄉一鎮(營前鎮、平富鄉、水巖鄉、五指峰鄉);而狹義上的營前是行政區域概念,指以營前小盆地為中心的營前鎮。本文通用文化上的概念。營前是個邊陲小鎮,但卻創造了高水平的民間燈舞——“九獅拜象”,這一直讓人感到驚疑,殊不知營前在晚清至民國年間,其商業繁榮程度號稱贛南“頭唐江,二營前”。[1]
“九獅拜象”不是單獨的一種燈彩或舞蹈,它是融造型、音樂、舞蹈于一體的綜合藝術。“九獅拜象”由1龍、9獅、1象、1麒麟、1牌燈、2鑼鼓彩亭組成,龍多為9節至11節,每節的間距大約6至7尺,龍頭用竹片造型,內置龍珠,龍身多用紅布或黃布綴接而成,內部可點燈燭,龍鱗多用金箔紙或用粉過金黃色的紙粘貼而成;獅一般由八只大獅、一只小獅(小狗獅)或七只大獅、兩只小獅組成,造型有蠶形、狗面、貓頭、豬臉等,以顏色分有黃獅、紅獅、綠獅等,其中黃獅最為尊貴,狗牯獅子若為白色,頭上須披紅布。獅身的腹部可以點燭,裝有機關通耳、眼、鼻、口各部;象比較龐大,骨架用竹篾編成,造型要顯得壯碩,骨架外面用白布貼好,口裝有機關;麒麟似鹿,身披梅花點,頸部可伸縮;牌燈是一個制作精美的長方形立體彩燈,一人舉著起引導作用,牌燈中央在舊社會時都書寫堂名或姓氏,解放后會寫主辦單位或“迎春”之類,有的就直接寫著“九獅拜象”;鑼鼓彩亭是放鑼鼓的“亭子”,隊伍前后各一個,由兩人抬著走,彩亭實際上是樂隊的依附。彩亭的制作很講究,上面可以扎出“八仙過海”、“劉海砍礁”、“三打白骨精”等紙牌人物,這些“人物”會做各種各樣的動作。在整個燈彩表演隊伍中,其順序是:
牌燈——鑼鼓彩亭(樂隊)——麒麟——黃獅(1)——紅獅(2)——獅(3)——獅(4)——小獅(5)——龍——小獅(6)——獅(7)——獅(8)——獅(9)——象——鑼鼓彩亭(樂隊)。
“九獅拜象”一般在農歷正月初二至十五期間搞,臘月就得準備,正月初二、初五、初八這幾天最為熱鬧,[2]到正月十五晚上活動完畢,需要舉行“謝龍神”儀式,把龍獅身上破損的布面燒掉,骨架留至明年再用。除了過年搞“九獅拜象”,特殊需要時也會搞,如開圩或有錢人家“暖屋”[3]也會請“九獅拜象”來熱鬧添喜。
“九獅拜象”表演節目一般有“少獅戲龍”、“金龍纏柱”、“麒麟獻瑞”、“九獅拜象”、“麒麟獅象團龍”等,表演場面十分活躍。伴奏樂隊以吹奏樂和打擊樂組成,吹奏樂有沙喇子、嗩吶等,沙喇子是一根細長銅管喇叭的樂器,只能簡單吹幾個音符。嗩吶常吹的曲牌有《狀元游街》、《三子對》、《將軍令》、《十杯酒》,有時也吹《小桃紅》、《茉莉花》等;打擊樂主要是鑼鼓,鑼鼓曲牌有引子、一花、二花、三花、滿堂紅等。整個樂隊吹奏的聲音高飄嘹亮,喜氣洋洋。
二、“九獅拜象”形成的歷史原因
“九獅拜象”確切產生于何年何月已無法考究。但可以推測:“九獅拜象”起源于明末清初時期粵東、閩西一帶客家人的內遷(贛南)。龍燈是中國春節傳統的娛樂活動,發源于中原,營前的土著人蔡氏、陳氏、朱氏其實也是從中原遷來的,幾經周折,最終在南宋年間遷到營前,所以蔡、陳、朱也可以算是客家人,只不過比后來的客家人早幾百年來到營前,從中原來的客家人自然也會搞龍燈,這時與全國其他地方的龍燈沒什么兩樣,故營前從南宋到明末并沒有“九獅拜象”。直到粵東客家人的內遷,帶來了廣東那邊的獅燈、獅舞,營前的燈彩才開始與其他地方不同。
要追溯“九獅拜象”的源頭,就不得不從姓氏龍燈講起。粵東、閩西一帶的客家人在明末清初遷到營前時,政權和土地已被當地人占據,剛來的客家人生活過得非常艱苦,隨著客家人內遷數量的增加,客家人口逐漸超過了當地人,客家人越來越想得到話語權,與本地人的矛盾就日益尖銳起來,期間還發生了械斗和屠殺,[4]客家人最終取得了合法地位,政府將客家人“編戶齊民”,這樣客家人就在營前站穩了腳跟。社會已經穩定,械斗、屠殺也很少發生了,更多的是宗族之間的摩擦和競爭,有的宗族就借春節時間在圩上以龍燈、獅舞來展示自己的經濟實力和威信,姓氏龍燈開始出現。每個姓氏搞龍燈都打上自己的堂名或姓氏,就當時燈彩隊伍來看,已具備現在的牌燈、龍和獅了,這應該是“九獅拜象”的雛形,但與其他地方相差還不是很大。
到了清朝末期,營前的地理位置優勢開始發揮出來,周邊地區的貨物在此集聚置辦,商業開始走向繁榮,其商業地位在贛南圩鎮中僅次于唐江。經濟上的繁榮,為文化的創造奠定了物質基礎。在龍燈方面,營前人也發揮了非凡的創造力:一些經濟實力雄厚的宗族在龍燈規模上大動手腳,龍的長度開始達到了9節至11節,據說劉姓扎過99節的長龍,[5]獅子個數也由最初的3個到5個、7個,最后達到9個,這樣的規模,已不是一般的宗族所能承受,因為要制作這些燈彩,要耗去大量財力,即使做好后,還需要請幾十個青壯年,又要花去不少錢。后人發現在龍、獅身上再也沒什么可攀比,隨后就引進了大象和麒麟,象是陸地上最龐大的動物,能壓獅,而且象通“相”和“祥”表示權利和吉利;麒麟是祥瑞動物,仁德之獸,人人期盼自己的兒子是個“麟子”,許多地方都有麒麟送子的年畫。至此,“九獅拜象”就成型了。這時的龍、獅、象、麒麟等造型精美而夸張,加上樂隊和彩亭,整個隊伍浩浩蕩蕩,十分壯觀,能搞“九獅拜象”的都是一些大宗族。
“九獅拜象”在龍燈、獅燈的基礎上,在營前繁榮經濟和客家文化的孕育下,通過營前宗族之間的攀比和創造產生了。這一時期始于明末清初,止于清末民初,如果要一個準確的時間,“九獅拜象”應該成形于清末民初時期。
三、“九獅拜象”活動現狀
“九獅拜象”現被上猶縣文化局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下來,并申請到了贛州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現正在申請江西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每年投入不少資金搶救,“九獅拜象”逐漸恢復起來,現在在縣城每年過年和元宵都能看到其身影,但規模不能跟以前相比。
自新中國建立后,廣大農村實行了土地改革,土地分田到戶,宗族的“宗田”、“宗產”被分割。“宗田”、“宗產”有兩個作用:一是用來資助本宗族的孩子上學;二是作為全宗族祭祀或其他重大活動的經費來源之一。“九獅拜象”是全宗族的大型活動,但作為其經濟基礎的“宗田”“宗產”已經消失,僅僅靠個人籌資困難很大。這樣,維系宗族關系的活動變少,全族內部就沒有以前團結了,至此,宗族走向衰落,“九獅拜象”在姓氏中就很難搞起來。民間無法舉行如此重大的活動,政府組織也不是年年都有,畢竟“九獅拜象”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此外,這跟營前乃至整個上猶的經濟狀況也有關,營前的商業在民國初年達到了頂峰,隨著現代交通的發展,營前的交通區位優勢減弱,經濟逐漸被其他交通便利的鄉鎮所趕超。整個上猶的情況也差不多,至今是國家級貧困縣。經濟上的軟弱,致使對文化的投入和重視嚴重不足。
“九獅拜象”的恢復工作或許還面臨許多困難,但隨著研究“九獅拜象”的成果越來越多以及政府對其恢復工作投入的加大,相信“九獅拜象”在不久的將來就能以古老而恢宏的氣勢出現在人民面前,并讓“九獅拜象”的故鄉為世人所熟知!
[1]羅勇.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和發展:上猶縣營前鎮的宗族社會與村落文化[A].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C].臺灣中央大學出版社,2002.
[2]羅勇.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和發展——上猶縣營前鎮的宗族社會調查[J].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02,(1).
[3]羅勇.客家贛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4]黃志繁.營前的歷史、宗教與文化[J].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001,(24).
[5]黃志繁.國家認同與土客沖突——明清時期贛南的族群關系[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4).
[6]譚東輝,劉志民.贛南客家民俗體育文化的社會功能及其價值的研究——上猶縣營前鎮“九獅拜象”田野調查[J]. 南京體育學院學報,2010,(2).
[7]鐘善金,李君.贛南上猶營前大型客家民間燈彩藝術“九獅拜象”[J].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9,(1).
[8]李伯勇.九獅拜象探源.上猶縣文史資料:第1輯[M].南昌:江西省新聞出版局出版,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