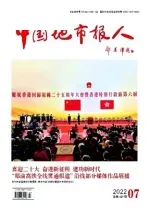小議輿論監督的發展趨勢
□冀亞鳳
(漯河日報社,河南 漯河 462000)
說起“新聞”,容易引起我們聯想的有兩個詞:一個是“監督”,一個是“宣傳”。新聞監督、新聞宣傳這兩項工作是我們媒體人同時肩負的兩大使命,缺一不可。
當下的社會,監督有著四大監督體系。這就是人大的法律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社會的群眾監督和新聞的輿論監督。這四大監督體系各有所長,但輿論監督作為社會公器,具有特殊的作用。
進入網絡時代,隨著網民的全民化,人人都可以在網絡這一新興平臺上發表個人的見解,每位網民都成為一位獨立的發言人。作為自然人,強烈的自我表現欲望和參與社會事務的欲望因為網絡這一表達平臺的設立成為可能。媒體監督的功能也得以在某種程度上泛社會化。周久耕、躲貓貓、趙作海、孫志剛等人物和事件成為這一新興監督形式的代表。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我國新時期新聞事業大變革的三十年。首先是與傷痕文學同步的反思類新聞,對歷史進行客觀冷靜的檢討和反思。這時候的典型文體是全方位展示某一社會現象的通訊類的大視角,如《唐山大地震》、《西北大移民》等;其后是直面社會陰暗面、自揭傷疤類的大曝光文章成為媒體主打,如《中國青年報》的“冰點”欄目中的文章,《大河報》上關于張金柱的報道等;之后是推動經濟體制改革、所有制轉型的報道,人們心無旁騖,將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經濟、創造社會財富上。如關于馬云盈利模式的報道、史玉柱東山再起的分析等。
最近幾年,隨著國際國內各種新矛盾、新問題的出現,我們的媒體人面臨適應新社會,思維觀念重構、報道方式創新的挑戰。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以往的傳播方式,各種敏感問題也隨之出現。
這些問題的出現,意味著媒體人必須摒棄原來純粹的監督者、正義者化身的角色,不能再一味地對社會品頭論足、指指點點,而要成為社會進步大船上的 望者和預警員。
2009年11月底,成都市民、企業家唐福珍自焚維權案發生,如果放在10年前,可能整個媒體就是一道腔:聲討暴力拆遷者,同情以死抗爭的唐女士。畢竟,面對強大的拆遷一方,唐福珍屬于弱者。但事實情況是:媒體不僅對唐福珍表現出了足夠的同情,對拆遷方給予無情的譴責。同時,人們更多地把眼光盯住了有違憲嫌疑的《城市拆遷條例》。造成一件件以命相爭的惡性案件、群體性事件的“靠山”或者“元兇”不是別人,正是這部條例。一個“拆遷”,將雙方爭論的焦點由寸土寸金的城市土地變為按照建筑物面積去賠償的物什。難以統計,一部條例制造了社會上多少的不和諧音符!同時,也正是這種反思的輿論,推進了《條例》的修訂,使“城市拆遷”向“搬遷”邁進。
我們不會忘記,2009年烏魯木齊的“7·5”事件,本是我國的一個省級建制的行政單位內部發生的一起有預謀的事件,結果受到各種國外媒體、團體的別有用心的關注。多虧了國家及時實施互聯網管制、歡迎境外媒體實地采訪等措施,截斷了謠言傳播渠道,使得事件及時得到平息,國際輿論也最終成為可資利用的力量。
政府越來越開明,問題越來越多;時代越來越敏感,處理問題的難度也越來越大;人人都是媒體人,但每個人的發言都不權威。這就是我們媒體人所要面對的現實。
這樣的媒體生存環境讓我們想起了一則故事。
古代一位高明的民間醫生和一位御醫相遇。民醫問御醫:我們都是救死扶傷,我是民醫而你是御醫,你說民醫和御醫有什么不同?御醫回答:你在給人治病時只求治好病,別的什么都不考慮;我在給皇上治病時不但要考慮治好病,還不能讓皇上有痛苦。這就是咱們的不同。
一語中的!盡管我們常說苦口良藥利于病,但如果藥太苦,病人仍然不愿意吃,甚至因此把病情給耽誤了。遇到這種情況怎么辦?最為妥當的辦法就是給藥裹上糖衣,讓病人無痛苦地服下。
御醫有著讓普通民間醫生艷羨的地位,但也擔當著難以預料的風險:一旦在治病的過程中讓龍體有了痛苦感,可能就有性命之虞。因此,御醫在治病過程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心理可以感同身受。
作為新時期的新聞從業人員同樣需要御醫這種心態。不是為某個人,是為了適應整個社會對新聞工作的需求。
因為,我們面臨著新的風險,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政治風險。我們已經走過了“上級讓說什么,媒體人說什么;媒體說什么,社會聽什么”的時代,更多的時候是大家都在說,分不清誰是職業媒體人、誰是業余的,分不清誰的權威獨家、誰的是流言蜚語道聽途說。這對我們媒體人的政治素養和敏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足夠的政治敏感和鑒別力,就有可能被人利用,被所謂的民意所裹挾,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
權威風險。我們已經知道,網絡時代就是一個人人都是傳播者的時代,每個人都在說,作為職業媒體人要說到點子上,說得讓大家口服心服,就要有足夠的權威的對新聞事實的掌握,有嚴謹的對事件發生發展的分析,有科學的對事件性質的評判。要做到這些,就必須有過硬的新聞專業知識和技能,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正如大家同時身陷險境,你要讓大家都聽你的,相信你能帶領大家走出險境,就要有足夠的智慧和人格魅力。
權力風險。我們已經習慣了面對負面新聞,地方媒體和外地媒體截然不同的兩個態度:地方媒體集體噤聲、外地媒體不依不饒。集體噤聲是因為地方保護主義,認為負面新聞都是家丑,家丑不能外揚;外地媒體不依不饒是因為他們覺得要報道事實真相,地方官員的意志無法強加于他們。即便如此,本地與外地本身就是邏輯學上的一組模糊概念,把握不好,仍然有輕者受批評、受處分,重者調離工作崗位的風險。準確拿捏負面新聞的曝光度,并非易事。
跟風風險。網絡時代的新聞與傳統媒體的新聞時代的顯著區別就是新聞傳播的瞬間效應。無論是非曲直,只要是網友感興趣的,無論是正面報道還是負面新聞,都會被熱情的網友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傳播開來,很少有糾錯的時機。這對我們新聞從業人員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于新聞事實,來不得半點的“可能、也許、似乎、大概”。一旦出現閃失,造成的負面影響絕非個人努力能夠挽回。
相對于互聯網理論上沒有數量上限的網友,和他們的熱情、敏銳、沖動、跟風以及幾乎無所不能的“人肉”手段,作為傳統媒體人,所謂的新聞輿論的工作內涵必須適應這一新的大眾傳播方式,改變以往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將以往慣常使用的監督社會下發為引導輿論,成為輿論羊群中的領頭羊,解放大軍中的先導部隊。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新的輿論環境,才不至于被網絡時代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