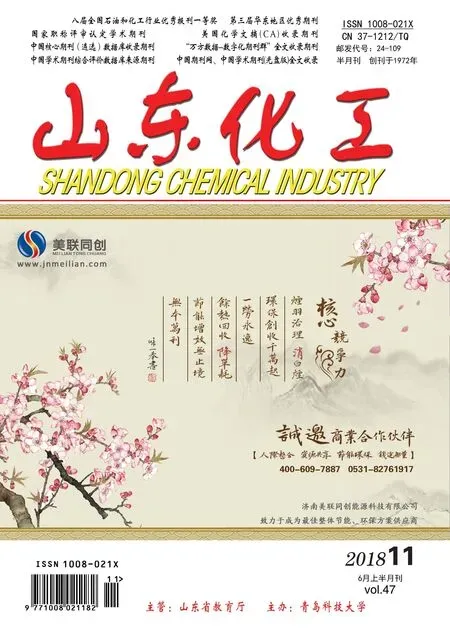裂解爐供熱方式對燃燒特性影響的模擬研究
夏文娟,王 濱,李 智
(鄭州大學 化工與能源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乙烯裂解爐是乙烯裝置中的重要設備之一,裂解爐的運行情況是由爐內的燃燒情況決定的[1-2],燃燒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如燃燒器的結構形式、爐管以及燃燒器的布置結構、燃料的組成和性質、底部和側壁燃燒器的供熱比例等[3],其中燃燒器的排布結構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4]。燃燒器的安裝主要布置在裂解爐的輻射段底部和側壁兩個位置,根據組合方式主要分為以下3種:全部由底部燃燒器供熱(即全底燒供熱)、全部由側壁燃燒器供熱、底部燃燒器和側壁燃燒器聯合供熱[1,5]。
本文應用流體力學Fluent計算軟件,以某石化廠的乙烯裂解爐為模擬對象,模擬計算出三種供熱方式下燃燒器內的NO濃度場、燃氣噴口的溫度場等。可以為新型乙烯裂解爐的設計和現有裂解爐的優化研究提供參考。
1 物理模型及邊界條件
1.1 幾何模型
本文應用Solidworks和 icem CFD軟件對裂解爐進行模型建立和網格劃分。聯合供熱與全低燒供熱的裂解爐的底部燃燒器均為燃氣分級的低NOx燃燒器,區別僅在于全底燒供熱時無側壁燃燒器;另外側壁燃燒器為單排分布。

圖1 聯合供熱模型結構示意圖
鑒于爐膛結構的對稱性,本文選取爐膛的1/12進行建模,兩種裂解爐的幾何模型結構示意圖分別見圖1和圖2,其中圖1所示為聯合供熱時側壁燃燒器分別采用預混燃燒個非預混燃燒的模型結構示意圖。OPrins等計算結果表明裂解爐燃燒模型用非結構化網格模擬得到的壓力場分布比用結構化網格模擬的結果更準確[6]。裂解爐的燃燒器尺寸與爐體尺寸差距較大[7],故這里采用混合網格的劃分方式進行網格劃分,如圖3所示,燃燒器的周圍區域及裂解爐橫跨段采用非結構化網格,爐體和爐膛區域采用結構化網格。全底燒供熱裂解爐與聯合供熱裂解爐幾何模型的網格數量分別為183萬個和214萬個,網格質量行列式檢查時大于0.50,角度檢查大于0.40,因此網格劃分滿足質量檢查要求。

圖2 全低燒供熱模型結構示意圖

圖3 裂解爐模型網格劃分
1.2 爐膛計算邊界條件
計算時,聯合供熱情況下底部燃燒器與側壁燃燒器的供熱比例為85∶15,空氣溫度為353.15K,過剩空氣系數為1.05;爐膛出口采用壓力出口邊界,爐管和爐墻均采用輻射和對流的混合壁面邊界調節,燃料氣及空氣采用速度入口邊界條件,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入口邊界條件
注:聯合供熱1為底部和預混側壁燃燒器聯合供熱;聯合供熱2為底部和非預混側壁燃燒器聯合供熱。
2 計算結果與分析
2.1 溫度場分析

圖4 聯合供熱1(a)、聯合供熱2(b)和全底燒供熱(c)時燃氣噴口面的煙氣溫度分布
圖4為兩種聯合供熱以及全底燒供熱時底部燃氣噴口面上煙氣溫度分布。由圖4可見,聯合供熱1(側壁非預混燃燒)燃燒室內的最高溫度為2130K,聯合供熱2(側壁預混燃燒)燃燒室最高溫度為2210K,而全底燒最高溫度為2300K,全底燒供熱時煙氣最高溫度主要在爐膛下半段。另外,比較聯合供熱條件下燃燒室內溫度場的分布可以看出,側壁燃燒室的燃燒方式對底部燃燒器的燃燒具有顯著影響,側壁非預混燃燒時,底部燃燒器的燃燒更加充分,呈現長火焰燃燒,爐膛內溫度分布的均勻性更好;而側壁預混燃燒時,側壁燃燒器以上部分呈現均勻性較好溫度場,但燃燒室內整體呈現較大溫差。
聯合供熱以及全底燒供熱的底部燃氣噴口中心線的溫度曲線如圖5所示,由圖可見聯合供熱條件下側壁燃燒器的燃燒提高了爐膛上半段的溫度,側壁非預混燃燒時在爐膛底部溫度逐漸升高,在0.15 m處溫度達到最高,在0.15~2.5m段溫度較為穩定;側壁預混燃燒時對底部燃燒器的流場有較小影響,在0.15 m處溫度達到最高然后下降,在1.7m處溫度最低1310K,然后快速升高,在2.8 m處溫度達到最高2013K,此后隨著爐膛高度的增加,煙氣溫度逐漸下降;全低燒供熱時在0.2 m處溫度達到最高2180K,此后隨著爐膛高度的增加,煙氣溫度越來越低,在爐膛中部2.1 m處溫度最低,此后煙氣溫度又逐漸升高。由于全低燒供熱時底部燃燒器的燃氣流量大于聯合供熱,故全低燒供熱的燃氣和空氣速度更大,混合更充分,燃燒劇烈;側壁非預混燃燒時燃燒室內的溫度較為穩定、均勻性較好。側壁預混燃燒時爐膛內的溫度有小幅度的波動,爐膛內溫度均勻性略差。

圖5 聯合供熱1(a)、聯合供熱2(b)和全底燒供熱(c)時燃氣噴口面的煙氣溫度曲線變化
2.2 中心線上NO分布

圖6 聯合供熱2(a)、聯合供熱1(b)和全底燒供熱(c)時燃氣噴口面的煙氣溫度分布
燃氣噴口中心線上的NO質量分數分布如圖6所示,由圖可見側壁非預混燃燒時,NO含量在0.3 m處開始逐漸增大,在1.2 m處達到7.00e-5,此后在2.15 m之前均保持7.00e-5
不變,此后由于側壁燃燒器的燃燒使得NO含量經過少量降低后快速增加,在2.9 m位置達到最大值2.95e-04,此后開始快速降低,最后在出口位置為1.25e-4;側壁預混燃燒時NO含量隨著爐膛高度增加快速增加,在2.0 m處達到最大值1.85e-04,此后由于側壁的預混燃燒NO含量快速降低,在2.4位置處降到最低后隨著溫度的升高而逐漸增加,在出口位置達到1.42e-4;全低燒供熱條件下NO含量隨著爐膛高度的增加而緩慢增加,在出口位置達到3.0e-4。由此可見全低燒供熱時NO的生成量大于聯合供熱。
3 結論
(1)聯合供熱時側壁燃燒器采用非預混燃燒時的溫度場比采用預混燃燒時,溫度場更均勻,爐膛下半段的溫度變化較穩定,煙氣中NO的生成量也增長緩慢且含量較少。由此可見爐膛溫度均勻性越高,NO生成量越少。
(2)全低燒供熱時底部燃燒器的燃氣及空氣速度比聯合供熱條件下大,故兩者混合程度較好,燃燒更快速,爐膛內溫度增長快速,且全低燒供熱時爐膛內的平均溫度高于聯合供熱。
(3)聯合供熱條件下側壁燃燒器采用非預混燃燒和采用預混燃燒時,兩者的燃燒結果差別較大,對于本裂解爐側壁燃燒器采用非預混燃燒更節能、環保。
[1]袁霞光.乙烯裂解爐燃燒器技術進展[J]. 化工機械,2011(3):255-259.
[2]張 建,李金科. 裂解爐用低NOx燃燒器國內技術進展[J]. 化工機械,2012(6):681-685.
[3]蘇 毅,揭 濤,沈玲玲,等. 低氮燃氣燃燒技術及燃燒器設計進展[J]. 工業鍋爐,2016(4):17-25.
[4]劉 波,吳 雨,王元華,等. 低NOx工業燃氣燃燒技術研究進展[J]. 化工進展,2013(1):199-204.
[5]周先鋒. 數值模擬研究不同供熱形式對裂解爐運行的影響[J]. 石油化工,2010(11):1221-1227.
[6]張朝環. 乙烯裂解爐內燃燒與裂解反應過程數值模擬[D]. 天津:天津大學,2008.
[7]Guihua H,Honggang W,Feng Q.Numerical simulation on flow, combustion and heat transfer of ethylene cracking furnaces[J].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2011,66(8):160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