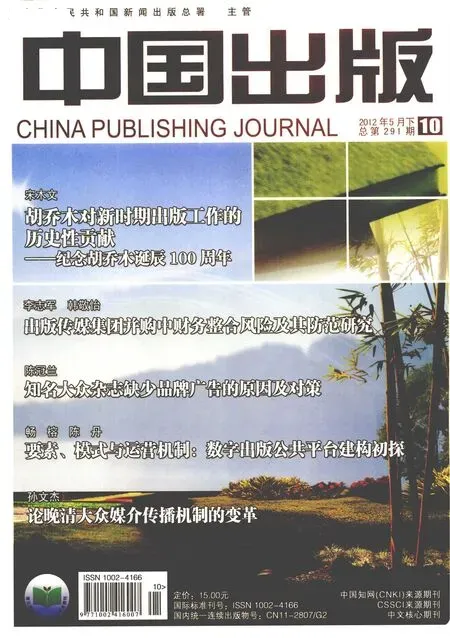論晚清大眾媒介傳播機制的變革*
文/孫文杰
中國晚清社會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無數仁人志士懷抱救亡圖存、富國強民之目的,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許多西方文化思潮借助圖書、期刊、報紙等大眾傳媒在中國得以快速傳播。作為清代傳播史的一個重要支脈,媒介機構通過哪些傳播機制變革,使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國得以廣為流傳,從而對中國社會及文化產生深遠影響,這是一個很有學術價值的問題,本文試就此探析,并求教于方家。
一、稿件來源的變革
中國古代稿件多源自士大夫階層,由于“恥于言利”的傳統觀念,沒有稿酬制度,給著者僅有部分的潤筆費。至晚清,民營書局和報館日益增多,據梁啟超統計,在1815 ~1902 年間,全國存佚報刊總數達124 種。市場競爭導致爭奪稿件現象的出現,稿件來源歷經從免費刊登到向作者支付稿酬的發展階段。
1.免費刊登稿件
為了吸引士大夫階層向報館投送稿件,有的報館專門設立專欄,免費刊登稿件。例如,《上海新報》在1862 年的征稿啟事云:“華人如有切要時事,或得自傳聞,或得自目擊,但取其有益華人,有益于同好者,均可攜之本館刳刻,分文不取。”[1]又如,《申報》在1872 年創刊時刊登《本館條例》曰:“如有騷人韻士有意以短什長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區竹枝詞及長歌紀事之類,概不取值;如有名言讜論,實有系乎國計民生、地利水源之類者,上關皇朝經濟之需,下知小民稼穡之苦,附登斯報,概不取酬。”[2]這等于為文人們開辟了一個免費刊登其文學作品的園地,反響熱烈,來稿踴躍,以至《申報》容納不下,隨后出版了以文學為主的《瀛寰瑣紀》、《四溟瑣紀》和《寰宇瑣紀》等專刊。
2.有獎征稿
在晚清,一些教會、民營書局、報館為了吸引士人,獲取優質稿源,利用廣泛的社會智力資源,曾多次舉行有獎征文。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1836 ~1907 年)于同治初年(1870 ~1871 年),分別以《圣經》的“持守美事”、“宜查凡事善者執之”為題,公開征文,對錄用的30 名作者,分別獎洋7 元、2 元、1 元。清光緒十五年(1889),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 ~1890 年)以“格致之學泰西與中國有無異同”與“泰西算學較中國為精”為題目征文,獎金分別為洋10 元、7 元、3 元、2 元。光緒二十年(1894年),英商公平洋行湯姆斯·漢璧禮應李提摩太之請,捐贈500 金作為征文經費,在蘇州、北京、廣州、福州、杭州五地散發1 萬張通知征文。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初二,傅蘭雅(John Fryer, 1839 ~1928年)在《申報》登載“求著時新小說”時,設立洋8元至50 元不等的酬金,并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1 月13 日在《申報》上登載“時事小說出案”,公布了20 名獲獎者名單及獎金。[3]
3.支付稿費
在免費發表文人作品數年之后,一些報館實行向作者支付稿酬購買書稿,申報館首開先河,《申報》在1878 年曾刊登《搜書》啟事:“啟者,本館以印刷各種書籍發售為常。如遠近諸君子,有已成未刊之著作,擬將問世,本館愿出價購稿,代為排印。抑或俟裝訂好后,送書數十或數百部,以申酬謝之意,亦無不可,總視書之易售與否而斟酌焉。”[4]從這則史料可知,申報館愿意出價購買稿件,同時考慮有一些有身份的作者不愿意出賣自己的著作,則可采用變通的手段按照慣例出版新書作為酬勞。隨后,報館又發展到對來稿支付稿酬,最早始于《點石齋畫報》,于1884 年6 月4 日刊登《請各處名手專畫新聞啟》,公開聲明愿意付給稿費,成為晚清報刊建立稿酬制度開始的標志。其他以新聞為主的報館相繼采用申報館的做法。稿酬給予的方式不一,有以字數計算,或論篇計算,或論本計算,不一而足。如商務印書館付給林紓的稿酬為每千字5 元,后來增至6 元。林氏用文言翻譯歐美小說170 余種,其語言清暢明麗,曲盡其致,平添原著感人魅力,深受人們喜歡。清劉聲木(1876 ~1959 年)《萇楚齋五筆》卷八云:“光緒末年,閩縣林琴南孝廉紓,翻譯西文小說,由商務印書館排印,盛行一時。”[5]晚清社會逐漸對稿酬標準、支付范圍等達成共識、形成慣例,對圖書、雜志和報紙等大眾傳媒的發展,以及對西方文化思潮的傳播有著重要的驅動作用。
4.版權制度
在晚清最后10 年,版權制度初現端倪,著作者的權益逐漸得到保障。一些如嚴復等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士向民營書局提出版權問題,并翻譯和介紹相關西方版權的論述。在1900 年前后,嚴復在翻譯《原富》時,和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明確提出版權問題。當時南洋公學以2000 兩銀買下《原富》書稿,并按嚴氏要求,將該書售價20%給譯者,并提出給予分利的具體條款。約在1903 年,嚴復致書管學大臣張百熙詳細闡述實施版權法利益之所在,“國無版權,使寫作翻譯者裹足不前,則出書必少,最終有害社會教育和民智開啟”。嚴氏翻譯的《社會通詮》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時,與該館簽訂了第一個版稅合同,第一次使用版稅權印花。1904 年,嚴復翻譯的《英文漢詁》一書尾部首次印有“候官嚴氏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著譯者印花,用以控制印數,保護著作的權益。這些實踐客觀上也催生了1910 年的《大清著作權律》的出臺,對后來民國時期的新聞傳播影響較大。
二、言述方式及傳播符號的變革
傳播的本質是信息的流動,而信息的有效傳播則需要借助受眾能夠接受言述方式與傳播符號。西方文化思潮的傳播同樣也根據受眾需要做出調適,以滿足啟蒙思想、開啟民智的社會需求。通過言述方式和傳播符號的變革,傳媒機構擴大了受眾的覆蓋面,影響更為廣泛。
1.大眾媒介言述方式變化
大眾媒介的言述方式歷經從文言到白話的嬗變。英國傳教士威廉·米憐(William Milne,1785 ~1822 年)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在編輯和撰稿時,盡量迎合中國人的傳統心理,表現主要有二:其一,言述形式上附會儒學,每一期封面上都印有“子曰:多聞,擇其善而從之”的字句。在其闡釋《圣經》的文句中更多引用“四書”、“五經”和孔孟程朱的言論,以此顯示二者在思想和精神上的一致。其二,在文章的寫作上也采用中國文學特別是章回體小說的表現手法,在篇末用“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之類的句子,并注意文章的短小、通俗。
隨著大眾傳媒的興起,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及民主革命運動輪番登場,這就需要通過在盡可能廣的范圍內警醒和發動大眾,西方文化思潮需要運用大眾最熟悉、最親切、最貼近的語言去表達、去言述。當時社會上一些文字改革的倡導者用新時代的理念對傳統漢字進行反思,揭露弊端,由此最富于感染力、最具有直接性的“白話”成為各個報刊的通用表達方式和語言。如《大公報》在創辦之初就專設“附件”一欄,堅持白話宣傳,成為白話文有力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以其說理平淺,最易開下等人之知識,故各報從而效之者眾”,[6]在1897 ~1918 年間,共有170 余種白話報刊。[7]白話報刊出版地遍及全國及東京等地,但以長江流域的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為盛。白話報刊中影響較大的有《民報》《無錫白話報》《寧波白話報》《杭州白話報》《中國白話報》《安徽俗話報》《直隸白話報》《京話日報》等。較之傳統文言而言,白話成為傳播新思想的工具,能夠深入普通民眾,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新詞匯的輸入
大眾傳媒自身的特性和功能,要求它所傳遞的語言傳播符號系統要與之相適應。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傳播過程中,各大傳媒機構在編譯西書時引進和創造出一批新詞匯。墨海書館、同文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廣學會、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機構出版的西書匯集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詞。李善蘭、徐壽、華蘅芳、嚴復、林紓、偉烈亞力、傅蘭雅、林樂知等中外學者都為新名詞的引進創造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從引入的變化上來看,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形成的新詞匯主要源自歐美國家,之后由于大量翻譯日本書籍而從日本引進了一系列新詞匯。例如,政治方面的新詞匯有革命、維新、殖民、民權、人權、女權、自由、平等、憲法、民約論等;文化學術方面的新詞匯有天演論、進化論、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物競天擇、文明、德育、科學、文明進化論等。后來由于日文新詞的流行,使不少以前輸入中國的時髦詞匯(主要從歐美引進的新詞)逐漸被淘汰,如英文Artificial selection,中文原譯“人擇”,日文翻譯“人為淘汰”;Selection, 中文原譯“天擇”,日文翻譯“天然淘汰”;Evolution, 中文原譯“天演”,日文翻譯“進化”;Struggle for existence, 中文原譯“物競”,日文翻譯“生存競爭”。較原來傳統的漢語詞匯而言,晚清從日本引進的新詞匯具有易懂、準確等優點,最終成為漢語的一部分,有的還進入基本詞匯的行列。
三、傳播技術的改進
西方文化思潮通過大眾媒介之所以能夠快速傳播,其重要因素之一是依靠傳播技術的提高和改進,其中包括印刷技術、造紙技術、通訊技術等提高,使得傳播速度快、覆蓋面廣成為可能。
1.印刷技術的提高
晚清中國傳統幾千年沿用的雕版印刷日漸式微,逐漸退出市場,石印技術、鉛印技術被大規模引進,由此引發中國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文化生態的巨大變化。其中,印刷技術的提高使印刷速度、數量、質量、版料、字體、形式等得到改進,適合大規模、專業化的生產。戈公振先生曾對咸同與光宣年間的印刷速度做過對比,“咸同間,始多鉛印,但印機甚陋,每小時只印一二百小紙;光宣間,石印機與鉛印機輸入日多,報紙每日可出數千大張”,[8]由此可見印刷速度提高之快,而王韜所見到的上海墨海書館印刷機則可達到“一日可印四萬余張”。商務印書館采用了凸印、平印、凹印等技術和設備,甚至可以做到一天出一書的速度。
隨著印刷技術的提高,編譯出版西學類圖書數量也迅速增加。據周昌壽《譯刊科學書籍考略》統計,1853 ~1911 年,翻譯出版的西方科學書共有468 部,其中數學164 部,理化、博物(生物)各90 余部,地理58 部,總論及雜著44 部,天文氣象12 部。周振鶴《晚清營業書目》中多有西文、日文、法德文、英文科學等類目,說明隨著西學東漸,此類書在市場中日漸走俏。以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為例,該館在開辦的前11 年內,銷售圖書達31111 部,共計83454 冊,零售出地圖4774 張。[9]
2.西方造紙法的引進及紙張進口
中國傳統的造紙都是手工操作,所生產的紙張用于書寫、包裝,雕版印刷所用的紙張的品種有十則紙、竹連紙、官堆紙、白宣紙、賽連紙、重賽紙等,雖質量上乘,但不適宜于近代用機器高速印刷。晚清時期西方造紙方法的引進,用于近代機器印刷的造紙業——機器造紙業,19 世紀80 年代才首開其端并逐步發展。同時一部分印刷機器用紙從海外進口,據李伯嘉《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出版業》統計,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至宣統三年(1911 年),進口紙張銀34165333 海關兩,[10]見表1。

表1 1903 ~1911 年進口紙張海關兩統計表[11]
據上表,宣統三年(1911 年)的進口紙用銀5605755海關兩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 2684437海關兩的2.09倍,足見海外進口紙張之多,使傳播業突飛猛進,發行量一天天擴大的平裝書和近代化報刊的大量生產才會成為可能,且成本降低引起價格下降,以報刊和平裝圖書為主要媒體的大眾傳媒才得以繁榮興盛。
3.通訊技術在傳播中的運用
晚清時期,電訊技術在新聞中得以運用使傳播速度加快。以往的新聞傳播多依靠人力或快馬加鞭式的傳遞,若從北京到上海最快需要20 天左右,遑論惡劣天氣。隨著電訊技術的發展,一些報館開始運用此技術。《申報》在1882 年2 月23 日首次用電訊傳遞新聞“光緒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農歷)奉上諭:禮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著孫毓驤署理。欽此。”從收到該電訊稿距刊發《申報》的時間僅3 天時間。當時清政府的電訊總局設在天津,從天津到上海,陸路計程2800 華里,沿途在臨清、濟寧、靖江、鎮江、蘇州、上海均設有分局。各個報館派有外埠訪員,若有新聞則隨時可到電報局拍發。有的報館為了追求新聞的時效性,對使用電訊傳播的外埠訪員有所獎勵。如《中外日報》的《章程》中規定“各處如有異常緊張之事,均令訪員即行電告,俾閱者先睹為快”,首設自己的“專電”,對每一條專電獎銀2 元。另外,電話也在各個報館、民營書局經營中得以運用,從大眾媒體的廣告上可以看到聯系的電話號碼,如在《商務印書館書目提要》一冊封面上署有“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市,電報八八六六號,電話五五五號”,[12]這無疑也加快了信息的傳播速度。
四、經營運作的市場化
晚清時期大眾傳媒市場化運作,使西方文化思潮傳播的覆蓋面更廣,同時競爭也日趨激烈,營銷手法也策略迭出。隨著市場的需求而呈現動態變化,多頭并進,傳媒機構也不斷調整其經營策略以適應市場,主要有三個方面。
1.對受眾群體需求的調查
晚清傳媒機構對受眾群體需求的調查,主要包括購買群體、暢銷品種、購買能力等,以此生產適銷對路的圖書和期刊,其針對性更強,如“旨在廣為譯著有益書籍”的廣學會的市場調查及營銷策略很值得關注,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 ~1919 年)于光緒十七年(1891 年)曾對中國文人、官員的數量做過較貼近實際的調查統計,以確定廣學會的銷售重點對象,見表2。

表2 廣學會調查受眾統計表
從表中來看,李提摩太以其中5%為重點,計算約30501 人,經過挑選的官吏與文人家庭的婦女兒童,以10%計算,4000 人,這樣廣學會工作重點對象共計44036 人。至于整個中國而言,平均每縣只有30 人,這些人有購買書刊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力。隨之發行《成童畫報》、《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大同報》、《女鐸》等暢銷書刊,其中以《萬國公報》影響最大。廣學會1893 年出售書刊僅953 本,次年即升為2286本,1899 年有20379 本,1902 年達到售書量的高點,有48306 本。[13]而從其售書額來看,根據《廣學會第十一屆(1898 年)紀略材料》統計,1893 ~1898 年,廣學會下屬各省書所售賣西學圖書的收入,從1893年的800 余元增加為1898 年的1.8 萬余元,5 年之內陡增20 多倍,也足見當時中國求新者眾。
2.媒介的促銷宣傳
有的媒介機構采用免費贈送的方法,以此吸引受眾,如“《泰西新史攬要》《中東戰紀本末》《格物探原》《時事新論》《列國變通興盛記》及《萬國公報》諸書,初印時,人鮮顧問,往往隨處分贈,即而漸有樂購者,近三年內,幾于四海風行”。[14]有的媒介機構加大廣告宣傳,除了在報紙上刊登書籍發行宣傳廣告,還在書刊上印制廣告宣傳圖書,不僅是刊登本書的推銷廣告,還出現在一本書刊上刊登多種書籍廣告的形式。光緒十六年(1890 年),英國傳教士傅蘭雅主編的刊物《格致匯編》,自光緒二年(1876 年)創刊至光緒十八年(1892年)終刊共計60 卷,其中各類廣告多達60 余則,而格致書室等發售書籍廣告占了1/2。光緒三十年(1904年),商務印書館創刊的《東方雜志》,常常利用余幅,刊登本館出版物的廣告。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上海發行了我國出版界主辦的第一本期刊——《圖書月報》。其正文僅44 頁,廣告卻有94 頁,比正文多出一倍有余。后來的媒介機構就充分利用書刊的封三、封四,分門別類地介紹自己的出版物,尤其是刊登該書刊的同類書廣告。這種廣告給讀者的印象頗深,有助于圖書銷售。
3.建立銷售網點
隨著晚清大眾傳媒渠道的拓展和延伸,民營書局和報館等傳播機構紛紛建立銷售網點,降低經營成本,加快圖書和報刊流通速度。例如,點石齋書局(又稱為點石齋石印局)、上海創立同文書局、廣學會、申報等機構在全國建立銷售網絡,發兌圖書和報紙。其中《申報》在開創之時,僅在上海本埠銷售。1873 年年初,申報館才在杭州設立分銷處,到1881 年2 月間,外埠的分銷處共有北京、天津等17 處。每天銷售的份數也從600 份左右擴大到2000份左右。到1887 年,又增加15 個分銷處,前后共計32 處。至1907 年,申報館在西南地區桂林、東北地區的哈爾濱、海參崴以及國外日本、英國、法國等地先后設立分銷處,每天的銷數增加到萬余份。[15]作為地方性報刊的《安徽俗話報》也逐步建立自己的發行代派處,除安徽省外,在北京、上海、山東、河北、江蘇、江西、湖北、遼寧等省設置58 處之多,發行幾乎遍及全國。
注釋:
[1]上海新報,1862-05-07
[2]本館條例[N].申報,1872-04-30
[3]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57-558
[4]申報,1878-03-07
[5](清)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M].北京:中華書局,1998:1037
[6]大公報,1905-08-20
[7]蔡樂蘇.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種白話報刊/丁守和.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93-546
[8]戈公振.中國報學史[M].上海:三聯書店,1955:357
[9]傅蘭雅.江南制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A]/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 [M]. 上海:群聯出版社,1953:12
[10]“海關兩”是清代至1930 年海關用的記賬單位,各地不同,每兩約合紋銀1.05 兩左右
[11]李伯嘉.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出版業[C]/ 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9:386
[12]周振鶴.晚清營業書目[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256
[13]王樹槐.清季的廣學會[C]/林治平.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M].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240-242
[14]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7:336
[15]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 [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