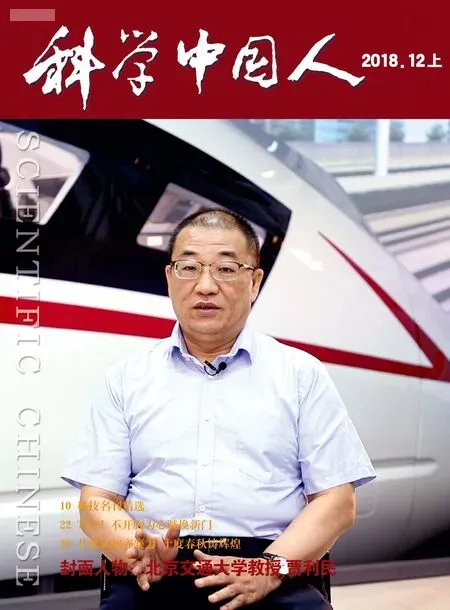與時俱進,求索于生命科學最前沿——專訪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及生物動態光學成像中心蘇曉東教授
本刊記者 胡魁元 宋 潔
隨著二十一世紀初人類全基因組測序計劃的完成,國際上生命科學研究的“航母”極速駛入了所謂“后基因組時代”。這一時代最主要的研究特征就是按照全基因組圖譜提供的信息來闡明生命體內的基因產物,即蛋白質及核酸的生物學功能。作為生物體內廣泛存在且最為豐富的物質——蛋白質一直被認為是生命活動最主要的功能執行者,全面深入闡明它們的詳細機理可以幫助人類理解復雜的生命現象以及生命的起源、演化過程,從而對于人類的健康醫療事業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因此,對該領域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持續性的熱潮。
在這場生命科學領域的世界性角逐中,中國科學家正以越來越多的實際行動與越來越高的研究水平走向生命科學的國際前沿,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長江特聘教授”,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蘇曉東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搞科研:鉆堅研微 迎難而上
如同地球上所有其他物質一樣,生命體也是由原子構成的。構成生命物質的原子種類相對簡單,是元素周期表中靠前面排列的幾種較輕的元素(氫、碳、氮、氧、磷、硫及一些金屬離子),其特殊性是生物大分子由有限的簡單單元線性排列組合成為幾十到幾千個單元乃至上億個單元(如DNA)的多聚大分子物質,這樣的排列組合理論上可以形成幾乎無窮無盡多種復雜的三維結構。而“后基因組時代”研究領域之一的結構基因組學,最終目的就是要把自然界生命體中存在的所有蛋白質三維原子結構都一一解析出來,從而為進一步功能研究及生物醫學應用打下堅實的物質及結構基礎。
事實上,目前已知的蛋白質序列已經有幾千萬種,隨著越來越多的生物物種的全基因組序列被完全組裝測定,不同種類的蛋白質總數還在呈指數增長,而我們目前已知三維結構的蛋白質還不到十萬種,因此,即使已經考慮到蛋白質序列間的同源性,擺在結構生物學家面前的工作也還是異常艱巨的。前路漫漫,要想探知真理,需要各國結構生物學科學家共同努力、多年奮斗方有可能完成。
面對著科研世界的萬頃狂瀾,蘇曉東教授自2003年回國之后,就迅速投身北大,致力于組建高通量蛋白生產及晶體結構解析技術平臺、應用及發展蛋白晶體學技術方法。他的目標堅定而明確,直指結構基因組學研究中的“瓶頸問題”。
蘇曉東教授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88年入瑞典皇家卡羅林斯卡醫學院諾貝爾醫學研究所細胞與分子生物學專業學習結構生物學,獲得博士學位后,又進入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生物學部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作博士后研究,回國工作前曾任瑞典隆德大學化學中心助教授及副教授。豐富的海外求學與研究經歷,為他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夯實的基礎。
經過五六年的不懈努力,蘇曉東實驗室建成了初具規模的高通量、高效率、低消耗結構基因組學技術平臺。這個可以達到每年處理2000個以上基因克隆、蛋白表達純化及晶體篩選能力的結構生物學平臺,為大規模結構基因組學研究打下了基礎。并且完成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重點項目“致齲變形鏈球菌全基因組的蛋白表達及三維結構研究”。
作為國內僅有的進行細菌全基因組蛋白結構解析的結構基因組學研究項目,這一課題不僅本身蘊藏著豐富的科學價值,同時也在病原生物學、蛋白質結構與功能研究、齲齒防治等各方面具有重大意義。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高通量生物技術平臺得到不斷完善。蘇曉東實驗室始終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放在首位,成功地將改進的常規克隆方法應用于高通量自動化技術當中,在不失效率的前提下,完成了把解析一個蛋白晶體結構的平均成本降至國際水平的五分之一的預期目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到目前為止,該結構基因組學平臺已經完成了4000多個各類基因的克隆、表達純化及晶體篩選工作,主要以大腸桿菌和昆蟲桿狀病毒表達系統為主,表達純化了從人類到細菌的各種可溶蛋白500多個,得到蛋白晶體近300種,解析蛋白晶體結構100多種,在一些重要蛋白質的結構與功能研究中取得可喜成果。

蘇曉東教授向前北京市委書記劉淇等匯報實驗室自主研發的自動化蛋白結晶篩選系統。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向科學巔峰奮勇攀登的同時,蘇曉東實驗室還極為重視科學儀器設備及耗材的自主研發及應用推廣,即不僅要將購置的國際先進儀器利用好,還致力于研發生產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自動化設備及相應耗材,這個策略在平臺建設初期是作為降低成本的手段提出,后來逐漸演變成為蘇曉東實驗室科研工作的一個方向。與其他許多科學研究儀器類似,我國在自動化、規模化、高通量篩選等生物醫學儀器方面基本依賴進口。然而,近年來,我國在科學研究、醫療衛生、公安、制藥等高科技領域對此類設備的需求卻與日俱增。蘇曉東實驗室在科學儀器方面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國家科技部863重大項目“人類肝臟、肝病相關蛋白質的三維結構研究及高效率低成本蛋白晶體自動觀測系統的研發”的支持,目前,蘇曉東實驗室研發的自動化蛋白晶體觀測系統及結晶板研發第二代自動化蛋白晶體觀測系統樣機已經完成,典型產品已經市場化,軟件系統升級及相關知識產權注冊進行中。國際生物系統標準SBS標準的幾種96孔蛋白及384孔結晶板的設計加工已經完成,部分耗材已經產品化,正在多個實驗室使用及測試中。
與此同時,蘇曉東實驗室還積累了豐富的基因、蛋白實物及數據資源,尤其是蛋白晶體結構解析以及分析產生出的數據資源,在探討蛋白質晶體學新方法、相關生物系統功能的進一步研究等各方面,均奠定了堅實有利的基礎。在此背景之下,蘇曉東實驗室和其他幾個相關單位一道啟動了科技部973項目“基于上海同步輻射光源的結構生物學技術和方法研究”。這個項目的實施,將為中國進一步塑造一批高精尖技術人才,蘇曉東實驗室20多名研究生在該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得到充分的學習和鍛煉,截至2012年,在蘇曉東建設回國工作的近十年間已有20多人順利完成博士學業,先后有十多名博士及博士后研究人員直接參與了結構基因組學的研究工作。

蘇曉東教授與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前諾貝爾化學獎評委會委員、著名結構生物學家 Anders Liljas 教授在一起。

2011年6月BIOPIC中心的各位研究員與國際學術評審委員會合影留念。
建中心:開拓視野 銳意先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回溯現代生命醫學重要領域的發展進程,每一個重要的飛躍都是由技術進步所驅動的。而這些技術進步大都來自其他相關交叉領域的知識積累和經驗總結。新的技術和實驗方法帶來的不僅僅是實驗效率的提高,更多的是還使得許多新的生命現象得以發現,從而引發并解決新老生命科學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在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中,由于對儀器或測試方法進行創新或者改進而獲獎的科學家約占四分之一。而在生命科學和醫學領域,技術與儀器的進步帶來的不僅僅是我們對基本生命過程認識的加深,更極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質量。現有的儀器和技術手段在生命科學與醫學的研究中往往存在靜態、低效、非活體等缺點,難以滿足生物體這一特定體系研究的需求。要實現原位、實時,動態多參數活體檢測,就必須在方法、技術、設備等各個方面有所突破,提出新的想法,發展新的技術及研究平臺。
在結構基因組學研究取得初步進展的同時,蘇曉東教授將目光敏銳地投向了單分子生物物理研究及分子成像領域。他介紹說:“現代生命科學研究和醫學診斷與治療技術對相關儀器和技術的開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在不同層次的活體上獲取動態的生命活動信息。分子成像技術作為我們認識生命過程、改善醫學診斷的一個重要手段,得到了生命科學、醫學、工程學、化學、材料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科研工作者的重視。正如單分子單細胞生物物理研究的開拓者、哈佛大學謝曉亮教授和美國已故著名科學家J.Widom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活細胞是21世紀的試管。這方面的研究從國際上來看也是起步不久,許多技術需要綜合運用生物、數學、物理、化學、工程及計算機信息科學等多學科知識,僅依靠單一學科難以取得重大突破,我們急需多學科的交叉、協作與融合。”
由此,經過一年多的充分醞釀,在學校領導的大力支持下,2010年底,由美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長江特聘講座教授及哈佛大學謝曉亮教授和蘇曉東教授推動及組建下的“北京大學生物動態光學成像中心”(簡稱“BIOPIC”)應運而生,謝曉亮教授任BIOPIC主任,蘇曉東教授任中心常務副主任。
古人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世間萬物形態各異,由此衍生出了各種思維和各種學科,將不同的思維,不同的學科交融在一起,往復生一,往往又能獲得令人欣喜的新發現,BIOPIC可以說是生物、物理、化學及數學、計算機等各學科交融貫通的結晶,它的成立,可以充分利用北京大學在多學科交叉研究中的獨特優勢,在分子、細胞、組織和機體多個層次上開展成像關鍵技術與方法的研究和開發,為推動生命科學發展、提升產業結構、改善醫學診斷等多方面提供支持。
“生物科學新的發展趨勢是從定性科學轉變為定量科學,從數據不足及模糊的科學轉變為數據豐富及清晰的科學。生物學的進展會越來越依靠新的物理化學及現代分析手段。BIOPIC要發展和利用最新的單分子生物物理、生物光學成像和下一代DNA測序技術,通過跨學科研究來大力促進生命科學的發展。具體來講我們要發展的技術是活體內單分子、單細胞檢測、超高分辨率光學成像、無標記光學成像和新一代的DNA測序技術及其應用。”據蘇曉東教授介紹,BIOPIC自成立以來,近兩年時間內已經完成了具有國際最先進水平的實驗室基礎建設和設備購置及安裝;建成了900多平米的高標準實驗室與辦公空間,獲得了海內外來賓和同行的高度評價,為科研平臺搭建和科研人員全心全意工作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基礎和條件。目前,中心已經建成以微流控技術為主要手段的集成生物學實驗室、單分子及活細胞動態過程研究實驗室、干細胞及表觀遺傳學實驗室、單分子生物物理實驗室以及相干拉曼散射顯微鏡實驗室。特別要提到的是建成了國內外高校最大的下一代DNA測序設施及分析中心,現已擁有四臺國際上最先進的HiSeq 2000測序儀及一臺SOLiD 5500測序儀,并且正在建立相應配套的超大計算機機組和數據分析平臺。BIOPIC的主要大中型儀器安裝測試培訓已經基本完畢,各項研究項目正在大力推進中;在十來位團隊PI成員的共同努力下已經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近兩年來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幾十篇,其中包括Nature Biotechnology,Nature Structural and Molecular Biology(NSMB),Nature Methods,Acc.Chem.Res., Cell Research, Lab on a Chip等國際頂級雜志,最近,BIOPIC的兩項重要原創性合作成果也已經被Science期刊接受發表。
做管理:凝心聚力 劍指科研
身兼國際晶體學聯合會(IUCr)大分子專業委員會主席、中國晶體學會秘書長、北京大學“蛋白質與植物基因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以及BIOPIC常務副主任等職務,蘇曉東教授在帶領課題組全力進行科研攻關的同時,還要處理日常管理事務,這對一般人而言絕非易事。
當我們問及蘇曉東教授是如何理解常務副主任、課題組負責人和研究人員這三者之間的角色異同,以及如何分配時間和精力來兼顧到這三重身份時,蘇曉東教授如是作答:“角色可能不同,但目標卻是一致的。無論是作為科學研究人員、課題組負責人,還是常務副主任,工作核心都是為了科學研究。從這個角度來說,合理分配時間和精力來兼顧到這三重身份,并不矛盾,也不復雜。值得欣慰的是,通過幾年的努力,我們已經打造出了一支優秀和高效的科研和管理團隊。大家秉持共同的信念,團結協作,已經形成了很強的科研攻堅能力。”
事實也正如蘇曉東教授所說,近年來,他所帶領的科研團隊無論在結構生物學或者是BIOPIC相關的科研上都屢有收獲。
2012年6月,《自然結構與分子生物學》 (Nature Structural and Molecular Biology, NSMB)上發表了蘇曉東實驗室的論文“The structural basis for the sensing and binding of cyclic di-GMP by STING”。這項研究解析了固有免疫信號通路中的重要接頭及感應蛋白STING胞內部分及其與c-di-GMP(bis-(3’-5’)-cyclic dimeric GMP)復合物的晶體結構。STING (也被命名為MITA/ERIS) 是由北京大學蔣爭凡實驗室、武漢大學舒紅兵院士實驗室和國內外多家實驗室幾乎同時發現的多次跨膜蛋白,進一步研究發現它可以直接感受并結合一類細菌特有的第二信使分子,如c-di-GMP,從而介導激活宿主下游信號傳導通路,進而產生細胞因子及其它固有免疫反應,這是人類固有免疫響應中的一個全新概念。通過結構分析,蘇曉東組的研究人員發現以前預測的在不同物種中非常保守的第五跨膜區實際上處于胞內,并且這個區域對于STING形成同源二聚化介導的生物學功能至關重要,這一結果與蔣爭凡研究組以前的發現非常吻合;結合與c-di-GMP復合物的結構分析,他們提出,STING具有一個“蓋子”區域,在沒有結合c-di-GMP前,這個區域具有較高柔性,易于敞開;一旦感應及結合c-di-GMP后這個“蓋子”區域就會與其它部分一起形成更加穩定的結構,非常牢固的結合c-di-GMP,復合物也進一步穩定了同源二聚體結構。
除此之外,蘇曉東實驗室近年來的另一代表性工作是Caspase-6的結構與功能研究。Caspases是一類特異性剪切天冬氨酸位點的半胱氨酸蛋白酶,廣泛存在于從線蟲到人類的多細胞動物中,參與執行、介導和調控一系列重要生物學功能包括細胞凋亡及炎癥反應等。Caspase-6與Caspase-3和Caspase-7類似,同屬于下游的effector caspases,負責細胞凋亡的執行。但是,最新的研究發現它在神經退行性疾病,如亨廷敦舞蹈癥和老年癡呆癥中扮演重要角色。蘇曉東研究組近五年來系統深入地研究解析了Caspase-6的特殊活化功能,從生化測試到原子結構水平上探討其功能及活性調控機制。到目前為止已解析了多個處于不同活性狀態的Caspase-6相關三維結構,這些結構填補了國際上Caspase-6酶原及結合抑制劑結構的空白,為酶機理的深入研究以及基于結構的藥物設計奠定了基礎。根據已得到的結構信息,他們設計完成了一系列生化實驗,最終得出了Caspase-6利用分子內自切反應實現活化的模型。該活化反應機制在Caspase的研究領域中具有較強的原始創新性,為進一步研究Caspase家族,尤其是Caspase-6的作用機理以及生物體內調控機制提供了新思路。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如EMBO reports及JBC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生物、物理、化學、計算機……多個學科交叉詮釋了科學空間;原子、分子、基因、細胞……微小的發現開啟著生命的種種奧秘。在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和生物動態光學成像中心里,生命科學的精彩正在演繹,蘇曉東教授與時代的賽跑,還將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