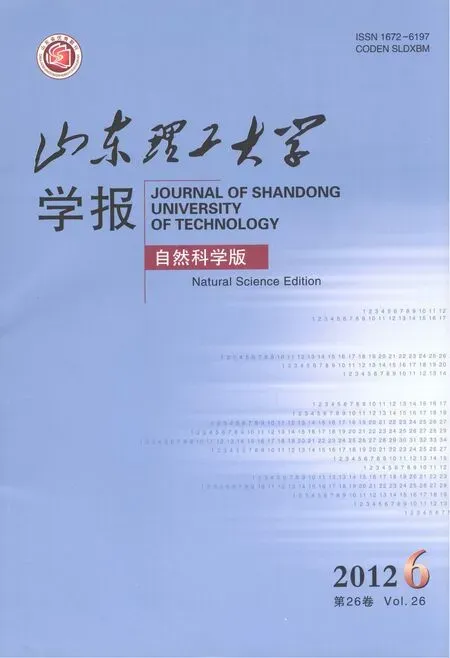山西黃土地區公路邊坡強度參數選取方法研究
籍延青,隋來才
(山西省交通科學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黃土地區公路邊坡的防護設計中,首先要計算邊坡穩定性,穩定性計算的理論如極限平衡法、數值分析法等均需要提供巖土體強度參數.目前常用的方法是按照巖土規范并參考實踐工程中直接剪切測試或采用反演法確定抗剪強度指標,之后進行計算,但計算結果常與實際情況不符,計算是穩定的,而實際仍會失穩破壞甚至出現滑動.究其原因,除了測試手段的局限性、巖土強度參數的高變異性外,反演過程中的人為經驗分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本次課題研究依托山西省臨吉、離軍、汾離等已建、在建高等級公路,以現場調查、室內試驗為基礎,通過研究邊坡土體變形機理和強度參數變化規律,并結合本次調查綜合考慮山西的氣候、地理地貌差異、黃土的地質特征以及黃土的各種物理力學性質指標得出的山西黃土地區公路工程地質分區(圖1)、地層組合形式以及邊坡破壞模式,力圖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參數選取方法,減少人為因素對參數選取的失準,為山西黃土地區公路邊坡防治設計中強度參數的合理選取提供理論依據.
1 邊坡變形破壞與強度的關系

圖1 山西省公路工程地質分區圖
黃土剪切破壞可以由其過程曲線(圖2)表示,從中可以發現強度參數之間的關系及土體的變形規律:剪應力τ隨剪切形變ε變化,A點對應土體彈性極限,A點后土體開始發生塑性剪切破壞,B點為土體的強度極限即峰值強度τf,BC段為土體骨架結構破壞、顆粒定向排列的階段.CD段后強度趨于穩定,不再隨剪應變而變化,D點是土體在對應垂直應力作用下達到的顆粒重排的最佳排列點,此時土的強度達到其殘余強度τr.

圖2 土體剪切變形曲線
室內試驗一般取B點即峰值強度作為抗剪強度值,而實際上邊坡失穩破壞可能發生在AB段,其值小于τf,即沒有達到峰值強度前就發生破壞,又如邊坡所在區存在老滑坡,此時計算強度常取CD段參數值,因而單純采用峰值強度來計算邊坡的穩定性顯然是非常不合理的,反演值又不能擺脫人為因素的影響.這里需引用“啟動強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啟動強度是滑坡失穩時滑帶土的強度,它是概化的概念,因為滑坡啟動時部分滑帶土達到了峰值強度,部分可能已過了峰值,對于不同發育階段的邊坡和滑坡土,可能等于邊坡土的峰值強度、殘余強度、完全軟化強度或長期抗剪強度,也可能是介于以上各種強度之間的某一數值,可認為是邊坡整體失穩啟動時滑帶土的平均抗剪強度,對應于黃土塑限含水量時的抗剪強度.
2 強度參數的獲取
2.1 峰值強度
峰值強度一般通過室內試驗四聯直剪儀獲得,試驗時不少于取4個試樣,逐級遞增施加不同的垂直壓力,慢剪試驗是土樣在某一級垂直壓力作用下,待排水固結變形穩定后,再緩慢施加水平剪應力剪切,快剪則沒有固結排水的過程直接施加水平剪切力,剪應力峰值對應的強度為土體峰值強度.
大量試驗分析[1-9]表明,峰值強度特征值受多因素影響,不同試驗條件測得的峰值強度是不同的.分析原因,峰值強度反映的是測試樣品在某一含水狀態下的一種”狀態強度”,排除試驗方法的影響,試驗樣品由于采樣部位不同導致的含水率不同、土體結構不同是這種離散性大的主要原因.
2.2 殘余強度
殘余強度一般通過反復直剪強度試驗獲得[10-13],試驗儀器采用應變控制式直剪儀,黃土常以0.02~0.06mm/min的剪切速度進行剪切,第一次在低垂直壓力下剪出試樣的滑動面,然后再重復剪切5~6次,每次剪切位移量為8~10mm,總位移量一般在40~50mm之間.繪制出不同垂直壓力下剪切位移—剪應力曲線(圖3),以最后剪應力的穩定值為殘余強度τr.殘余強度反映的是土體的“屬性強度”,與土體物質成份、顆粒含量相關,試驗中變化率不大,在判定老滑坡穩定性計算中可直接選用此值作為抗剪強度.
2.3 啟動強度

圖3 剪應力-位移曲線

圖4 含水率-強度曲線
文獻[14]通過對黃土、古土壤進行大量的剪切試驗,繪制出含水率-強度曲線(圖4),建立了強度與含水率之間的聯系,曲線由平緩段BC和陡降段CD組成,C點對應的含水率表示強度發生突變的起點即為啟動含水率ωC,對應的強度為啟動強度τC,并通過試驗比較發現該含水率接近塑限含水率.室內直剪試驗測得的峰值強度,雖不能表征邊坡啟滑時的強度狀態,但峰值強度體現了在邊坡啟滑這一特定含水條件下的“狀態強度”,在工程實踐中可利用變含水率直剪試驗來得到土體的啟動強度參數.
3 對比分析
通過野外調查以及室內試驗結果分析,我們發現對于山西黃土邊坡,無論發生坡體還是坡面破壞均與土體強度參數以及地層組合形式有關,而不同工程地質分區因氣候差異、地理地貌差異、黃土的地質特征、地質構造的不同也造成了物理力學參數的不同,粘聚力c值更是呈現了北低南高的規律,對應到分區也就是Ia、Ib、Ic逐漸增大,這也表明邊坡穩定性與工程地質分區也存在著間接聯系.本文以實際工程為例,選取位于不同分區不同地層組合形式的邊坡體,采用峰值強度、啟動強度與殘余強度對其穩定性進行對比分析.
3.1 計算參數
對比分析中,巖土體力學參數(表1)均來自野外實地取樣經室內試驗獲得,具體試驗方法如2.1~2.3所述.

表1 巖土體力學參數
3.2 計算結果
由于邊坡高度大、范圍廣,整個坡體在沿軸線方向的變形很小,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力學分析采用平面應變假設模型.邊界條件為兩側限制水平移動,底部限制垂直位移.計算采用邊坡穩定性分析軟件GEO-SLOPE試用版生成.穩定性系數結果選用Bishop、M-P、Janbu法算出的最小值.
3.2.1 新黃土單一形式(Ⅰ)
計算簡圖如圖5所示,計算結果列于表2.

圖5 新黃土單一形式邊坡計算模型
由表2分析,采用不同強度計算邊坡穩定性系數,結果明顯不同.抗剪強度取峰值強度時最大為1.308,處于穩定狀態;取啟動強度計算時有所降低為1.111;取殘余強度計算時最小于為0.999,已處于極限平衡狀態.表明相同地層組合,相同坡型,受計算參數影響程度明顯,在實際設計工作中針對不同分區、不同地質環境背景,有必要合理選取相應的強度參數.

表2 新黃土單一形式邊坡穩定性計算結果表
3.2.2 新老黃土組合形式(Ⅱ)
計算簡圖如圖6所示,計算結果列于表3.
由表3計算結果可知,抗剪強度取峰值強度時邊坡穩定性系數為1.253,處于穩定狀態;取啟動強度計算時有所降低為1.053,已處于極限平衡狀態;取殘余強度計算時最小于為0.941,已處于失穩狀態.

圖6 新老黃土組合形式邊坡計算模型
結合數值分析結果認為,按照常規峰值強度指標計算,此邊坡穩定不易破壞;而按啟動強度取值計算,此邊坡處于極限平衡,破壞先出現在接觸面坡面部位,與實際調查情況接近;若按殘余強度取值計算,此邊坡則處于整體失穩狀態,評價過于保守.

表3 新老黃土組合形式邊坡穩定性計算結果表
3.2.3 老黃土單一形式(Ⅲ)邊坡

圖7 老黃土單一形式(Ⅲ)邊坡計算模型
計算簡圖如圖7所示,計算結果列于表4.

表4 老黃土單一形式邊坡穩定性計算結果
由表4可知,抗剪強度取峰值強度時邊坡穩定性系數為1.362,處于穩定狀態;取啟動強度計算時有所降低為1.129,仍處于穩定狀態;取殘余強度計算時為1.053,處于極限平衡狀態.說明老黃土單一組合形式邊坡利于穩定.
3.3 計算結果分析
綜合數值分析結果發現,采用不同強度參數對于邊坡穩定性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對于某一個邊坡,有可能采用峰值強度計算邊坡處于穩定狀態的,使用啟動強度或殘余強度計算出的穩定性降幅明顯,甚至會出現不穩定的狀況.因此在實際設計工作中,必須考慮結合不同工程地質分區,不同地層組合形式,選擇合適的強度參數評價邊坡穩定性,以求科學評價、合理設計、客觀投資.
4 結論及建議
山西許多高速公路不同程度穿越黃土地區,而不同工程地質分區、不同地層組合形式的公路邊坡,其穩定性分析參數的選取會有很大程度的區別,對應的評價結果也會截然不同.也就是說實際公路邊坡穩定性評價必須考慮峰值強度、啟動強度和殘余強度的合理選擇問題.
本文研究認為,在山西黃土丘陵溝壑區即工程地質分區中的Ⅰ區,其中部——Ⅰb區構造發育,地震活動使得土體強度相對下降,老滑坡較多,特別是基巖出露地區,公路通過此區域時,邊坡設計的強度參數應選用殘余強度,有很高的安全保證;北部——Ⅰa區降雨少,構造活動不頻繁,邊坡以坡面破壞為主,應優先考慮采用峰值強度進行邊坡設計;南部——Ⅰc區降雨多,此時在進行邊坡設計時應優先選用啟動強度,雖顯保守,造價高,但其最大程度的避免了地質災害的發生,實際上也節省了大量治理費用,其長期效益不言而喻.
[1]王永炎,林在貫.中國黃土的結構特征及物理力學性質[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
[2]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中國自然區劃概要》編寫組,中國自然區劃概要[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4.
[3]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公路自然區劃標準(JTJ003-86)[S],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
[4]交通部第二公路勘察設計院,公路設計手冊[S],路基,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
[5]全國道路氣候分區修正方案說明[J].公路,1959(15):33-36..
[6]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JTJ003-86公路自然區劃標準[S].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6..
[7]翟禮生.中國濕陷性黃土區域建筑工程地質概要[M].科學出版社,1983:134-145.
[8]劉怡林,支喜蘭,石剛.基于GIS的黃土地區公路地基承載力評價系統[J].公路,2006(l):123-126.
[9]羅纘錦.巖質邊坡破壞模式初探[J].廣東公路交通,2001(71):11-14.
[10]劉才華.巖質順層邊坡水力滲流及雙場禍合特征[D].北京:中國科學院,2006.
[11]劉海松.黃土地區公路高邊坡防護方案優化選擇研究[D].西安:長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12]高德彬.公路黃土路塹高邊坡穩定性研究[D].西安:長安大學,2008.
[13]李瑞娥.黃土地區公路工程分區及指標體系研究[D].西安:長安大學:2009.
[14]龍建輝.高速遠程黃土滑坡預測預報方法研究[D].西安:長安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