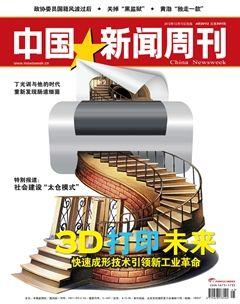切實推進媒體監督權的法制保障
盡管沒有確切的數據統計,但大致可以肯定,很多貪腐案件是由包括新媒體在內的輿論率先揭發或曝光的。例如,今年以來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表叔”“房叔”及最近的“雷政富”案件,起初都是在網絡曝光,隨后傳統媒體持續介入,從而對事情的性質轉化和最終被處理起到了關鍵作用。
可以這樣認為,在當今中國日益開放多元的社會環境里,以媒體監督為代表的人民大眾的社會監督,與執政黨的黨內紀檢監督、政府的行政監督和司法監督同等重要,是中國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基礎和保障。
近年來,中國媒體的監督作用也日漸增強,尤其在進入網絡時代后,傳統媒體與網絡技術相互結合,更強化了這種監督作用。然而,我們也不可對媒體的監督作用估計過高,很多時候,媒體呈現的是一種事后監督、異地監督、低階監督,媒體只是在某個事件或官員被查處后才介入,很多媒體和記者在報道公權力的丑聞時,不得不考慮,這樣做會不會對自己的安全帶來麻煩。
這是因為,中國的媒體監督缺乏實質的法制保障。這導致中國的媒體在行使監督權時,天生的艱難,故而,也就須付出更多努力乃至犧牲。不過,這從另一面說明,需要對媒體的監督功能給予更多保障,尤其是法制保障。
目前我們并不缺乏對媒體監督權的一般性規定,如憲法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都有這方面的條文。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條文,有關規定多半體現為政府的政策和主管部門的意見,法律層次太低。其次,這些條例條文,也不是從加強輿論監督的角度制定的,如一些地方在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中規定,對干擾、阻礙新聞媒體依法開展輿論監督的負有領導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問責直至追究刑事責任,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幾乎沒起到什么作用。而憲法雖然具有理論上的法律效力,然由于中國的憲法是不可訴的,因此,還需要依照憲法的其他立法來保證媒體監督權的落實。
要發揮媒體對公權力的監督作用,就必須以制度來保證各級政府充分尊重新聞機構對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所享有的知情權、采訪權、發表權、批評權、監督權,這惟有賦予法律保障才有可能實現。換言之,必須為輿論監督立法,新聞機構及其采編人員依法從事的新聞采編活動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干擾、阻礙。在當前態勢下,制定這樣一部法律條例,非常必要。
當然,為輿論監督立法并不表示一定要以新聞法的形式出現。包括新聞、法律界在內,社會上多年來有制定新聞法的呼吁。但鑒于新聞法牽涉多方考量,它的制定必是一個曠日持久的事情。而媒體監督的法制保障又迫在眉睫,所以必須抓緊時間,制定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規,以保障媒體行使監督權。
在此過程中,需要強調,政府尤其領導干部必須轉變對輿論監督的觀念。某種意義而言,這是當務之急。因為領導干部觀念跟不上,要做好媒體監督只能成為一紙具文。為此,須讓領導干部認識到,輿論監督的威力并非來自新聞本身,而是來自新聞背后所代表的民意。藐視和不愿自覺接受媒體監督,實際上也就是藐視和不愿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它導致的后果是,權力固然可以在不透明的情況下為所欲為,但也會為領導干部帶來極大風險,等到大錯鑄成,后悔就來不及了,而輿論監督,雖然對其是一種束縛,卻至少可以避免積小錯為大錯,從這個角度講,輿論監督實際上又是官員免于犯錯的“護身符”。
強化媒體監督的法制保障,還包括當權力觸及底線,打壓媒體時,社會包括主管部門,要勇于站出來保護媒體,司法在這方面尤其發揮著不可替代之作用。一些受監督官員往往抓住媒體報道中的某些不足,以所謂失實和侵犯隱私權為由,把媒體和記者告上法庭,此時,若司法不能秉持正義,無疑對媒體是一種災難。
在中國現有國情下,要媒體做到既理直氣壯地行使監督權,而又不擔心自己受打擊報復,確有隱憂。但社會客觀上又需要媒體發揮更大作用,只有以媒體監督為代表的廣泛的社會監督,才能有效打擊和預防腐敗。這對執政黨有百利而無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