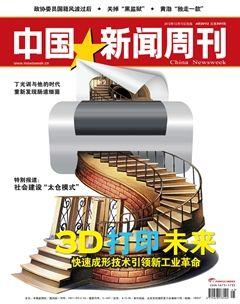再見,丹羽宇一郎
陳言

丹羽宇一郎2010年6月17日來中國前,也許沒有想到自己的命運會和釣魚島連在一起。
“我的工作從尖閣諸島(日本對釣魚島的稱呼)開始,最后也是在尖閣諸島問題上結束的。”做了兩年半駐華大使之后,2012年11月26日,丹羽宇一郎在離職前最后一次記者見面會上說。無奈的表情從他臉上一閃而過。
自1962年大學畢業開始進伊藤忠商事工作后,他遭遇過不少困難,但都憑自己的毅力、運氣挺過來。
此時,丹羽宇一郎的最大后盾執政的民主黨,已經無力顧及他們派出的民間大使。12月16日的大選,對民主黨來說更加緊要。
啟用民間人士出任駐華大使,曾經顯示了民主黨內閣改革外交的決心,但在執政黨地位難保的時候,外交革新早已無從談起。當丹羽宇一郎爬上萬丈高墻后,民主黨撤走了梯子,至于丹羽該怎么下來,變成了他的私事。
11月28日,丹羽宇一郎穿著他平日愛穿的深灰色西服,系一條深色領帶,輕裝簡從悄然回國。
從“抗議”開始
2010年6月,丹羽宇一郎來到中國前,日本外務省為他調配了最強勢的從事中國外交的官員、最好的中文翻譯。
3個月后,他已經比較熟悉外交工作,準備發揮自己對中日經濟、東亞及全球態勢的獨到見解,進一步推進中日關系。但此時日本大本營方面發生了變化。
進入2010年9月后,50多艘福建小型漁船在他們自古以來的傳統漁場釣魚島打魚,日本海上保安廳派出巨大船只驅趕福建漁船。9月7日,還有一條中國小船在抗爭,就是不肯從釣魚島撤出。日本方面在經過國土交通省大臣的同意,并征得首相菅直人的意見后,決定抓捕中方船長。
之前是日本使館的低級別外交官與中國外交部交涉,但抓人以后便需要大使出面了。
“中方召見日本大使前,會提前通知我們。到時大使便會準備資料,帶上公使、使館政治部的參贊級外交官、中文翻譯,按中方指定的時間去中國外交部。然后是聽中方的抗議,日本進行抗辯等等。在9月的一段時間內,這樣的工作成了大使館的主要對華工作內容。”一位日本外交官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顯然這不是丹羽宇一郎的特長,一切需要按外務省給好的口徑向中方抗辯,具體用詞規定得十分詳細,并沒有大使本人可以回旋的地方。這讓剛來中國不久的丹羽始料不及。
中日關系在2012年9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主黨內律師出身的大臣們,開始按日本國內法來處理外交問題。丹羽宇一郎的外交生涯,是從“抗議”及“被抗議”開始的。
不過,在記者和丹羽宇一郎多次接觸中,他從未談及這段經歷。“日中關系太重要了,不能讓這個關系出現倒退。”丹羽宇一郎對《中國新聞周刊》反復說,似乎也是在說給自己聽。
被忽略的經濟外交
在按照日本外務省規定的語言履行大使職責的時候,丹羽宇一郎開始時并沒有把釣魚島問題看得有多嚴重。
在他看來,中日經濟關系看上去發展順暢,貿易額從2010年的2977億美元,發展到了2011年的3428億美元,取得了13%的增長,但是和香港、韓國、歐洲、北美等國家和地區對華貿易的增長率比起來,日本已經落后很多。
“中國+1”的論調在日本甚囂塵上。“能否給我們公司的高管談談中國風險?”這是在日本,中國經濟問題的評論家最常接到的演講題目。不斷在高估中國風險,是日本疏遠與華經濟關系的重要原因。
而日本職業外交官又缺少了企業家具有的經濟視角,也缺少和中國經濟界以及地方政府的關系。丹羽最大的優勢便是這方面的人脈。
“到中國赴任后,我將盡可能走遍中國主要省會、主要城市。”丹羽宇一郎來中國前對日本媒體說。
撞船事件如疾風暴雨一樣,很快就過去了。丹羽開始實施走遍中國的計劃。
“每次去中國的地方城市之前,丹羽大使會先和在華日本商會打招呼,愿意和大使去地方訪問的企業,可以派人隨同大使一起去。畢竟能見到省長、省委書記,對企業來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商會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經常會有十幾家,有時是二十多家企業的中國地區總裁同時報名參加。
丹羽宇一郎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隨口就能說出那些地方省委、市委官員的名字。這是丹羽在日本最大商社之一的伊藤忠商事工作四十余年積攢下的巨大財富。
“很多中國的省級領導,在丹羽出任大使前便和他有過較多的接觸,現在丹羽成為大使了,自然更愿意抽出時間來見他。不單單談中日關系,經濟動向,重溫和大使個人的友誼,也是很輕松愉快的事。”前述日本外交官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日本企業更是直接從省級干部那里聽到了經濟發展的重點,能夠從地方最高層獲取投資、商務方面的機遇。
但是,對丹羽宇一郎去中國地方城市訪問,《中國新聞周刊》在日本聽到了完全不同的評價。
“丹羽大使一個人差不多把駐華使館的出差經費都花了,其他外交官反而沒有了出差的機會。”一位以外交評論為職業的日本媒體從業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我們從未聽說過丹羽大使會帶企業家去中國地方城市訪問,也未見過相關報道。”一家新聞周刊的副主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日關系本來因為領土問題已經非常不易,評論家、日本媒體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丹羽宇一郎的經濟外交,讓中日關系進一步后退,已在情理之中。
啟用丹羽宇一郎來中國做大使,這里面有民主黨內閣希望在經濟上強化與中國關系的考量,但又因缺乏統一的對華政策,結果讓政治目的大大地超越了經濟上的訴求。
一己之力無法力挽狂瀾
出任大使前,丹羽宇一郎是最成功的企業家。當伊藤忠商事背負4000億日元不良資產的時候,他挑起公司總裁的重擔,迅速扭虧為盈,讓企業重新成為日本最具有盈利能力的公司之一。2001年,他和日產公司總裁戈恩一起獲得了經團聯經濟廣報中心頒發的最優秀企業家大獎。
“1998年,丹羽當上了伊藤忠商事的總裁。因為公司虧損,他每天乘坐輕軌上下班,不用公司開工資,中午飯去吉野家吃一個蓋澆飯解決。”在伊藤忠商事工作的曹先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05年,《中國新聞周刊》在北京再次采訪丹羽宇一郎的時候,他已經是伊藤忠商事董事長。那時他剛出版《工作磨練人生》一書不久。“我的失敗別比人更多,所以感觸也多了一些。”丹羽宇一郎說。
其他公司的董事長總是前呼后擁,但丹羽宇一郎卻很少有人隨侍在旁。在職業生涯中,親赴前線直接應對各種問題,一直是他的特點。
“放棄每年數億日元的收入,來中國任這個僅有二千萬左右收入的大使,如果不是出自一種使命感,丹羽是不會接受這個職務的。”采訪外務省的日本記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丹羽宇一郎希望以一己之力力挽狂瀾,但中日進入全面合作新時代的大勢已去,等待他的只是一個更為動蕩的局面。
2012年4月16日,時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煞有介事地在美國宣布了自己的購島計劃。
“這會給日中關系帶來重大危機。”丹羽宇一郎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警告說。日本國內見到該報道后,頓時炸了鍋。在野黨紛紛要求解除他的大使職務。外務大臣召丹羽宇一郎回國后,警告他要在語言上多多注意。
“實際上誰都知道丹羽說了句大實話。而且后來的中日關系倒退到現在這個地步,暗合了丹羽的警告。”日本亞洲太平洋論壇理事長田中健二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離開中國前的最后3個月里,丹羽宇一郎還是和剛來時一樣,需要不斷和中國外交部交涉。9月11日以后,使館及日本企業遇到了二戰后前所未有的中國民眾在購島問題上的抗議游行,中日間領海問題的沖突愈發激烈起來。
“恢復日中(正常)關系,今后要再花40年時間。”10月20日,丹羽宇一郎回到自己的母校名古屋大學發表了關于中日關系的演講。
臨近離職的日子,丹羽宇一郎愈發地忙,除了在公眾場合外,記者已經沒有了一對一地和他交談的機會,但依舊能感覺出他對中日關系的期待。
在他離開北京的時候,中日關系因釣魚島而出現的裂痕,因為自民黨、維新會的候選人而變得更寬更深。今后幾年維持2011年經貿規模已經十分困難。民主黨的民間外交也脫離初衷,迎來了終局。
再有兩個月,丹羽宇一郎就會迎來74歲生日。日本人所說的“73歲大坎”也就要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