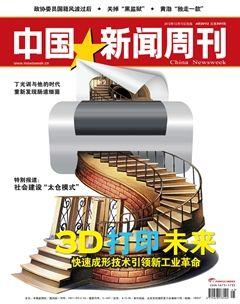《一九四二》:悲劇背后,所思者何
朱靖江
《一九四二》這部將近150分鐘的長片,全景式地展現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大饑荒,讓中國電影觀眾重新獲知一場幾乎已遭遺忘的歷史悲劇——以一種殘酷影像的方式。
在敘事方法上,導演馮小剛采取了全知視角的經典模式。一條線索是由張國立扮演的財主“老東家”范殿元一家人在哀鴻遍野的逃荒隊伍中家破人亡的慘烈經歷,另一條線索則是國民政府與軍隊對河南災情置若罔聞,甚至趁火打劫的貪腐行徑。這兩條主線由一位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白修德串連在一起,從而讓本片成為一個既有宏大背景可供反思國運,又有個體命運可供抒情嘆息的多層故事架構。
繼《集結號》和《唐山大地震》之后,馮小剛史詩電影創作的雄心壯志在《一九四二》中達到了巔峰,不論從實景拍攝的場面規模、出場明星的陣容,還是動用群眾演員、車馬物資的數量上,都堪稱近年中國電影中的超大制作。該片甚至邀請到阿德里安·布羅迪與蒂姆·羅賓斯這兩位影帝級的美國演員,足見其野心甚至是在奧斯卡的領獎臺上。
作為一部商業故事電影,《一九四二》無疑已經達到了優等品的檔次。影片結構完整,情節飽滿。一眾老戲骨演員——飾演“老東家”的張國立、飾演蔣介石的陳道明與飾演河南省長李培基的李雪健,也都展現出幾十年的演技修為。由于阿德里安·布羅迪曾在波蘭斯基執導的《鋼琴家》中扮演過一個幾乎被餓死的猶太鋼琴家,因此置身于《一九四二》餓殍遍野的逃荒路上,倒也并不突兀,反倒是蒂姆·羅賓斯扮演的傳教士,頗有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氣息,沒能對影片的情節發展起到任何催化作用。
如果說《一九四二》的創作初衷是為了制作一部有關1942年河南饑荒導致300萬災民死亡的影像文本,讓今日之國人對這段歷史悲劇所知所思,那么影片顯然已達到目的。然而,馮小剛試圖以本片為講臺,傳達他所奉為圭臬的道德準則與價值觀念,卻多少顯得有些笨拙和無力。
在某個電影網站提供的《獨家對話〈一九四二〉導演馮小剛》的訪談錄中,馮小剛表達了他對中國人“民族性”的批判態度。他認為“我們的民族飽受苦難,卻不當個事,麻木,然后就任其重演”,“好死不如賴活著”“自私和目光短淺確實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弱點之一”,以一種言辭激烈的姿態,為《一九四二》涂抹上一輪道德救贖的光暈,似乎“我們這個民族”的成員觀看了這部電影,感悟到其中的微言大義,反思自身,便有可能洗心革面地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貴族。
《一九四二》戲里戲外對逃荒饑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潛臺詞,都隱含著一種將精英與大眾對立,讓前者成為后者“救星”的文化立場。然而,這種意識形態既偏頗且危險。抽象的“民族性”通常是一種缺乏事實根據的主觀謬見,鼓吹者未必真的對“丑陋的”同胞心懷悲憫,反倒用它來反襯自我的道德優勢,甚至將其作為一種牟利的工具。特別是在草根階層所展現的道德勇氣和行動能力已遠遠超越知識精英的當代,對普羅大眾的藐視與所謂的“民族性”批判,其實是一種早已過時的自說自話。
《一九四二》的另一重道德困境,或許還在于影片主創者對于史料的選擇性運用。有人參研史料,認為蔣介石遠非影片塑造的那么清白無辜,而河南省長李培基與軍事長官蔣鼎文在這一事件中的是非功過卻與影片中的表現剛好相反,更有人舉證所謂“河南民眾靠日軍放糧獲救,進而協助日本人對抗中國軍隊”其實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謬論。無論質疑者是否有其事實依據,這些有關歷史事實的大關口確實值得我們探知真相,但馮小剛卻在上述的訪談中意外地強調:“因為這是一個故事片……不能拿著歷史去對照這個人說過沒說過。歷史上就沒有老東家這樣的人,但是有千千萬萬個老東家。”
盡管有千千萬萬個老東家,但真實的歷史人物與原本的歷史事實卻只有一個,不應成為劇情演繹的犧牲品,尤其是當這部影片的宣傳口號為“重現被遺忘的歷史”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