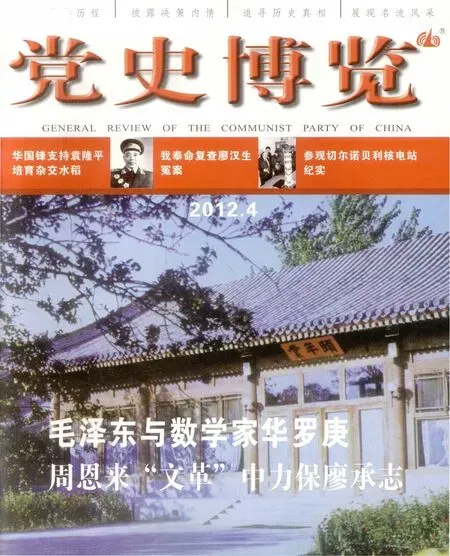參觀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紀實
■ 周曉沛
(本文作者為中國駐烏克蘭原大使。)
2011年3月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事故后,世人談“核”色變,再度對核電安全問題提出質疑,并情不自禁地聯想到20多年前發生的蘇聯切爾諾貝利核災難。應該說,一個是人禍,一個是天災加人禍,二者既有所不同,也有某種相似之處。切爾諾貝利核泄漏及其后果的真相究竟如何?我們又應從中汲取哪些教訓?雖然有的現在還是謎中之謎,但筆者愿將本人目睹的一些真實情況和切身感受同對此事感興趣的讀者一起分享。
乘車進入“死亡區”
2000年初的一個星期天,烏克蘭外交部組織駐基輔的外交使節參觀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據介紹,這是多年來首次安排這樣的活動。震驚世界的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在我心中一直是個謎團,巴不得能有機會親眼去見證一下歷史。
清晨,我們乘坐一輛大巴向基輔以北的方向駛去。切爾諾貝利離基輔的直線距離只有90公里,而汽車的行程則為130多公里。出城后,一路上很少遇到過往車輛。當我們經過一個名叫伊萬科夫的城鎮后,道路開始顛簸起來,還不時可以看到被廢棄的住宅、廠房和雜亂的建筑材料,給人一種莫名的凄涼之感。
大約過了兩小時,我們來到了一個有武裝衛兵把守的檢查站。陪同人員介紹,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事故后,政府作出決定,以切爾諾貝利為中心,將方圓30公里內的區域劃為“核隔離區”,亦即所謂的“死亡區”。周圍筑起兩米多高的鐵絲網,未經批準,任何人不得入內。
進入“死亡區”后的第一感覺是,這里并不像原先聽說的那樣可怕,路旁的草木依然茂盛,并未發現什么畸形的動植物。據介紹,兩年前有17匹蒙古野馬進入了這塊兒沒有人煙的地帶,并繁衍后代。隔離區內目前有400多種動物,包括280種禽類和50種瀕臨滅絕的動物。在遠處,居然還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民宅和耕地。經詢問得知,雖然政府嚴令當地居民疏散外遷并予以妥善安置,但一些老人不習慣異地生活,又陸續回遷,目前大約住著200戶土著居民。
臨近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時,又經過了一道崗哨的嚴格檢查。與此前不同的是,這里多了點人氣,可以見到路上的行人和車輛。按照指定路線,我們先去參觀當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工作人員居住生活的普里皮亞季城。這個小城離核電站不到5公里,原有約5萬居民。如今,普里皮亞季成了一座再也不能復生的“死城”。在進入小城之前,陪同人員就交代,要把所有玻璃窗關嚴,任何人不得開門下車,車內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了。
當汽車緩緩地開進一片杳無人煙的街區時,我們都被呈現在眼前的悲慘景象驚呆了:街道兩旁的商店、旅館空空蕩蕩,職工宿舍樓破爛不堪,幼兒園、文化宮一片狼藉,廢品、垃圾堆積如山,被遺棄的公共汽車還敞著車門停在路邊……廢墟四周死一般的寂靜。一改過去使團旅行時的歡聲笑語,大家誰也沒吱聲,都目不轉睛地看著車窗外閃過的一個個只有在電影里才能看到的恐怖鏡頭。待汽車駛離這片生命禁區后,陪同人員才繼續進行介紹。這里很少有人前來參觀。城里的核輻射量比以前要小多了,據專家測試,從幾百微倫琴到幾十倫琴不等。這種輻射量通常不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傷害。當然,停留的時間不能長,也不能碰摸這里的任何東西。
沒過多久,我們來到了由一座辦公樓和四個核電機組聯為一體的乳白色建筑群前,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
參觀“蘇聯列寧核電站”
核電站主樓前屹立著一座列寧雕像,樓門上方依然保留著蘇聯國徽,一塊銅制門匾上刻有“蘇聯原子能部切爾諾貝利列寧核電站”的字樣。這里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14年前的情景。1986年4月26日1時23分44秒,就是眼前這座核電站綜合體另一端的4號機組核反應堆發生爆炸。反應堆內的8噸多放射性物質外泄,相當于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輻射量的200多倍,給核電站附近的員工和居民,給國家經濟和生態環境帶來了無法估量的災難,釀成人類和平利用核能歷史上最慘痛的悲劇。
國際上最先報告核泄漏事故的是瑞典核電站的監控人員。蘇聯官方于28日21時才公布了有關消息,5月1日還照常在基輔市舉行盛大的節日游行。
據統計,歐洲地區遭受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污染的區域達20萬平方公里。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遭污染的土地約14.5萬平方公里,受災人數為650多萬。核輻射直接導致27萬人罹患癌癥,其中9.3萬人很快死亡。參加救災的60萬人中,有7000人在5年內相繼死亡,其中包括一些核科學家和核工作者。因核災難而致死人數總計約50萬。烏克蘭有近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遭核污染,13萬居民被迫遷移,受災人數達300多萬,特別是兒童患放射性疾病的比例急劇增高。俄羅斯受污染耕地為2900平方公里,森林達98萬公頃,至今仍有4300個村鎮、近150萬人未能撤離污染區。受災最重的要數白俄羅斯。由于當時正好向西北方向刮風,并下了一場暴雨(據說是人工降雨),大量含有核放射性物質的塵埃飄落在位于切爾諾貝利北部的白俄羅斯境內。白俄羅斯約23%的國土被污染,400多個居民點變成無人區,另有200萬人包括47萬名兒童至今仍生活在污染區內。

核電站的總經理和工作人員在門口迎接我們。基輔市市長特地趕來會見使節參觀團。市長對我們來切爾諾貝利表示歡迎后指出,最近某些媒體散布謠言,稱電站3號機組又出現了核泄漏。因此,使節們是冒著“風險”來參觀的。他同時說,希望西方國家盡快兌現提供財政援助的承諾,以便烏克蘭政府能如期安全關閉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總經理向我們詳細介紹了有關核電站的情況。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當時有職工5000多人,居住在距切爾諾貝利50公里外的新城——斯拉烏季奇市。電站始建于1970年,共有4座裝機容量為1000兆瓦的石墨型核反應堆,是蘇聯時期世界上最大的核電站。1號、2號、3號、4號機組分別于1977年、1978年、1983年、1984年并網發電。沒想到,最新的4號機組在1986年會出事故,爆炸引發的大火濃煙整整持續了10天。當時十萬火急,飛機從高空向燃燒中的核反應堆拋投水泥和鋼筋,以便構筑一個厚達幾米的保護罩,形成封蓋反應堆的“石棺”。
烏克蘭煤炭資源豐富,但清潔能源嚴重缺乏,在切爾諾貝利興建這座大型核電站正是出于彌補清潔能源不足的考慮。1986年4號機組發生事故后,烏克蘭因供電緊張,其他三個機組不得不冒著極大的安全風險繼續運行。2號機組于1991年又發生火災事故,此后一直處于非工作狀態;1號機組運行到1996年關閉;3號機組按計劃應于2000年底前關閉,可經過幾次檢修后仍在運行。專家們對“石棺”內殘留的核燃料狀況知之甚少,估計還有100噸左右。在雨水的長期滲透侵蝕下,“石棺”已出現裂縫,其頂板有坍塌的危險。而且,核燃料也會產生某種自然反應。因此,徹底改造“石棺”成了最緊迫的難題。1997年,西方七國集團首腦會議要求烏克蘭政府完全關閉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并承諾籌集10億美元的資金,幫助建造一個重達1.8萬噸的巨大鋼棚,用以屏蔽整個“石棺”,保護核電站周圍免受放射性物質的危害。但改造“石棺”所需的大量資金遠未到位,核電站能否如期關閉也成了問題。
聽了核電站負責人的介紹,使節們的心情變得沉重起來。大家未提任何問題,都默默地跟在核電站負責人后面,參觀了展廳中的核電站模型和3號機組控制室。自4號機組發生事故后,與3號機組相鄰并連接在一起的通道已被封堵。我們順著一條長廊返回主樓的門口,坐上汽車前往4號機組參觀。
令世人驚愕的“石棺”
不一會兒,一座造型奇特的巨大灰色建筑體呈現在我們眼前。四周有圍墻和鐵絲網,戒備森嚴,一看便能猜出,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石棺”。“石棺”長160米,寬110米,高75米,里面掩埋的就是4號機組核反應堆。當年,為撲滅反應堆爆炸而引起的熊熊烈火,政府動用了軍隊和直升機。搶險人員當時毫不知情,身上沒有任何防護設備。經過200多個晝夜的奮戰,投入5000多噸鋼材,澆筑了36萬噸混凝土,才構筑起這座奇特的“石棺”。
緊挨著圍墻處有一個專門為進出禁區而建的二層小樓,樓上設有觀察“石棺”的望臺。據介紹,來這里參觀的代表團一般都是到望臺上看一眼“石棺”,或拍一張照片即匆匆離去。因為“石棺”周圍有核輻射,通常不安排到實地參觀。當然,考慮到逗留時間很短,并采取嚴格的防范措施,一般不會危及人體健康。在陪同人員的指導下,我們在更衣室換上潔白的襯衣、襯褲、線襪和工作服,穿上黑色棉外套和高筒套鞋,并戴上防毒口罩、白帽、手套和頭盔。最后,還發給我們每人一支放射性劑量測試筆。核電站工作人員一再提醒說,進入4號機組控制室時,要一個緊跟著一個,不許停留,不許接觸任何物體。
一踏進潮濕昏暗的控制室,我仿佛一下子就屏住了呼吸。這里與剛才參觀3號機組時看到的寬敞明亮的控制室大廳和令人眼花繚亂的精密儀表的景象有著天壤之別:控制臺上密密麻麻的儀表都被拆得七零八落,殘存的設備也盡是銹跡斑斑,油漆剝落的墻壁上還隱約可見搶險人員簽名留念時的字跡……我們在里面總共也沒待上幾分鐘,卻覺得過了好長時間。
參觀結束時,核電站工作人員認真查看了我們身上攜帶的測試筆,并告知一切正常,所受的輻射量只相當于在醫院進行一次X光透視檢查。大家臉上的緊張神情隨之煙消云散了,但圍繞那場核災難的重重迷霧卻一直籠罩在人們的心頭。
核輻射依然是個未知數
記得剛來烏克蘭時,使團中有關核污染的傳聞很多,不少人談“核”色變。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位于第聶伯河上游,河水遭受放射性物質污染后,不能直接飲用。自由市場上的東西也不能隨意采購,因為很難保證沒有受到污染。有的使館還請自己國內專家來測試所在地區的核污染情況。
在“石棺”前合影留念后,我特意向核電站的管理人員提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1986年的那場核事故的真實原因到底是什么?對方稱,當時蘇聯官方宣布,這是由于核電站工作人員違規操作而引起的。事發后,蘇共中央下令將有關的檔案、文件、照片等全部資料調往莫斯科秘密封存,至今仍未解密。
第二個問題是,這種放射性污染究竟什么時候才能徹底消除?有人回答說,至少100年。有人則表示,從自然規律看,核輻射會逐年衰減,但實際上這兒(他指了一下“石棺”)恐怕永遠都是一個未知數。

人類不能因噎廢食
核能技術是一門深奧的高端科學,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逐漸開發掌握并加以和平利用。核電站是利用核反應堆內原子核的可控鏈式裂變反應所產生的熱能來發電或發電兼供熱的動力設施。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后果是慘重的,但人類并未因噎廢食,而是從中汲取教訓,更加注意科學、安全地運用核技術。
經過20多年的協同努力,如今的核電技術及電站運行方式日臻完善。據統計,目前世界上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有核電站,共有440多座核反應堆在運行,總凈功率為406136兆瓦。正在建造的核反應堆有30余座。核電占世界總發電量的16%左右,預計今后這個比例還會增加。
此次日本核泄漏事故給人類和平利用核能帶來致命性打擊,世界核電事業有可能再次陷入低潮。但核能是一種經濟清潔能源,安全利用核能是人類生存與社會發展的必然抉擇。隨著全球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長以及人們對氣候變化的憂慮不斷加深,生產成本較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較少、安全性能相對較高的核能優勢日益突出。從長遠看,經過一番曲折之后,核能的安全利用必將更加發展。
當務之急是,在進一步提高核電技術安全系數的同時,切實加緊研究有效應對各種突發核事故的關鍵技術和設備,真正確保萬無一失。愿切爾諾貝利和福島核泄漏災難的警鐘長鳴,讓和平利用核能的事業為全人類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