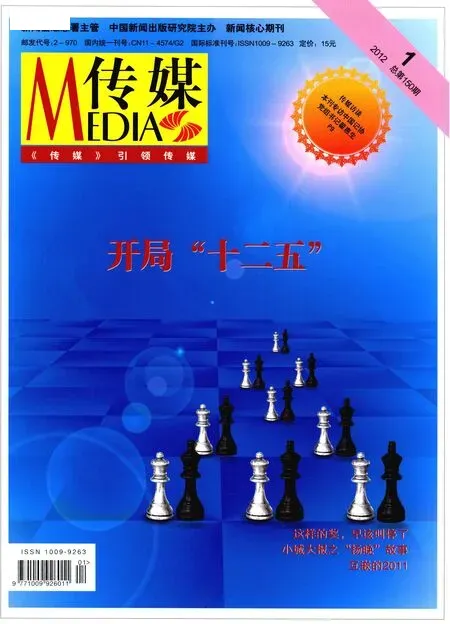“井噴”的沖擊
——2011年微博傳播及其指向
文/鄧炘炘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傳播系主任
如果說2010年是中國內地的“微博元年”,2011年就是微博“井噴之年”。新浪微博2009年試運行,騰訊、百度等隨后紛紛開通微博服務,時間大體集中在2010年中期。2010年9月9日,新浪首發《中國微博元年市場白皮書》,吹響內地微博熱浪的號角。到2010年底,百度、盛大、騰訊、新浪、網易、搜狐等中國主流互聯網企業均積極投身這一大潮。值得一提的是,人民網的“人民微博”于2010年2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公測,這是中央重點新聞網站推出的首家微博服務,反應可謂相當迅速。
陡然崛起 急速擴張
2010年微博陡然崛起,2011年微博的“沸騰”更出乎意外,迄今為止微博應用仍在持續擴張。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報告,截至2011年6月底,內地微博用戶數達到1.95億,對比2010年底的6311萬,增幅高達208.9%,成為年內用戶增長最快的互聯網應用模式;微博用戶在總網民中的比重從13.8%提升到40.2%;手機網民使用微博的比重從2010年末的15.5%上升至34%。報告數據還顯示,中國內地網民總規模為4.85億,較2010年底只增加 2770萬人,增幅僅為6.1%,顯示內地網民增長已進入平緩期;然而當大部分網絡應用的增長率有所下滑或平緩爬升之時,微博用戶數卻陡然上揚,反映出時下網民對互聯網絡傳播方式的強烈的選擇性和偏好性——內地網民的信息活動,正在大步奔向微博化或移動微博化。
2011年中國內地微博傳播的年度特色是:由龐大的微博用戶群體所托起的、數量眾多、紛繁雜亂的微博熱點事件,令人目不暇接難以招架。如何看待這一“亂象”呢?出于敘述與討論的方便,這里采取分類分組例舉的梳理方式,且只涉及2011年微博事件的代表者,并偏重新聞傳播。
組織與行動的力量。個體微博能引發或促成群體性、有目標指向的行為事件,這種事件在2011年數次出現,未來仍會不斷出現。于建嶸微博發起“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鄧飛微博發起為貧困地區學童提供免費午餐,某網友微博呼吁到京郊高速路上攔車救狗等活動,都屬這類事件的代表。上述三個例子中,微博的發起皆具有個體性和自發性,并且都因得到網友的廣泛支持和關注而成為迅速膨脹的熱點。前兩個事件還獲得官方的跟進和響應,使問題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決。“攔車救狗”事件則因爭論較多,保持在“街談巷議”式的民間狀態。可見,一旦個人發出的微博議題具有社會性和公共性時,它就不但表達意見態度,還可能成為行動組織工具,引發社會響應和群體行為。
有研究提示,包括微博在內的社交網絡用戶最多的城市或國家,往往并不是權威社交網站總部所在城市,甚至所在國。例如,有學者指出,臉譜網Facebook總部在美國加州,而其用戶最多最活躍的地方則是突尼斯、土耳其等。社交網絡在一些社會環境較為動蕩的國家或區域,使用往往更為普遍。這種錯位現象既顯示出社交網絡的傳播生命力,也顯示出網絡傳播話語權與社會現實話語權及社會組織架構之間的錯位離散程度。
“輕率”遭遇“拍磚”。本意為“卡拉OK”的個體微博內容,卻招來社會熱議和廣泛抨擊,成為網民追責和猛烈“拍磚”的對象。年內比較典型的例子有“郭美美炫富”、“蠢局長直播開房”、“潘石屹微博調侃蘋果公司”等。這類事件的共性是:首發微博內容似乎都具有自我表達的“輕松”,發出后產生的社會震動和反響顯然出乎首發者的意料,連慣于面對媒體和擅長使用微博的潘石屹都未能瀟灑。事實上,在“輕松”和“意外”這兩點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跳躍落差”:網民們把首發者的“輕松”放到客觀現實中解讀,致使有關微博內容中的荒謬、扭曲和丑陋赫然凸顯,結果引來更多的參與和圍觀,形成線上線下巨大的社會輿論。
網絡關注由此出發,但其鋒芒往往指向更復雜更深層的社會難題和爭議現象。眾人所見的是,“郭美美炫富”扯出中國紅十字會運作的窘態和尷尬,“蠢局長直播開房”暴露出政府官員素質及其腐敗墮落指數,而老潘隨口說要蘋果公司減價惠民的輕巧話,使他轉瞬成了被譏諷的房地產大鱷。這些“跳躍”或“騰挪”,都說明微博話語與社會歷史現實之密不可分,某些個人微博的行為或意見,一經發布就脫離了微博主個體的主觀定義控制;網絡傳播不僅可以放大始發者的信息或意見,往往還可以借此導出其他始料不及的含義、問題或指向。不能理解其中復雜的交錯關系,任何指責網民小題大做的人,都可能會在某個時刻某個場合墜入與前例微博主類似的困境或尷尬。
微博的新聞報道空間。微博具有“新聞報道”功能,這在2011年的很多重大事件中都有體現,而且數量很多、影響很廣,比較突出者有“甬溫動車追尾”、“中石化天價酒”、“藥家鑫案”、“故宮夜盜”、“南京梧桐樹事件”等。微博參與新聞報道的作用,一般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正規新聞傳媒的“官方微博”,它是專業新聞工作的延伸;當專業傳媒機構“正常發揮”作用時,普通網友微博只具有輔助性、次要性或初級性報道的作用,大多集中在初始新聞信息的提供和補充方面。二是一旦普通個體微博“喧賓奪主”,持續地成為相關新聞事件中的報道主角或關鍵引領者,則說明專業傳媒機構此時此刻缺位,即失語或“被失語”。

在2011年的微博事件中,網民微博發揮了比較突出的信息披露、追蹤或直播作用。在這種“微博報道”的參與和迫壓下,有些事件暫且得到“積極化解”,如南京梧桐樹事件。但是多數事件則因缺少重要當事方的后續反應和專業傳媒的持續跟進,而進入不了了之的“自然淡化”狀態。而這后一種傳播狀態往往會消蝕有關當事方、責任方和專業新聞傳媒機構的誠信度,從而給個體微博新聞傳播添加更多的可信度。因此,自發式草根類微博的“新聞報道”能量和空間有多大,其實要看社會機構和專業傳媒的“專業主義”在歷史和現實維度中的表現如何,亦要看它們“放棄”的幅度和力度有多大。
觀照微博的若干新視角
2011年的熱點微博事件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民生等深層次問題。其中一些并非由主流傳媒機構首發,而是由微博推動和轉發,進而成為受關注的社會議題。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這種微博傳播能量大,很難用“無序”、“亂象”、“炒作”、“道德失范”、“價值缺失”等字眼一筆帶過。對2011年微博傳播,各方難有共識,也沒有非黑即白的清晰判斷。

新浪微博用戶數變化趨勢(xueqiu.com)
改革的宏觀任務單。解讀中國問題要有改革的思考維度,更要知曉當前改革和發展的大任務單。內地的微博傳播不能直接接入全球Twitter網站服務,而是使用了國內的替代版“微博”,這實際是一種防火安全墻式的操作模式。中國互聯網絡目前的管理方針是:積極利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2011年5月,國務院新成立了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有關負責人表示,該辦公室將堅決貫徹上述16字方針,切實把互聯網建設好、利用好、管理好。同年10月,《中共中央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發展現代傳播體系”,“建設國家新媒體集成播控平臺”,“加強對社交網絡和即時通信工具等的引導和管理,規范網上信息傳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網絡環境”等具體目標。落實改革推進發展,把歷史自省意識代入互聯網傳播時代,具體地置于微博傳播環境之中,是更實際也是更為艱巨的硬任務。
政務微博“活躍”+“休眠”。2011年也是內地政務微博和官員微博活躍之年。根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2011年的研究報告,2011年微博“成為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的法寶和依靠”,是“信息時代貫徹群眾路線不可回避也必須爭取的重要陣地”。例如浙江省各級部門和廣東省公安廳,都有突出表現。2011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學和新浪微博合作,推出《2011年中國政務微博報告》。在肯定啟用政務微博的積極效應的同時,上海交大的報告也指出了目前政務微博還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在地域、行政級別、職能部門等方面分布不平衡,呈結構性失調;發布時效性差,技巧不熟練;定位不清,多作為信息發布平臺,未充分與公眾積極互動,內容官化或用語欠當;缺乏制度化安排,民眾微博問政較難,等等。推廣政務微博,促進地方民主化進程,顯然還有一段路要走。
作為一種政府信息傳播的延伸,政務微博是對原有政務運行的一種疊加、強化或者改善。政務微博也會牽扯出許多復雜的新問題新關系,譬如,官員實名微博,特別是高級政府官員微博,如何實現及時經常的發布與回復,在眼下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網絡傳播上需要新思維新制度。目前,主流媒體和以微博為代表的網上傳播,似乎一定程度上呈現平行并存樣式。固守傳統的管理思維和應對方式,很容易導致方鑿圓枘之誤。因為,傳統媒體是一對多的上下傳播模式,“把關人”的管控作用至為關鍵,也極為有效,可以做到“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網絡傳播是多向多元的上下左右交叉互動,就會出現“一夫難把萬千關”的局面。
在信息社會,因信息大量擁塞和冗余,信息本身已經變得不那么重要了,而信度則成為傳播關系和過程中最重要的元素,“誰說的”比“說的是什么”更重要。傳播效力和話語主導權主要靠信度推動,靠信度背后的基本價值觀和真誠度指數來支撐,網上和網下傳播概莫能外。問題是,當許多專業傳媒機構的信度和誠信建設普遍滑坡,經常失語無語,社會信任度下降時,它們與網上紛雜的信息和觀點在信度上的差距就會縮小。鐵道部原新聞發言人王勇平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就是高估了自身信度資源的典型。
網絡被普遍認為是謠言的“溫床”,對這一判斷,不應做簡單化的認同。謠言大面積流布的社會環境基礎,首先是社會誠信的普遍下降。微博確為傳謠提供了方便,但問題的關鍵并不在此。網絡傳播的特點之一是個體網絡用戶是傳/受身份同一的一體兩面,同為傳/受方。當某一“不實信息”在網上被千萬人主動轉發之時,所有轉發者都是協作人,這種“眾人拾柴”效應推動了該信息的擴散和放大,客觀上造成了謠言傳播的社會效果。傳統社會中,謠言傳播的關鍵環節在始發者,而在互聯網時代,謠言傳播的關鍵環節在轉發者。事實上,網上的不實信息大量存在——包括一些由專業傳媒機構發布的;但如果沒有被大規模轉發,它們并沒有被關注,也就沒有被認定是“謠言”。因此,“網上謠言”的出現,不在首發而在轉發。如果謠言的危害度是由傳播范圍決定的,網上傳謠者(轉發者)的責任要比網下大很多。
值得反問的是:為什么眾人都熱衷相信并傳播那些“謠言”呢?為什么沒有更可信的媒體或機構及時澄清,或者成為民眾主動尋證的訴求對象?探究普通民眾在類似情境中的集體心理,認識和處理在這類微博事件中所折射出的深層次問題,可能是比處罰個別肇事者更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