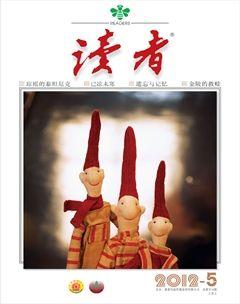時光遺忘之地
馬伯庸
我家小區北側橫亙著一條寬闊的馬路,叫做朝陽路,這條路是北京到通州的重要交通樞紐。我2005年來到北京,那時候朝陽路從青年路口到民航醫院之間的路面被挖成了連綿的溝塹,過往車流只能勉為其難地從兩邊極為狹窄的臨時通道前進。后來別人告訴我,朝陽路馬上要修公交快速路,正在施工。
時光飛逝如白駒過隙,很快一年時間過去了,但朝陽路的這一段工地依然如故,和我第一次與它相見時一樣,塵土飛揚,汽車擁堵。
又一年過去了。我以為它會隨著北京奧運會的臨近而有所改變,可我錯了,北京奧運會震撼了整個世界,但它撼不動朝陽路的這片工地。朝陽路工地安靜地橫亙在馬路當中,只是偶爾會來兩三個工人翻動一下土地。
到了2009年的國慶大閱兵之前,我欣慰地發現,它終于發生了變化。有許多工人過來,挖出了更多的溝渠,在大路兩旁鏟出許多大坑,紅褐色的泥土堆積在周圍,峰巒起伏。然后……然后就沒動靜了。它變得比從前更加雄偉,更加險峻,更加莫名其妙。
那些土堆在春季會被吹起紛紛揚揚的塵土;在夏天,工地之間會匯聚出一個個積水坑,可以養養金魚或者蚊蟲;在秋天倒是沒造成什么麻煩,興致好的人可以登高望遠,悠閑地望著山下堵成一團的車流;到了冬天,一旦下了雪,這里就會變得像1944年的蘇聯戰場,泥濘不堪,可以困住一到兩個德國裝甲連。
這個橫亙在大路當中的工地如同一塊被時光遺忘的領域,任憑時間在旁邊嗖嗖地流逝,即使朝陽區其他路段的快速公交線已初具雛形,它仍舊巋然不動。我甚至懷疑,市政部門已經把這件事忘記了。或許要等到許多年以后,一個頭發斑白的設計師偶爾翻開塵封已久的規劃圖紙,才會想起曾經有過這么一檔事。
一直到了2011年年初,忽然來了一大堆工人,就像是給自己家裝修一樣,夜以繼日熱火朝天地干著活。沒幾天工夫,整條道路煥然一新。
我沒有指責他們“才1個月的工作量,你們怎么花了6年時間來干”,漫長的等待讓我的心態變得平和。我叫上媳婦,對她說咱們去看一看新路吧。
然后我們看到朝陽路上塵土飛揚,無數溝塹縱橫,大堆大堆的新鮮泥土被拋成群山,焦慮的司機們擁堵在一起,喇叭聲四起。
一位正在忙活的工人告訴我:“這里建好以后才發現沒有埋設管道,所以得重新挖開。”
我向他道謝,然后默默地回了家。
(黎遇劍摘自《看天下》2011年第27期,圖選自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國際藏書票藝術》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