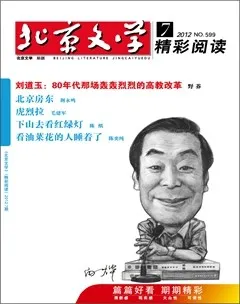中國新詩如何浴火重生
單純的重返古典,或者簡單地模仿西方,都不是解決新詩的靈丹妙藥。只有所有關心新詩發展前途的人們,共同地認真思考,將中西詩歌的傳統合理地融入詩中,同時找到對當下中國的最佳表現,也許才是新詩的唯一出路!
翻開《詩刊》《星星》這些中國的頂級詩歌刊物,我們細心品讀后不難發現,其中雖不乏實力不俗的詩人,但也有很多詩歌真像是把散文分行后的結果。怎么看待當下詩歌界普遍存在的這種魚龍混雜的情況?有人認為新詩好得很,也有人認為糟得很。
然而,在我看來,對新詩現狀的簡單臧否,對新詩的發展并不一定有什么幫助。眾所周知,新詩是一個舶來品,是中國詩歌在五四時期發生的一個裂變。所謂“不破不立”,也就是說“破”是為了“立”。不過,新詩的開拓者們盡管解決了“破”的問題,關于“立”的問題卻似乎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除了上世紀中國的動蕩不安之外,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不應忽視:新詩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處于不斷探索中,這常常使得一種有價值的藝術探索剛剛開始,還未來得及走向成熟,很快就被另一種探索所掩蓋,比如北島之于后朦朧詩。因此,盡管前人對新詩付出了艱辛的探索,但他們所獲得的教訓似乎遠大于收獲。我不知道這是新詩的榮幸,還是悲哀?
既然新詩的現狀如此不佳,是不是我們應該拋棄新詩,重返古典詩歌的殿堂?以我之見,這未必就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新詩的現狀。舉個簡單的例子,但凡對古代詩歌有所了解者,都會覺得古代詩歌總體上是講求含蓄的,切忌直白淺露。然而,時下的許多詩作中偏偏十分直白淺露,仿佛又回到了五四時期的早期白話詩的階段,就好像作者沒有讀過一首古詩(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也許有人會稱贊上述這些毫無詩味的詩作,認為它們通俗易懂,貼近讀者。不過,我覺得這種說法首先是把含蓄與晦澀混淆了。在我看來,含蓄不是讓讀者完全讀不懂,而是充分調動讀者的主動性,使他們盡可能地從詩作中讀出一些含義。當然,含蓄是有限度的;一旦過度,就容易走向晦澀。我想不會有人否認李商隱的詩是含蓄的,但很少有人說他的詩是晦澀的。因為它們盡管朦朧、多義,卻可以讓讀者讀出一些明確的含義,盡管未必是全部含義。此外,這種說法也無形中低估了讀者。在我看來,詩歌的一大魅力就是讓讀者通過一定的努力,對詩歌作出解讀。只要詩歌不是過分晦澀,我相信大部分讀者更愿意去讀那些有一定挑戰性的詩作,否則很難解釋為什么那么多人喜歡閱讀李商隱的詩。
現代人的情感已經變得極其復雜,比如對科技既迷戀又排斥,對鄉村既憧憬又抗拒。所以不管李商隱的詩歌有多么的優秀,這些復雜的情感都已很難在他的詩中得到真實、完整的表現。此外,現代詩人主體意識的張揚,也難以被他的詩歌所表現,甚至正是它所排斥的。
但是,古代詩歌并非要被我們完全遺棄。《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是一首典型的現代新詩。然而,在這首新詩中,我們卻可以找到一些古典詩歌的痕跡,比如在詩中反復出現的“丁香”這個意象。它在古詩中常被用來形容哀愁,被用在這首新詩中,不僅絲毫未影響質量,反而使這首詩成為新詩充分吸收傳統詩歌營養的典范。這說明,如果我們能將古詩中的有益成分加以改造或者化用,對新詩的發展也許不無裨益。
2011年歲末,瑞典詩人托馬斯·特蘭斯特勒默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一事,這使得許多中國詩人再次提出向西方學習,特別是向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學習。在他們看來,似乎這樣就可以解決我們當下詩歌的困局,縮短我們與世界詩歌的距離。然而,我對此卻并不這么樂觀。事實上,在新詩發展史上,我們不乏向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學習的嘗試,比如上世紀20年代以李金發等人為代表的象征詩派。這些詩人大多都受到西方前期象征派詩人的不同影響,注意意象的象征性,講究情調的暗示性,追求語言傳達的新奇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新詩的現代化進程,正是從他們開始的。然而,他們的創作很快走向沉寂。除了因為他們的詩作遠離時代主潮,更重要的是他們并未將傳統與西方詩歌的營養加以融合,而只是一種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簡單模仿。與之相反,以上面提到的戴望舒為代表的現代詩派,卻因其詩作對中西詩歌營養進行了完美融合,從而受到了許多人的肯定,比如上面提到的《雨巷》。
所以,單純地重返古典,或者簡單地模仿西方,都不是解決新詩的靈丹妙藥。只有所有關心新詩發展前途的人們,共同地認真思考,將中西詩歌的傳統合理地融入詩中,同時找到對當下中國的最佳表現,也許才是新詩的唯一出路!
責任編輯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