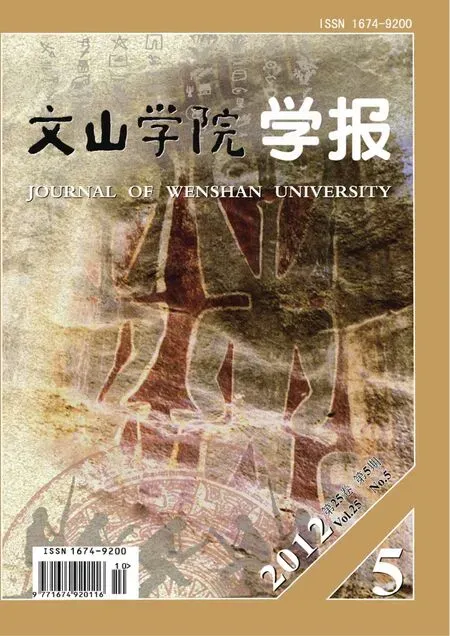論華企云的邊疆研究
蔣正虎
(云南民族大學 人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031)
一、華企云及其邊疆論述
華企云是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國邊疆研究出力最多、勞績最大的學者之一,用時人的話說,是“國內對邊疆問題最有研究的人”[1],其著作《中國邊疆》,亦被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是近代中國第一部從整體上研究中國邊疆的著述[2]。然而對于華企云的生平,目前卻所知甚少。時下的邊疆研究人員固未論及,時人亦語焉不詳。如戴季陶稱:“華君企云,向習史地,留意研究中國邊疆問題者垂六七年”[3];《新亞細亞》月刊中,一署名“英”的人說:“企云同志精研史地,專心致志于邊疆問題之研究者垂六七年,……所草邊疆問題之稿件,自滿蒙而至云貴,蓋已將中國之邊疆問題網羅無遺。”[4]而在《中國邊疆》一書的出版預告里則說:“本書作者研究中國邊疆問題有年,曾在上海大東書局發刊邊疆問題專著數種,早已膾炙人口。”[5]《邊事研究》雜志也僅稱“華企云君,關于邊疆著述,甚為豐富”[6]而已。筆者經多方查找,所得不過如此。其他比如其籍貫、生卒年份、學習經歷、人際交往等,幾乎一無所獲。
從目前筆者所掌握的材料來看,華企云邊疆研究之生涯,集中于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而抗戰爆發之后中國學界熱衷邊疆問題之探討,華反而似未曾參與。30年代末至40年代有代表性的邊疆研究期刊如《西南邊疆》、《邊政公論》、《邊疆研究通訊》、《中國邊疆》等,其中并無華企云的文章。華慣常發文的《邊事研究》,自1938年移渝出版之后,亦再無華企云蹤影。1944年《新亞細亞》復刊后,原先作為其資深撰稿人的華企云也沒有出現。經筆者多方搜檢,署名“華企云”最晚公開發表的文章,系刊于1941年《永安》月刊之《臺灣琉球越南識小錄》、《姓名與避諱》和《常言俗語輯》,均系短篇小文,且未審其作者與著《中國邊疆》之華企云是否為同一人。《永安》月刊系1939年在淪陷區上海出版之刊物,如果上述《臺灣琉球越南識小錄》之作者確系本文所言之華企云,那么可以肯定,抗戰爆發之后,華企云并未內遷。而如華企云未內遷,則其沒有參與四十年代的邊疆研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抗戰勝利之后,華企云沒有出現,邊疆研究界亦再沒有提及,然則他很可能卒于抗戰期間。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華企云之邊疆研究相當活躍。據筆者粗略統計,自1931年至1937年間,除《東方漫游記》、《馬來搜奇錄》、《亞洲之再生》等譯著外,華企云于《新亞細亞》等期刊發表文章共計四十余篇,其中多有萬言以上長文,而1938年之后,華企云竟似突然消失了。
以1931年為界,大致可將華氏之研究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要體現在邊疆論著的編輯上。自1929-1932年間,華企云所編輯之邊疆論著見表1。

表1 1929-1932年間華企云所編輯之邊疆論著
其中,由大東書局所出版者,以“邊疆問題叢書”為名刊行,而《中國邊疆》一書,大抵系將刊發于《新亞細亞》前四卷之文章組合而成。此外,在《新亞細亞》第一卷第三期《華企云同志邊疆問題之著作》及氏著《中國邊疆》“本書著者之其他著譯”中,提到尚有《邊疆游記》、《邊疆探險記》和《邊疆風土記》等書或在“集稿中”,或在“編輯中”,華本人也說“異日有閑,更當從事編譯中西人士所著邊疆游記,或風土考察記等書籍,以餉閱者”[7](P2),但筆者未見,或并未出版,或即后來在《新亞細亞》所連載之《天方歷險記》等書。另外,夏威在1941年出版的《中國疆域拓展史》中,提到他參考了華企云著《西北邊疆》一書,但該書筆者亦未見。
自1932年開始,華企云關于邊疆之著述,均以論文形式出現,其中刊發于《新亞細亞》和《邊事研究》的有28篇(連載以1篇計),另外《平等雜志》、《浙江青年》、《東方雜志》以及《申報》、《民國日報》、《新聞報》等報刊,也刊發過零星文章。此外,筆者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錢業月報》上發現亦有署名“華企云”的一批文章。雖然該刊并未對其作者做介紹,但從這些文章的內容和風格來看,當為本文所稱之華企云無疑。如《日俄與滿蒙》(第八卷第五號)、《論滿洲之天然富源》(第八卷第十二號,1929年1月)、《滿洲之鹽與日本之需要》(第十卷第三號,1930年3月)等,均不失“邊疆”之旨。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并沒有證據表明華企云曾對邊疆做過實地調查,華本人的著述中也從未提及,王明珂說華企云在江心坡做過 “調查”①,未知其所據為何。
縱觀華企云的邊疆論述,前期主要為介紹性質,內容不外乎邊疆各地之地理、交通、物產、經濟與外交關系等,而尤重外交。如《滿蒙問題》“分三編,首述滿蒙之地理,次述滿蒙之經濟,末述滿蒙之外交”[8](P1);《新疆問題》“分三編,曰從史地經濟上觀察新疆,曰從種族龐雜上觀察新疆,曰從外交關系上觀察新疆”[7](P1),其余幾部著作亦如是。從內容上來看,華企云前期的著作,恐怕不能算是精深的學術研究,而更像是當時的暢銷書,但是,這些著述主要的價值恐怕也就在于其通俗性。或者說,華企云前期的邊疆研究,其首要的貢獻并非在于其研究之具體內容,而在于其眼光之敏銳。在主流學界關注并投入邊疆研究之前的差不多十年,即“已將中國之邊疆問題網羅無遺”,實屬難能可貴。
華企云后期的研究,內容則愈見精審,尤其是《新亞細亞》第七卷以后所載之一組論文,其學術價值恐遠在華氏前期的一系列著作之上。分別是:七卷六期《中國近代邊疆失地史》、八卷三期《中國近代邊疆經略史》、八卷四期《中國近代邊疆政教史》、八卷五期《中國近代邊疆民族志》、九卷二期《中國近代邊疆界務志》、九卷三期《中國近代邊疆外侮志》、九卷四期《中國近代邊疆沿革史》、十卷四期《中國近代邊疆藩屬志》。不過,華氏這里所說的“近代”,大致系指17世紀或者明末清初以來。這一組論文,以孫中山“三民主義”為其理論內核,已經初步將“三民主義”理論與具體的邊疆研究結合起來,顯示了華企云在邊疆研究體系性建設方面的努力。而《總理遺教中邊疆建設之研究》一文,則是20世紀30年代前中期邊疆研究在理論方面的標志性論述。而這可以說是華企云邊疆研究的突破性進展。
二、華企云邊疆研究之主旨
20世紀30年代,不論國民政府 “開發西北”的政策也好,還是社會上對于邊疆問題的熱衷也好,其核心實在于國防問題,其他諸如邊疆政教問題、民族問題、開發建設問題等,均以此為鵠的。但華企云則更進一步,將邊疆視為整個中華民族生存之基礎。用華企云自己的話說:“中國民族便要不能生存在世界之上,我們不要求生存則已,倘使要想生存的話,那末便首先要來研究邊疆和怎樣鞏固國防,怎樣從事開發建設。”[9]華企云之邊疆研究,以此為起點,亦以此為終點。以邊疆為中國立國之基點,可將華氏研究之主旨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移民實邊,鞏固國防
20世紀2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上對于中國的人口問題似乎都有一種擔憂。這種擔憂的核心,就在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如20年代中期,馮玉祥即于西北“提倡墾務,各省爭先恐后,均愿受之一塵,耕于其地”[10],并辦有“中華墾殖公司”及“墾殖學社”,以達實邊之效。30年代之后,人口分布不平衡的問題進一步引起了學者的注意,如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就說,“中國人口是集中在狠(很)少數的幾個地方”,“百分之八十三強”的人口集中于“百分之十七弱”的土地上,認為“人口集中太密故生活低下”。[11]有雜志也稱西北“為中國沿海各省過剩人口之唯一出路”[12]。而華企云對于邊疆問題的關注,其主旨之一,也是因為中國人口分布不平衡對于國防穩定的影響問題。在1929年的《滿蒙問題》中,他說:“無論本部各省有人口過剩之患,藉曰過庶矣,亦可移植滿蒙以救濟之。此則吾人當竭力鼓吹本部人口移植前往者矣。”[8](P13)而在 1931 年的《新疆問題》中,他更進一步認為,要“籌邊固圉”,首先即是“移民殖邊”[7](P167)。在 1932 年的《岌岌可危的中國邊疆》一文里,他也認為,就“開發建設和固圉”而言,“先要移植一批閑散軍民前往辦理兵民屯墾”[9]。而到1937年,他對于“籌邊固圉”又有了新的認識。他將“將來的邊防系統”作如下之歸納:“籌邊”中的行殖邊、舉屯田、立鎮守和重諜報等四項舉措組成了邊防系統中的交通和政治方面,而“固圉”中的筑城池、置塞徼、遣戍守和制要地等四項措施則構成了邊防系統中的設防和堡壘方面。顯然,在這一“系統”中,首先就是“行殖邊、舉屯田”。
因此,“邊疆正是人口稀少而地大物博的疆土。正維這地廣人稀的現象,弄得比鄰的帝國主義者無時無刻不是乘機窺隙,狡焉思啟”[9]。中華民族想要生存,務須求國防之穩固,而國防之穩固,首要在于移民殖邊。
其二,團結各族,共謀發展
誠為華企云所見,邊疆各民族所居處之土地面積,“要占到全中國二分之一強一些”,廣大的邊疆地區既為立國之基,則團結邊疆滿、回、藏、蒙、苗等“五族”,就成為必須。而民族團結之觀念,亦貫穿于華企云整個邊疆研究生涯。該觀念之核心,則是以各民族之起源來論證民族團結之基礎。
華企云的民族觀念,其先依梁啟超與西方學者,較為支持“多元混血論”。認為中華民族由漢滿蒙回藏苗等族組成,而邊疆各民族也是混血而來。如說蒙族,“它的來源是東胡、突厥、氐羌,三大族的北方混血種,但是它總不失其為中華民族中大族之一。漢、滿、蒙、回、藏、苗六大族構成的中國之中,它也是基本各族啊”[13]。說藏族,則認為“今日之西藏族,其源流上實為土著與外來混血民族者,當可斷定無訛矣”[14]。后則折中于孫中山,認為中華各民族中,蒙族和滿族與漢族實為同源之民族。他說,匈奴與蒙古同源,據《史記》所載,匈奴系夏后氏之苗裔,“然則漢蒙兩族,顯出同源可知,只于匈奴一支居于大漠,漢族一支居于內部,……則同族之淵源,固可自信弗疑焉。”[15]又說:“滿族……實出于古帝少昊,與漢族有同源異地之關系。蒙族……亦為夏后氏之苗裔”,回族之先祖匈奴,“與漢族之關系最稱密切”,藏族“與漢族亦息息相關”,苗族“則當漢族未盛以前,原為中原土著”[16]。這是從歷史上論證民族團結之根據,也可以說是對“三民主義”中民族觀念的發揮。在這些表述中,有的前后并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如關于蒙族與回族之先祖問題),但這恰可以說明華企云在論證民族團結方面的努力。
在具體論述中,華也處處以民族團結為念。如說到新疆回民,則說:“新疆之民眾既同為中國之國民,則吾人對于新疆之利益,應當予以保障。……將來欲求國民革命之完成,則當非中國境內各民族之努力不可,新疆回民革命性素極豐富,更為實行國民革命之重要份子。”[17]說到蒙族,則認為:“漢族之與蒙族,同是中華民族,漢族應以蒙族的力量來捍衛祖國,……蓋惟有在蒙漢和衷共濟的合作條件之下,才可以應付當前的國難!”[17]又說:“集漢滿蒙回藏苗六族之凈化于一家,尤為中華民族復興之根基,全國人士其勿忽視焉。”[18]還說:“中山先生領導之革命光復漢族后,不再主張傳統之攘夷思想,而以各民族之互相提攜為國是,故今日無論漢、滿、蒙、回、藏、苗,均為中華民族之一份子,均應以中華民族為團結合力之標準。”[16]
其三,細敘原委,以明國恥
正如華企云所說:“自從最近一百年以來,國土逐漸逐漸的減少下來,邊疆上大好土地,一步一步經鄰國宰割了去。”[19]因此在他的論述里面,有關邊疆沿革與土地喪失之經過,是其敘述的一個中心環節。每述一地,則征引合約或“密約”原文,務使讀者明了帝國主義之侵略與我喪地之原委。如在《滿蒙問題》中,他敘述中俄外交關系之演變,先敘俄國自彼得大帝以來的開疆拓土,危及英法等國的利益,導致上述國家在東歐、小亞細亞和中亞對俄國的圍堵,以至于“俄國其不能不別圖發展矣,若論別圖發展,當以中國為最佳”[8](P83)。以俄國針對中國東北與西北兩個方向的“發展”為線索,華企云先后引用了尼布楚條約、恰克圖界約、恰克圖市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勘分東界約記、塔城界約、科布多界約、烏里雅蘇臺界約、中俄改定條約、喀希尼密約、巴布羅福條約之原文,將中國喪失于俄國的土地之經過原原本本的敘述出來;而《云南問題》一書中,則敘英法窺我西南的動機:法國是垂涎于我西南之“豐饒礦產”,而英國則冀借云南而“徑入長江”,“溯流而往,更可遍達川、鄂、湘、贛、蘇、皖、浙等省”,以達“爭通商之利”的目的[20](P3-4),是以“舉凡英法帝國主義侵略云南之歷史,與夫對華所訂關于云南之種種不平等條約,無不作扼要之說明”[20]。因此,華企云著述的核心之一,就是“考見晚清以來之邊患,且可以興民族國防安危之思”[21]。
對于已經被“宰割了去”的土地,華企云不時流露出一種激憤與無奈的情緒,所以對于“未定界”的云南邊界,華企云尤其關注。他先后寫有《云南界務問題之研究》(《新亞細亞》五卷四期,1933年4月)、《重勘滇緬南段界務的認識》(《東方雜志》三十二卷十一期,1935年6月)、《滇緬界務之實況》(《邊事研究》二卷一期,1935年6月)、《滇緬北段界務的檢討》(《新亞細亞》十卷一期,1935年7月)、《滇緬南段界務之現狀》(《新亞細亞》十三卷二期,1937年2月)等文章,力表寸土必爭之念。在地理上要實地調查,“把滇緬南段的一丘一壑,一村一寨,都要調查個詳詳細細,作為將來交涉上惟一有力的證據”[22],“要找出滇緬舊界的所在”,“在歷史上,要找出滇省的舊管證據,來維中國的舊有疆土”[23];在民族上,“舉凡已屬中國之明證,或自愿內屬之部落,均需列入版圖”,“已奉正朔如崇祀孔明、王驥等先賢之卡瓦民族,早已自認為與漢族一家,亦不容忽其邊氓,視為化外”[24]。
總之,邊疆與內地實為一個整體,邊疆事關中國民族的生死存亡,“無論在中國人口問題上,在經濟問題上,或是國防問題上,都可以靠解決邊疆問題來得到一個總解決,邊疆問題一經解決,那末三個聯帶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邊疆問題一日不解,那末三個聯帶問題也便一日不決”[9]。
三、華企云對于邊疆研究的理論建設
華企云后期的邊疆研究,有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對于邊疆研究理論方面的重視。華的這種轉變,與新亞細亞學會有密切的關系。雖然在新亞細亞學會歷屆的董事會、監事會、“評議員”中,均無華企云,且目前并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華企云為新亞細亞學會會員,但種種跡象表明,華本人應該是新亞細亞學會的資深會員。其一,自《新亞細亞》1930年創刊,至1937年第十三卷休刊,不算譯作,華于該雜志上發表文章共計二十余篇,數量之多與持續時間之長,除新亞細亞學會精神領袖戴季陶之外,少有其匹;其二,華1932年出版的《滿洲與蒙古》之“小序”,系作于新亞細亞月刊社;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從他本人后期研究的方向和興趣可以看出,華企云本人堅定支持新亞細亞學會的主張,或者說,華后期的著述,根本就是新亞細亞學會主張的具體體現。
新亞細亞學會的主張,可分理論和具體研究兩個方面:在理論上以孫中山“三民主義”為根基;在具體研究中,則“專門研究中國邊疆問題與東方民族問題”[25]。而自新亞細亞學會成立后,華企云的關注重點也隨之從專門關注中國邊疆問題轉為國內與國外并重。在其《中國邊疆》中,第三章與第四章即是關注“東方民族問題”②。這也直接導致了華后期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翻譯西書,在《新亞細亞》中連載(自四卷二期始)。自1932年開始,先后譯有《乾竺特探險記》、《崗強岬歷險記》、《馬來搜奇錄》、《天方歷險記》、《東方漫游記》等五部,且后三者均系長篇連載,此外還有未刊發而獨立成書的《亞洲之再生》。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華企云后期的研究。從這些譯著的名稱就可以看出,這類書籍均為探險獵奇一類,雖然可能有助于當時的國人了解所謂“東方民族”,但相對而言,其價值與中國邊疆研究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20世紀30年代初中期對于邊疆之研究,其理論實基于“三民主義”。華企云亦不例外。但華企云前期之著述,大抵以介紹邊地情形為主,論及邊疆研究理論與政策之處極少。如在《西藏問題》中,僅隱約提到要 “本三民主義之精神,按建國大綱之步驟,從事一切建設”[26](P159)。在《新疆問題》中,則引孫中山之原話而鮮有發揮。而且在骨子里,他也仍然將邊疆少數民族當做是“異族”,比如在《西藏問題》中,他就將內地稱為“我”,而稱西藏為“藏番”。但新亞細亞學會成立之后,或者說華企云邊疆研究后期,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變化的根本,就在于他在研究中有意識地運用和發揮“三民主義”理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三民主義”與邊疆及邊疆建設之關系。華企云對于邊疆建設理論之思考,集中體現于《總理遺教中邊疆建設之研究》,刊于《邊事研究》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7月)。在這篇文章中,華企云鑒于“自暴日先后攫我東北以來,新疆有俄國之覬覦,康藏受英國之窺伺。偌大邊疆,已成朝不保夕,長此以往,因循茍且,則非惟建國方略有失卻建設之效,而三民主義之理論,亦且根本動搖”,故“從遺教中研究建設中國邊疆,立論一本三民主義之真諦”,認為“民族主義扶助中國民族之獨立”,“民權主義扶助中國民族之發展”,“民生主義扶助中國民族之生存”[27],將“三民主義”作為中國各民族獨立、生存和發展之綱領。該文以“三民主義”為體,以“建國方略”為用,以邊疆為體用之結合與核心,從而將“三民主義”與“建國方略”的根本建立于邊疆之上。
第二,邊疆民族與中華民族之關系。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理論,大率講求將“已經失去了幾百年”的民族主義“恢復”過來,而因“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等五項因素,漢滿蒙回藏等各民族實際上已經融合為“一個民族”,認為“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完全是一個民族”[28](P183-188)。這是孫中山民族思想的核心,也是華企云在邊疆研究中就“民族主義”進行理論闡發的根本出發點。華企云說:
關于民族構成之原因,中山先生歸納為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及風俗習慣五項要素,所謂血統者,乃指一個血統或一個人種傳下者而言,祖先之血統,可以累世遺傳而不失,故黃色人種之子孫,永遠為黃色也。所謂生活者,乃指經濟狀況及謀生方法之一律者而言,故逐水草而居,以游牧為生活之蒙古人,亦可稱為一族。所謂語言者,乃指操同一語言之人而言,故自滿洲人操漢語而后,滿族即與漢族同化成漢滿一體也。所謂宗教者,乃指其人之信仰同一宗教而言,故信仰喇嘛教之西藏人,亦成其為一族也。所謂風俗習慣者乃指其人保持道一風同之情習俗而言,故如異教不通婚媾之回人,亦成其為一族也。推而言之,苗族之生活習俗等又復異殊,故苗蠻亦至今成一族也。[16]
又說:漢滿蒙回藏苗等民族,雖十九同化,然“在東北三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云南邊陲,則除漢族以外,猶有蒙回藏苗等種族”[16],只不過這些“種族”與漢族是“五位一體”。
孫中山和華企云同樣以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作為判斷民族的標準,不同的是,孫認定中國人“完全是一個民族”,而華企云則將之作為民族識別的依據,而將中國民族劃分為漢、滿、蒙、回、藏和苗六個民族。這可以看做是對“民族主義”理論的補充、發揮和完善,也可以看做是將“民族主義”理論與邊疆實際之結合。這種發揮、完善與結合,是華企云后期邊疆研究的理論出發點,同時也是華企云在邊疆研究理論上的一大突破。故此他說:“要救中國,要建設中國邊疆,首要提倡民族主義”,“漢滿蒙回藏,只可謂之中國民族種類之成分,又似一件有機體之各個細胞,絕非是此民族主義中所分之民族(筆者按:即“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之“民族”)”,所以中華民族實是“五位一體”,“雖則所處地域或有遐邇之分,在關系上實無畛域之殊”[16]。
華企云對于邊疆研究之體系性建設,集中體現在《新亞細亞》所刊發的一組文章之中。這組文章的內容表明了兩點,其一,華企云后期的邊疆論述,已經超越了早期單純的介紹性質,而進入了真正的研究階段。邊疆之氣候、物產、交通等華前期論述的重點,在這一體系中已經沒有位置;其二,邊疆研究應該以邊疆失地與外侮、邊疆經略史、邊疆政教民族與藩屬、邊疆界務與沿革為研究之重點與中心。這實際上說的是華企云所認為的邊疆研究的對象與范圍。
總之,華企云在邊疆研究上的建樹,一是與同時期的一大批邊疆研究團體與研究者一道,有意識地運用“三民主義”理論研究邊疆問題,使邊疆研究有了相對明確的理論指導;二是較為系統地發揮了“三民主義”理論,闡述了邊疆與內地、邊疆與國防、中華民族與邊疆民族以及邊疆建設之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指明了邊疆研究之對象與范圍,初步形成了一個理論體系,盡管比起20世紀40年代邊疆研究的主流理論“邊政學”來,這一體系并不完整,在深度方面也顯單薄。
注釋:
①王明珂說:“我今天在川大演講所舉的一個例子,早期景頗族中有一個傳說,過去華企云在江心坡‘野人’地區做調查時記錄下來的。這說法是,當地土人說他們是蚩尤的子孫;但老年土人說,我野人(景頗族那時稱野人)跟漢人、擺夷是三個兄弟;野人是老大,擺夷是老二,漢人是老三。因為爸爸特別偏愛老三,就把老大野人趕到山上去了。”見徐杰舜,王明珂:《在歷史學與人類學之間》,《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4年第四期。按:王氏所言,概出自華企云《中國邊疆》第十章“云南之界務問題”之第三節“江心坡問題”。原文為:“江心坡……各族性質風俗及生活狀況大致相同。領袖者曰頭目(即酋長);無文字,人多居于崇山峻嶺間,閉關自守,故其歷史世系,非特外人無從考查,即彼等亦不自知也。或謂彼等系蚩尤之子孫,即苗族別類,語涉理想,無從稽考。而年老土人則謂:‘我野人與擺夷漢人同種,野人大哥,擺夷二哥,漢人老三;因父親痛惜幼子,故將大哥逐居山野,二哥擺夷種田,供給老三;且懼大哥野人為亂,乃又令二哥擺夷居于邊界,防野人而保衛老三。后野人以山居甚苦,果然相率起反,打入京內;至永昌遇孔明領兵到來,受慰而返……’”云云。
②《中國邊疆》第三章題為“邊疆鄰接各地之地理概況與最近民族運動之鳥瞰”,第四章題為“邊疆鄰接各地之對華歷史與受制帝國主義之經過”。
[1]華企云.《現在的蒙古》編者按語[J].浙江青年,1934(2):187-203.
[2]馬大正.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J].歷史研究,1996(4):137-152.
[3]戴傳賢.中國邊疆之實況序言[J].新亞細亞,1931(5):13-14。又見戴季陶:《中國邊疆·序》。按:華企云《中國邊疆》一書,本擬題為《中國邊疆之展望》或《中國邊疆之實況》,出版時方改為《中國邊疆》。
[4]華企云同志邊疆問題之著作[J].新亞細亞,1930(3):129.
[5]《中國邊疆之展望》出版預告[J].新亞細亞,1931(3):9.
[6]編后談話[J].邊事研究,1936(5):124.
[7]華企云.新疆問題·凡例[M].上海:大東書局,1931.
[8]華企云.滿蒙問題·凡例[M].上海:大東書局,1929.
[9]華企云.岌岌可危的中國邊疆[J].平等雜志,1932(11/12):1-8.
[10]松介.西北農墾調查記[J].西北匯刊,1925(1):12.
[11]翁文灝.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J].獨立評論,1932(三號):9-11.
[12]原作者不詳,顛何 譯.西北為中國之生命線[J].社會科學季刊,1934(2):195.
[13]華企云.蒙古民族的檢討[J].邊事研究,1935(3):1-8.
[14]華企云.西藏民族之檢討[J].邊事研究,1936(5):1-8.
[15]華企云.蒙古問題之回顧與前瞻[J].邊事研究,1936(2):51-58.
[16]華企云.中國近代邊疆民族志[J].新亞細亞,1934(5):37-48.
[17]華企云.新疆之三大問題[J].新亞細亞,1931(4):25-35.
[18]華企云.一九三四年邊疆之回顧[J].新亞細亞,1935(1):17-30.
[19]華企云.一九三三年邊疆之回顧[J].新亞細亞,1934(1):47-58.
[20]華企云.云南問題·凡例[M].上海:大東書局,1931.
[21]華企云.中國邊疆·自序[M].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2.
[22]華企云.重勘滇緬南段界務的認識[J].東方雜志,1935(11):15-23.
[23]華企云.滇緬北段界務的檢討[J].新亞細亞,1935(1):15-24.
[24]華企云.滇緬南段勘界之現狀[J].新亞細亞,1937(2):31-36.
[25]新亞細亞學會總章[J].新亞細亞,1933(1/2):264.
[26]華企云.西藏問題[M].上海:大東書局,1930.
[27]華企云.總理遺教中邊疆建設之研究[J].邊事研究,1935(2):1-22.
[28]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