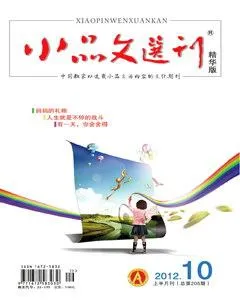兒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林少華
人在鄉下。每次散步路過一座農家院時我都放慢腳步。一年前的情景隨之浮上腦際。是的,恰好一年前暑假的一個傍晚,這座農家院大門旁貼的一張B4紙吸引了我的目光:“現房出售,價格面議”。好新好漂亮的房子!白瓷磚貼面,黃琉璃瓦,塑鋼窗,清爽明凈,燦然生輝。房前屋后一片蔥蘢,簡直綠得嗆人。尤其屋后山坡那三五棵老柞木,此刻滿樹夕陽,濃蔭潑墨,極具油畫風情。出售?我有些動心——半是貪心,半是好奇心——略一遲疑,推開院門進去。一位四五十歲的紅臉膛婦女撩開珠串門簾從里面走出。鄉下不講那么多虛禮,我劈頭一句:賣房子?“這房子我真不想賣啊!”女房主十分樸實直率,一見如故地向我訴起苦來。她說房子是三年前新蓋的,花了兩口子大半生的積蓄。本來是給兒子娶媳婦蓋的。可兒子去長春打工后找的女朋友橫豎不喜歡。跟兒子攤牌說,回來住這房子就“拜拜”,不“拜拜”就在長春買商品樓。于是兒子央求父母。父母再無積蓄,只好賣房子。“不賣咋辦呢?一坰地,去了成本一年就剩一萬。他爸爸外出打零工,我給冷庫剝青玉米,剝一穗三分錢,一百穗三塊,一千穗三十塊,起早貪黑剝一天才掙一百多一點點。什么時候能剝出首付啊?再說也就剝一兩個月。你看我這胳膊腫的!今天實在太痛才歇半天。”說著,女房東伸過胳膊給我看。我問賣了房子你們兩口子怎么辦呢?“那能咋辦?或者在附近買個小房,或者去縣城給親戚開的小店幫忙,還沒想好……”我問多少錢。“八萬。”城里人就是狡猾,我說八萬可夠貴的啊!“還貴?你看咱這房!”女房東把我讓到屋里。三大間,除了不是木地板,裝修比我的青島住所漂亮得多。中間堂屋,兩側臥室。米黃色大塊地磚,地暖。地暖!廚房也和城里別無二致。“你說這房子我怎么舍得賣喲?要不是為了這小死鬼兒子,給多少錢我都不賣!”
房子我當然沒買,但房子和房子的故事留在了我心里。今年暑假回來路過,自然放慢腳步往里多看幾眼。但看多少眼都沒看到去年女房東的身影。后來聽人說,房子到底賣了,賣給了城里一對退休的老夫婦。再后來路過,果然有一位老者在院里散步。那位女房東去哪里了呢?心里不覺有幾分悵然。
這么著,前幾天跟鄉下的大弟閑聊時我提起這件事。大弟聽了絲毫不以為然。這算什么呢,這算不得什么,大弟說,農村哪家不這樣!給兒子蓋房七八萬,娶媳婦七八萬,這兩件事沒十五萬下不來,再少也得十萬!在咱這山里,那戶人家有一坰地算例外了,一般只有三四畝地,不吃不喝一年只剩幾千塊,什么時候能湊夠十萬十五萬?現在又升級了,要去城里買房……養兒子簡直是一場災難!以前偷偷摸摸生兒子,現在給指標生都沒人要,不敢要!誰敢要?除非大老板!
農村拒絕兒子!我不由感到慶幸:如此下去,男女比例失調不難修正。同時感到悲哀:當兒子怎么可以這樣?孝心哪里去了?兒子猛如虎也!
但在當地,這遠遠不是最嚴重的。我當年務農時的一個熟人在小鎮一家老年公寓打工,告訴我一對老夫婦有九個兒子,九個兒子如今都混得人模狗樣的,但就是不肯把父母送來老年公寓或給生活費,任憑白發蒼蒼的父母彎腰九十度——差不多頭碰腳——到處撿破爛,有一次撿到兒子大吃大喝的飯店門口,而兒子看都不看一眼。你能相信?
這讓我想起一個多月前一位農民作家對我說的一件事。他說他所在的村莊有對父母有六個子女,而六個子女誰也不養老人,最后兩位老人熬一鍋農藥粥喝了,雙雙自盡。他補充說不孝之事十分普遍,而更可怕的是大家習以為常,無人指責。我說當地政府、村黨支部干什么吃的?為什么不上門做思想工作或繩之以法?“林老師,你太單純了,他們能干這個?何況他們自己做得怎么樣都要打個問號。”
不言而喻,孝德是所有美好德行的基礎。古人云“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前一句自然過時了,后一句沒有過時卻被拋棄了。我以為,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孝德的流失不妨說是最可怕也最可悲的流失,因為那是基礎人性的流失。說白了,有一部分人連人都不是了。即使在這個意義上,我也支持新一代家鄉人的做法:拒絕兒子,拒絕可能不是人的兒子!
選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