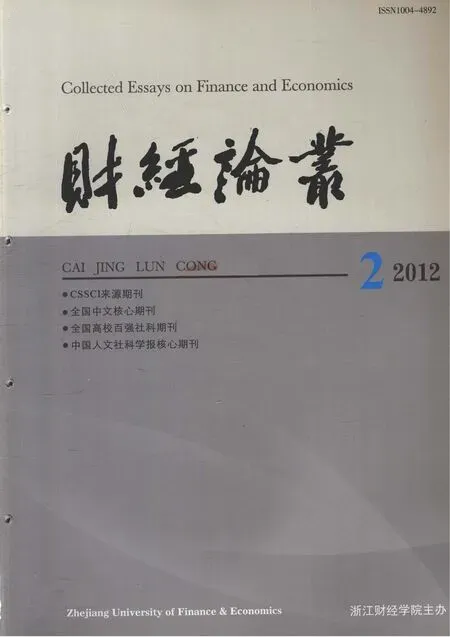研發支出資本化與管理層薪酬契約——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
林鐘高,劉捷先
(安徽工業大學會計系,安徽 馬鞍山 243002)
一、引 言
2007年 《企業會計準則》采用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相一致的規定,將研發活動劃分為研究和開發兩個階段,其中,研究階段的支出費用化,開發階段的支出在滿足特定條件下資本化①新準則規定對開發階段的支出,只有同時滿足以下五項標準才能資本化:完成無形資產以使其能夠使用或出售在技術上具有可行性;具有完成該無形資產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圖;無形資產產生經濟利益的方式;有足夠的技術、財務資源和其它資源支持,以完成該無形資產的開發,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該無形資產;歸屬于該無形資產開發階段的支出能夠可靠地計量。。然而,研究與開發階段的劃分有賴于企業自身的判斷;開發階段支出的資本化條件是原則導向規定,實際操作仍然有賴于企業自身的判斷。當客觀存在會計選擇機會時,企業管理當局往往會在準則規定的范圍內選擇有利于實現其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會計政策。1953年赫普霍恩以及后來戈登等人的實證研究表明,企業管理當局追求的目標并非會計報表利潤的最大化,而是通過會計政策選擇使前后各期收益均衡化 (Smoothing Income),管理當局選擇行動的準則是提高他們的福利。瓦茨和齊默爾曼 (1990)研究表明,企業管理當局在會計政策選擇過程中,既非人們傳統認為的那樣信奉穩健主義,也非一般地追求會計收益的均衡化,而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受簿記成本、契約成本、政府管制成本和政治成本等因素影響。國內學者方軍雄 (2009)[1]的研究發現,國內上市公司總體來說薪酬激勵有效,業績上升時的邊際增量顯著大于業績下降時的邊際減量。但是,國內外現有文獻并沒有專門就報酬契約與研發支出資本化的會計政策選擇問題進行研究,缺乏對于兩者相關性、進而缺乏對于管理層薪酬與研發支出資本化與其它盈余項目之間敏感程度的差異性分析。因此,本文要研究的問題是:研發支出的資本化對管理層薪酬的影響與其它盈余項目之間存在差別嗎?研發支出的費用化對管理層薪酬的影響與研發支出的資本化相似嗎?本文的研究為更好發揮報酬契約對企業管理者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提供了一定的經驗證據,尤其對研發密集型企業管理層薪酬的設計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二、文獻回顧:管理層薪酬的影響因素
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分離,以及信息的不對稱,衍生出了現代企業的委托代理問題。為防止代理人的行為損害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設計一套對代理人的激勵約束機制。設計有效的薪酬契約被認為是實現經理人目標和股東目標兼容的主要機制之一(Jensen&Murphy,1990)[2],薪酬契約所具備的保障效用與激勵效果,有助于促使經理人與股東的利益趨于一致 (Gibbons and Murphy,1990)[3]。
1.公司績效與管理層薪酬
代理理論認為,基于經理人逐利趨避的特性,當股東擁有關于經理活動和投資機會的完全信息,他們就可以根據經理的努力程度執行薪酬契約,其最佳薪酬契約即為固定薪資 (Holmstrom,1979)[4];但信息的不對稱使得基于經理努力程度的薪酬契約事實上是不可行的,這時,股東會傾向使用激勵薪酬契約,以促進經理人與股東的利益趨于一致,公司業績成為評價經理努力程度的次優選擇。當股東將經理人薪酬與公司績效相連時,即產生了所謂薪酬績效敏感性,從而使經理人與股東利益趨于一致,減少經理人危害股東權益之行為 (Fama,1980)[5]。Lilling(2006)[6]應用一階差分矩估計和系統矩估計方法,消除了內生性和企業特性的影響,發現CEO收入與企業市值之間呈現出更為強烈的相關性。Giorgio&Arman(2008)[7]對美國的 “新經濟”企業1996-2002的面板數據進行檢驗,結果仍然顯示出高管報酬與企業業績的強相關性。國內關于高管激勵與企業業績關系的研究結論卻各不相同,一種觀點認為高管人員的年度報酬與公司績效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8]。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經理人員薪酬與公司業績密切相關[9]。之所以有不同的研究發現,除了研究變量具有較大不同之外,更為重要的是研究窗口的選擇、高管薪酬的構成等的差異,更何況在中國上市公司中存在高管在職消費以及業績不變甚至下降但高管薪酬反而上升的不正常現象①也就是說,在中國較弱的監管程度下,經理人可能利用其權利獲得較高的收益,或者說利用其管理權力獲取更高的租金,混亂的治理結構只會導致 “高酬低績”(Bebchuk,2006)。。
2.公司治理與管理層薪酬
當面臨著過高的激勵強度,或是薪酬與績效的弱相關或不相關,單純的激勵契約已經難以解釋企業及經理人的行為,許多經濟學家開始轉向公司治理系統 (如董事會、股權結構等)來尋求答案。Core et al.(1999)[10]研究發現董事會以及股權結構對于CEO薪酬截面數據的變動具有很強的解釋力,過高的CEO薪酬與較差的治理結構相聯系,而此時往往伴隨著較差的業績。Cyert et al.(2002)[11]發現在CEO兼任董事長的條件下,CEO薪酬一般要比平均水平高出20%-40%;而在董事會成員持股比例高的條件下,董事會成員持股比例與首席執行官的薪酬呈較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董事會成員持股比例每增加一倍,CEO薪酬降低4%~5%。Hartzell&Starks(2002)[12]等的研究表明,外部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和機構投資者的集中程度與經理人獲得的報酬總量存在負相關關系。國內學者也注意到了公司治理對高管薪酬的影響。林浚清等 (2003)[13]研究發現高管團隊成員薪酬差距與公司未來績效有正向關系;國有股比例、股權集中度與薪酬差距呈負向關系。徐向藝等(2007)[14]研究表明在目前的報酬激勵體系下,非年薪制激勵形式優于年薪制和股權性報酬激勵形式;總經理為董事長或董事的公司治理績效和激勵機制優于其它類型;高管薪酬與公司治理績效顯著負相關。王克敏和王志超 (2007)[15]研究發現高管控制權的增加會提高其薪酬水平。
除此之外,學術界還就盈余管理、高管特征、行業以及地區差異等方面對薪酬的影響作了廣泛的研究,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在GAAP的規定下,研發支出的費用化處理,會對短期會計盈余和股價產生負面效果,導致管理者裁減研發支出[16]。因此為了鼓勵管理者投入創新活動與避免短視行為發生,董事會在制訂管理者薪酬契約時,除了盈余考慮外,也會根據公司的創新程度來決定管理者的薪酬水平[17],還可以通過對管理層薪酬結構的調整,使得短期績效對管理者財富變動的影響力逐漸減弱,降低管理者減少研發投資的動機。國內為數不多的相關研究發現,企業創新投資對管理者現金薪酬的影響呈現正相關,顯示董事會在薪酬設計上,通常會將薪酬制度與創新能力互相連接來改變管理者風險趨避的傾向,并且激勵管理者勇于創新。張周[18]研究了薪酬激勵和管理層持股與研發支出增加額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管理層持股和研發投入都正相關,對管理層實施股票期權激勵將增加企業研發投入。以上分析表明,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研發支出的資本化不僅使股東和外部投資者了解到公司研發活動的進展,也可以間接觀察到經理人的努力行為,同時更作為一種 “好消息”,向外界展現了公司擁有創新的技術、發展勢頭強勁、短期績效良好、長期效益可持續性等形象,從而增加外部投資者對公司的信心。據此我們提出假設1:
H1:管理層薪酬與研發支出資本化強度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根據委托代理理論的預期,有效地薪酬設計將激勵經理人去選擇與完善自身行為以增加股東財富 (Jensen&Murphy,1990)。但現有文獻很少討論在給定的業績水平下,股東財富是否有真實的增加。資本化的研發支出,盡管在當期并沒有相應的現金流入,但將在未來為公司帶來持續穩定的現金流入,同時增強企業長遠發展的競爭優勢。在盈余分項目的層面,有效的激勵契約要求給那些與管理層努力相關性更密切的業績指標以更高比例的薪酬激勵。與盈余的其它構成相比,研發成功帶來的持續收益更少地受到資本市場系統風險的影響,但是更多的會受到公司市場優勢地位的影響。一般而言,那些處于市場領先地位的企業,為了保持其競爭優勢而更有動機去進行研發活動,因此,理性的委托人應當知道公司市場優勢地位導致的企業研發支出資本化對于企業業績的貢獻,從而給予這類企業的研發費用資本化以較高的激勵系數。據此我們提出假設2:
H2:研發支出資本化強度更大的公司,管理層薪酬對研發支出資本化的敏感系數顯著高于對其它盈余的敏感系數。
現實中企業將研發支出直接費用化處理,除了不符合資本化的條件外,費用化處理對管理層薪酬沒有影響也是一個可能的解釋。大量研究表明當業績下降時激勵合同總是存在薪酬約束乏力的現象,管理層在業績增長時獲得了額外的獎金,業績下降時卻沒有絲毫的懲罰。Bebchuk and Fried(2004)[19]提出的 “管理層權力論”認為,董事會的獨立性不強,不能有效地監督管理層,使得管理層有機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獲得高于合理水平的薪酬,而這些超常的薪酬便是管理層權力的租金。在中國的上市公司中,這種高管薪酬粘性特征也同樣存在。首先,中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集中和控股股東的國有性質,加上信息披露的不透明,加劇了高管薪酬粘性發生的可能。其次,行政干預的存在使得國有企業承擔著諸如擴大就業等政策性目標,導致國有企業經營績效和企業負責人的努力和才能之間的因果關系模糊,削弱以業績為基礎的薪酬機制的有效性[20]。再次,當公司業績出現下滑時,公司高管總是以諸如成本上升、競爭加劇等外部因素為借口,加上行政干預的存在使得經營性虧損與政策性虧損難以區分,導致削減高管薪酬的舉措受阻。據此我們提出假設3:
H3:研發支出費用化的公司,管理層薪酬與費用化研發支出幅度之間不存在顯著相關性。
四、研究設計與樣本選擇

為了檢驗假設2,我們借鑒Lilling(2006)、杜興強和王麗華 (2007)采用的一階差分方法,建立模型2,即管理層薪酬-業績的靈敏度分析模型:

模型1因變量是高管年度報酬總額 (COM),自變量是研發支出資本化總額 (CAP)。考慮到研發支出資本化會對營業利潤與股東權益產生影響,所以我們以 “營業利潤”減去 “資本化的研發支出”得到 “其它盈余”(REV)進行區分,以單獨考察研發支出資本化對管理層薪酬的影響。為了進一步檢驗假設3,我們加入研發支出費用化總額 (EXP),以考察研發支出費用化程度更高的公司,管理層薪酬與研發支出費用化之間的相關性。考慮到樣本公司的資產規模差異性大,我們參考資產減值文獻 (Riedl,2004)[21]用滯后一期的資產總額 (ASSET)對以上變量做標準化處理,以評價公司規模對業績和薪酬的影響。模型2因變量是高管年度報酬總額的變化值 (Δ COM),自變量是研發支出資本化的變化值(Δ CAP)和其它盈余的變化值(Δ REV)。其他控制變量的設置如表1所示。
(一)模型構建與變量設置
為了檢驗假設1和假設3,建立模型1,即管理層薪酬激勵模型:

表1 變量定義表
(二)樣本選擇
本文收集了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在上海、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研究樣本的選取如下:(1)剔除了金融保險行業;(2)剔除相關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本文所研究的資本化研發支出是指上市公司開發支出的余額與轉入無形資產的研發支出之和。高新技術企業數據以年報財務報表附注中稅項所披露的關于高新技術企業的評定信息為準。這兩個數據均來源于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系手工收集,其它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和色諾芬數據庫的數據計算生成。
五、實證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表2 描述性統計
表2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樣本公司高管年薪總額 (Compay)的均值為327.26萬元,占公司營業利潤 (YYLR)均值 (2.75億)的1.19%,高管年薪總額的中位數低于均值,最大值與最小值相差甚遠,數據分布不集中,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差距較大。樣本公司的研發支出資本化額 (Capital)的均值為3561.83萬元,占公司資產總額 (CAP)均值的0.77%,比例較低,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的研發效率普遍偏低,且上市公司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我們對模型1和模型2的主要變量進行了Pearson檢驗①受篇幅的限制,模型1和模型2各變量間相關系數的Pearson檢驗數據生成省略,有興趣的讀者備索。,模型1的檢驗結果顯示,相關系數為0.219,說明企業的資本化研發支出的強度越大,高管的年薪報酬越高。模型2的檢驗結果顯示,相關系數較高的兩組分別是,SIZE與FST的相關系數為0.232,SIZE與RAT的相關系數為0.356,相關性均在合理可信的區間。
(二)回歸分析
1.研發支出資本化強度與管理層薪酬的回歸分析

表3 研發支出資本化強度與管理層薪酬的回歸結果
表3的全樣本回歸結果顯示,CAP的估計系數為0.02472,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管理層薪酬與資本化研發支出強度顯著正相關,該結果支持假設1。從其它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看,企業的其它盈余 (REV)、管理層持股 (ESH)均與管理層薪酬顯著正相關,說明我國上市公司中同樣存在以企業盈余為基礎的管理層薪酬制度,特別是管理層持股的上市公司,其高管的年薪報酬更高。企業的規模與管理層薪酬顯著負相關,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相一致。研發支出費用化強度 (EXP)與管理層薪酬也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這與我國政府行為有關。為了推動企業技術創新,我國政府對企業的研發活動常常給予政策支持、稅收優惠與更多的科技研發投入等。表3的分組回歸結果顯示,在研發支出資本化強度低 (研發支出費用化強度高)的公司,費用化研發支出的強度 (EXP)與管理層薪酬不存在顯著相關性,支持假設3。首先,我國不存在經理人市場造成的總經理與大股東關聯性以及外部接管市場的不完善,決定了我國上市公司代理人競爭機制的不健全,對高管控制權缺少有效的監督和制約。由于高管控制權的存在,使得研發投入的費用化處理對企業盈余的負面效應不會對高管薪酬產生顯著影響;其次,稅收減免政策又進一步弱化了研發投入費用對當期企業盈余的負面效應,不會對企業高管的薪酬產生影響;再次,行政干預的存在使得國有企業承擔著諸如擴大就業等政策性目標,導致國有企業經營績效和企業負責人的努力才能之間的因果關系模糊,從而削弱以業績為基礎的薪酬機制的有效性 (陳冬華等,2009)。最后,由于我國政府對上市公司高管實施的薪酬管制存在 “重獎輕罰”的現象,誘發了經理人自利的代理問題,形成了 “高管薪酬升降自定,業績掛鉤實成空談”這一特有現象。
2.管理層薪酬-業績的靈敏度分析
表4顯示,在那些研發支出資本化強度更大的公司,研發支出資本化每增長1個百分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卻減少0.01889個百分點,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而其它盈余每增長1個百分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將增長0.00384個百分點,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一結果與假設2相悖離。表明委托人并不理性,對研發支出資本化及其轉化所形成的無形資產帶來的股東現實財富與未來財富的增加,以及獲得的市場競爭優勢,毫無察覺,并沒有給予更高的薪酬激勵系數。
研發支出資本化的低敏感性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由于研發產出效應的滯后性,研發活動往往要經歷前期基礎研究、開發、后期維護等眾多流程,即使研發活動已經形成滿足資本化條件的開發支出,但其是否可順利轉化為實際生產力,所形成的無形資產能否為企業帶來預期的經濟效益,所生產的新產品是否為市場所接受等都具有不確定性,且需經歷較長時期才可以觀察到。委托人無法辨別自身利益的可實現性與現實性的差異,導致激勵不足[22]。

表4 管理層薪酬-業績靈敏度的回歸結果
(三)穩定性檢驗
借鑒已有研究,做替代變量檢驗,分別用 “薪金最高的前三名高管 (COM1)”、“薪金最高的前三名董事 (COM2)”表示高管薪酬,穩定性檢驗的結果與上述實證結果一致①這部分穩健性檢驗的結果和數據限于篇幅沒有列出,有興趣的讀者備索。。
六、基本結論
本文以2007-2009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分析了研發支出資本化與管理層薪酬之間的相關性,并進一步考察研發支出資本化與管理層薪酬之間敏感系數。實證結果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管理層薪酬與資本化研發支出強度顯著正相關;在研發支出費用化強度更高的公司,管理層薪酬與研發支出費用化強度不存在顯著相關性;相對于企業盈余,我國上市公司委托人并未給予研發支出資本化更高的薪酬激勵,即使在研發支出資本化強度更高的公司也是如此,說明委托人無法理性察覺,由研發支出資本化所形成的無形資產帶來的股東未來財富的增加。
[1] 方軍雄.我國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存在粘性嗎?[J].經濟研究,2009,(3):110-124.
[2] Jensen,M.,and K.Murphy.Performance Compensation and T op Management Incentiv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225-264.
[3] Gibbons,R.,and Murphy,K.J.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J].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1990,(43):30-51.
[4] Holmstrom,B.Moral hazard and observer ability[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0(1):74-91.
[5] Fama,E.F.Agency problems and theory of the fir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0,(88,April):288-307.
[6] Matthews Lilling.The Link Between CEO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 for mance:Does Simultaneity Matter[J].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2006,(34):101-114.
[7] Giorgio Canarella.Arman Gasparyan.New insights into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fil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new economy”firms,1996-2002[J].Managerial Finance,2008,34(8):537-554.
[8] 李增泉.激勵機制與企業績效——一項基于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 [J].會計研究,2000,(11):24-30.
[9] 杜興強,王麗華.高層管理當局薪酬與上市公司業績的相關性實證研究 [J].會計研究,2007,(1):58-65.
[10] Core,J.,Holthausen R.,Larcker,D.,Corporate governance,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ompensation,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9,(51):371-406.
[11] Cyert,Richard,Sok-Hyon Kang and Praveen Kumar,Corporate Governance,Takeovers,and Top management Compensation:Theory and Evidence[J],Management Science.2002,48(4):453-69.
[12] Hartzell,J.C.,and L.T.Starks.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3,58(6):2351-2374.
[13] 林浚清,黃祖輝,孫永祥.高管團隊內薪酬差距、公司績效和治理結構 [J].經濟研究,2003,(4):31-40.
[14] 徐向藝,王俊韋華,鞏震.高管人員報酬激勵與公司治理績效研究——一項基于深、滬A股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 [J].中國工業經濟,2007,(2):94-100.
[15] 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權、報酬與盈余管理——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 [J].管理世界,2007,(7):111-119.
[16] Shijun Cheng.R&D Expenditures and CEO Compensation[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4,(79):305-328
[17] Geiger,S.W.and L.H.Cashen,Organizational Size and CEO Compensation: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versification in Down scoping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2007,19(2):233-52.
[18] 張周.基于股市行情的薪酬激勵與研發支出關系研究[J].會計之友,2010,(9):100-102.
[19] Bebchuk,L.,and J.Fried,Pay without Performance: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2004.
[20] 陳冬華,陳信元,萬華林.國有企業中的薪酬管制與在職消費[J].經濟研究,2005,(2):92-101.
[21] Reidl,E.J.,An Examination of Long-Lived Asset Impairment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4.179(13):823-852.
[22] Lippert,R.,Moore,W.Compensation Contracts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Determinants of 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y[J].Journal of Finance Research,1994,(17):321-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