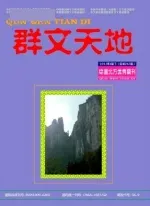還童心于童子

小學是個中轉站,一個人要在這里開啟他由生命個體走向群體生命的道路,這個轉向自然就顯得至關重要。如果說這個轉向是我們的共識,那么對它的不同理解就構成了教育的兩種路向。一種將生命理解為一個目標,著眼于未來,盡快實現生命個體的社會化;一種將生命理解為一個過程,著眼于當下,盡量完善生命作為其本身的意義。正如佛家有三世佛,人之為人,既屬于未來的世界,也屬于當下的世界。一個人固然應該以承當責任、融入社會為目標,但同時,如何走好當下的每一步也是人需要用畢生來完成的功業。二者非但不沖突,而且互為依托,彼此相長。只要將一個個的生命段落串聯起來,生命鏈條自然會呈現,個體生命的社會化必然水到渠成;同樣,只有將整個生命鏈條分解開來,在每一段上用工夫,方能使一人發揮出天生一人必有之作用;教育便應該是二者的統一。然而現實是,由于沒有在這一意義上理解學以致用,學以致用便被強行付于了第一種路向,從而顯得與當下的完善毫無關系,每一個教育階段都以下一個教育階段為唯一目的。這樣做無疑是危險的,其一,在價值層面上抹殺了人存在的意義。因為人生最大的終點是死亡,如果總要以下一個為目的,那么顯而易見,死亡便是人生的全部目的所在。如此說來,只關注未來的教育本質上是死亡教育。其二,在事實層面上,未來沒有當下作為奠基,便永遠是未來,時間的鏈條少了此時此刻便不足以鏈接過去和未來。因為所有的未來都必須在當下的轉化中進入人的生活。這就是說,只關注未來的教育本質上不可能如其所愿。
人經過的每一個教育階段便是他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階段,它導向未來,有益于未來,卻不是為了未來。人有權利以生命呈現生命本身的意義,而我們應該做的,便是幫助他實現這種權利。小學是一個人的孩提時代,他們被稱為兒童,既是童子,也有童心,讓童子之心存留于童子之身便是最好的當下即時。如此,則教育成人化、世俗化的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因為接續上了如前所說的鏈條斷層,所做甚多而收益甚少的教育狀況也可期改善,這便是今天我們提出童心校園的初衷所在。
童心說由明代思想家李贄提出,他以人最初的本心為童心,認為“初心”沒有受到外界的熏染,因此最為珍貴,人最好的狀態便是剝去塵俗的干擾,常保此心。內心的體認和知識的積累是學習的兩個方面。《中庸》有云:“自誠明謂之道,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即誠明本心,是內心的體認;明即明了事理,是知識的積累。在此處,二者是沒有分離渾然一體的。李贄處于思想被程朱理學絕對壟斷的時代,程朱認為內心的體認必須通過知識的積累得以實現,是“由明而誠”之路。這原本沒有問題,然而一味“以知代心”就會走向只重外在知識,沒有內心體認的僵局,最終導致在浩瀚的知識中迷失自我,甚至迷失良知,以書本之對錯為對錯,以見聞之是非為是非。李贄為了打破這個桎梏提出童心說,走了“自誠而明”的道路,以此糾正只重知識不重本心的偏頗。
童心是無邪之心,不受約定俗成的限制,不受成人世界的羈絆,當一個孩子稚嫩地問道哪個是好人哪個是壞人時,他們希望揚善棄惡的本心便脫然顯現在我們面前了,我們又何必以成熟的眼光挑剔他們的天真呢?這不正是這個時代久違了的價值原則嗎!從這個意義上說,書的所有價值在于教人明辨是非、知曉善惡、澄明本心,因此書是對心的護持,而不是相反。童心說由李贄正式提出,然而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對于童心的珍惜肯認卻是從來就有的。對于孩童的推崇首推道家,老子說“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認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整部《道德經》中寫滿了對兒童柔弱稚嫩的推崇;莊子以“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之人為“神人”,以“真人”作為人格的極高境界,整部《莊子》中寫滿了對兒童天真無邪的推崇;佛教經典《六組壇經》有云:“念念本心,如如自現”,便是要以“本來無一物”的明凈本心去顯現真如佛性;儒家的整體氣質是溫潤的,初看不似孩子的頑皮無狀,然而溫潤的德性根本是由無邪的赤子之心帶來的,這就是孟子為什么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原因所在。《中庸》有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到好的自然去喜歡,見到壞的自然去討厭,這孩提本性才是人們可以分辨善惡的最終依據所在,有了這份心,人才有喜善厭惡的可能。即便是溫而厲的孔子,又何嘗不珍重童心,又何嘗不以童心教人!“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這分明就是一個玩得忘了吃飯的孩子。《論語》中最長的一章乃是由童心二字寫成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當孔子對這幅畫面心馳神往,喟然感嘆的時候,天真無邪四字便刻在了世世代代讀書人的心中。
理想人格是德知雙全的人格,一種好的教育便應使人德智雙修。童心是無邪向善之心,是直好直惡之心,孩童保有童心便保住了良善的德性。童心亦是好奇求知之心,是不受羈絆之心,孩童保有童心便是保住了創新的天性。好奇是知識的來源,世間的知識無不生發于想要追究原因的一念好奇,創新則無不泯滅于司空見慣的怠惰定式。童心是活潑爛漫之心,是橫生妙趣之心,孩童保有童心便是保住了審美的天性。當求真與求善統一于審美,當一個人可以用審美的態度去參看大千世界,和大千世界中的自己,這種人格模式便會就此升華為一種生命境界。有人說,時代莫大的悲哀在于蕓蕓眾生喪失了生命之美卻渾然不知。童心是生命之美的原初形態,生命順著這條路延展就不至于走失了自己。生命不失其本是千古圣賢對人類最美好的祝愿,我們雖不敢奢望如此,然而,在這紛繁的塵世中辟出一方凈土,讓孩子可以在校園的庇護下懷揣著童心,安心走過他的童年,便也是我們小小的心愿了。
(作者簡介:劉思言,女,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10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