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見與不見》著作權案
詩歌《見與不見》著作權案
從目前的博文發表習慣看來,大家并未形成一致的共識,發表在自己博客上的內容即為博主原創。而法院的這一判決可能會使得博客上的文章署名更加的亂而無序,不利于形成網絡作品的權屬清晰化,法院更應該在引導網絡用戶發表作品時正確署名問題上作出一些努力。”
當事人
原告
談笑靖
被告
北京市新華書店王府井書店(簡稱王府井書店)
珠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簡稱珠海出版社)
【案情】
原告談笑靖主張其創作了詩歌《班扎古魯白瑪的沉默》,并于2007年5月15日發表在其個人博客上。2008年10月,《讀者》第20期第7頁刊登《見與不見》一文,與原告主張權利的作品僅一字之差且字義相近,其余文字及分節均一致,署名為倉央嘉措。2008年10月7日,原告向《讀者》雜志發送電子郵件一封,告知上述文章署名錯誤,原告為該文作者,該文發表于原告博客。2010年8月,被告珠海出版社出版了《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一書,該書副標題為“‘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情與詩”,作者子非,該書第33頁收錄了前述《見與不見》一文。
法院經審理認為,博客作品同樣是創作者智力成果的反映,作者依法對其享有著作權。原告以其博客登陸過程的公證及做出權利主張的郵件相互印證,足以證明涉案作品的創作和發表情況,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認定原告對涉案作品依法享有著作權。由于倉央嘉措的出版物中該文作者爭論較大,且有《讀者》對該文署名在先,故該認知錯誤非被告珠海出版社自身所能避免。另外,涉案圖書主要內容為倉央嘉措作品賞析及其生平介紹,對《見與不見》一文使用比例有限,且對其作者爭議進行了聲明。故認定珠海出版社侵權主觀故意不大,盡到了審查注意義務,僅需承擔停止侵權的法律責任,王府井書店銷售涉案圖書,應承擔停止銷售的法律責任。據此,判決珠海出版社停止出版、發行含有《見與不見》內容的圖書、王府井書店停止銷售含有《見與不見》內容的圖書。
【點評】
當前,著作權保護仍然是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內容之一,互聯網出現后,由于網絡傳播信息的便利性及虛擬性,給作品的創作、使用、管理和保護帶來了新的挑戰。相對于傳統的創作載體,博客是一種借助網絡技術實現的全新的作品創作形式和傳播途徑。只要網絡作品符合著作權法關于作品獨創性等的規定,其著作權利就應得到認定和保護。該案不僅在理論層面彰顯了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原則,而且在實踐層面探索了諸如技術咨詢、實地勘驗、電子實物證據相互印證等有效做法,突破網絡虛擬性及網絡信息易修改等障礙,準確地認定事實,正確適用法律,切實維護了權利人合法權益,恰當平衡了社會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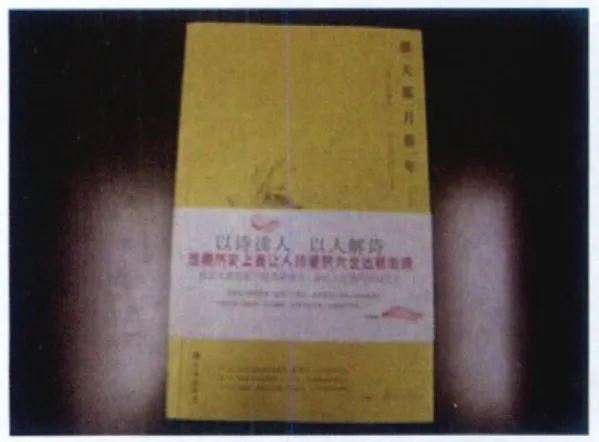
涉案侵權作品 (東城法院 供圖)

媒體澄清作品權屬 (東城法院 供圖)
【EIP點評】你署或不署名,博文都是你的?
繼2010年“搜狐博客博文抄襲案”被選入“北京市十大知識產權典型案例”,今年“《見與不見》署名權案”再次入選。兩案均是因“博客是一種借助網絡技術實現的全新的作品創作形式和傳播途徑”而入選,其所體現出來的問題也基本相同。去年EIP編輯部在評析“搜狐博客博文抄襲案”時明確,無論如何新穎的創作形式抑或傳播途徑,都逃不過著作權侵權認定的既有程序:權屬確定、侵權行為認定、損害賠償。較之于“搜狐博客博文抄襲案”,本案的案情又略顯復雜,這讓我們更多了一些值得思考和探索的內容。
無論是去年的“搜狐博客博文抄襲案”還是今年的“《見與不見》署名權案”,在權利人的權屬確定問題上法院都采取了相同的標準,即“如無相反證據證明,博客上發表的文章應為博客空間所有人所創作,即博客上發表的文章著作權應由博客空間所有人享有”。這是“搜狐博客博文抄襲案”確立的標準,當時筆者并未多加思考,按照傳統著作權權屬確定標準,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即為作者,那么法院所認定的“博客上發表的文章應為博客空間所有人所創作”的標準確無太大爭議,但《見與不見》一案的案情復雜了些,我不得不去思考這一表明證據標準是否完全適用于目前的網絡環境。
《見與不見》的風行得益于《非誠勿擾2》,一首小清新的詩鋪墊了一部電影的感情基調,而一部名導名角的電影徹底捧紅了這首小清新的詩。電影放映后,“你見,或者不見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成為一句經典,又因這句與片尾曲《最好不相見》的同源同宗,而電影告訴我們《最好不相見》改編自倉央嘉措的《十誡詩》,就這樣,我們深信倉央嘉措就是《見與不見》的作者。但當出版社趁著網友追捧的熱潮出版倉央嘉措的詩集后,自稱為原作者的談笑靖跳了出來,給各位追捧的倉央嘉措的網友們一記悶棍:《見與不見》不過是她2005年的一篇博文。當然,權屬證明責任自然是談笑靖承擔的,這個證明過程并不艱難,從“搜狐博客博文抄襲案”所確立的表面證據證明標準看來,談笑靖只需要證明發表《見與不見》的博客歸她所有,盡管《見與不見》并未署名,就已經履行了初步證明責任。判決讀到此處,我忍不住思考一個問題,在一個轉載便捷且盛行的網絡媒介上,如此低的證明標準是否合理?從目前的博文發表習慣看來,大家并未形成一致的共識,發表在自己博客上的內容即為博主原創。而法院的這一判決可能會使得博客上的文章署名更加的亂而無序,不利于形成網絡作品的權屬清晰化,法院更應該在引導網絡用戶發表作品時正確署名問題上作出一些努力。
再具體到本案上來,《見與不見》本身就有著錯綜復雜的來歷,先是《讀者》的傳頌,又有《非誠勿擾2》的烘托,對原作者這種根深蒂固的“誤讀”真的是一個簡單的博主身份證明就能做到的嗎?對此,法院完全沒有分析和考慮。盡管,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考慮可能會導致案情更加復雜,但因噎廢食,完全不考慮個案的特性,而只進行最為簡單的認定和證明也會導致判決難以服眾的結果。(文/左玉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