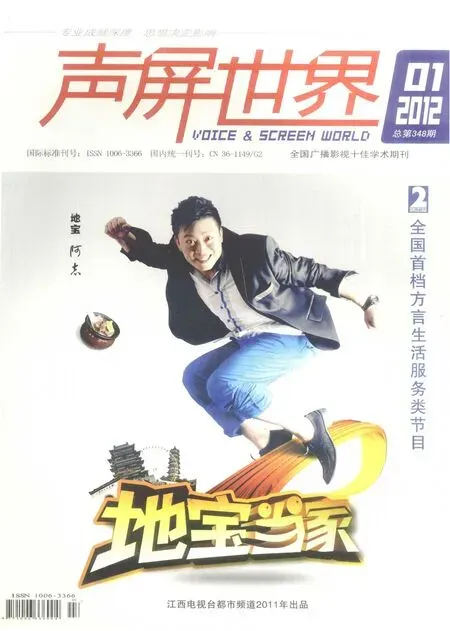新聞業、新聞教育及民主
□ 作者:[美]赫伯特 J.甘斯(Herbert J.Gans)
□ 譯者:奚路陽 王哲平
一
在某種程度上,政治新聞是新聞記者的生命線,讓民眾接觸政治是他們的職責之一。在他們看來,民主有賴于知情的公民,而新聞業的主要任務就是告知。
盡管如此,實際情況卻是,出稿時限和商業利益等方面的壓力使得新聞記者無暇去細究他們所提供的信息是否符合知情的公民的真實需求,更不用說一開始就著眼于培育知情的公民了。雖然新聞的受眾們并不是完全從一而終的,但是新聞記者卻是社會民主得以幸存所必不可少的,這也是執政者在掌權伊始便開始尋求對媒介的控制的原因。 正如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新聞記者不僅要受眾及時了解代表他們的政府正在以及將要對他們做什么,而且他們的出現也提醒著政府官員,他們的行為正在受監督和被報道。
但是新聞記者們并不是總能成功地履行這些基本的民主化職能,因為政治家們知道如何應付記者的來訪。更為重要的是,新聞記者的很多工作都會受到限制。舉例來說,為了充實新聞版面,他們必須要有可靠的、穩定的新聞來源,因此他們不得不依賴官方,因為官方擁有權威、權力以及制造有新聞價值的實踐及評論的資源。結果,大部分美國新聞媒體都會整齊劃一地根據白宮及其高官的要求來報道新聞。盡管相關的高級官員所擁有的權力、權威能極大地影響政府,為參加選舉的候選人鋪路,通過立法來獲益,但它們卻沒有向媒體提供信息的義務,甚至那些把大眾的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力量的大型團體,也鮮見報端。
對于那些普通公民們而言,他們在政治上的行為幾乎從來上不了新聞,即使在選舉日,大部分不參加競選的人也會因為現實目的而被忽略。但是,當公民通過威脅或激怒政治的方式表達異議時,便成為報道的主角。因此,新聞并不是從社會底層產生出來的。從2000年12月開始,一些新聞記者在實現其專業的民主責任時,他們的缺點就表現得淋漓盡致。為了能確保他們的穩定可靠的新聞來源,他們需要在原來的政府和之后的新白宮之間轉變,于是,他們不急于了解佛羅里達競選票數繼續清點的情況,也不急于發布關于佛羅里達投票不正規的調查,主流新聞媒體從未認真追蹤過佛羅里達或其他州選票被偷的情況。對于兩黨能夠對國家進行分區而治和不公正地劃分選區以確保他們在參眾兩院占有四分之三的席位這些事件,記者們也未能進行充分報道。
二
記者們不愿意報道不民主或反民主進程的行為,并不能簡單地按照當下盛行的媒介批評者們所譴責的那樣去理解。這一行為不是因為知名記者與上層民選官員處于同一個圈子,或是習慣于從高級或中高階級和常春藤大學聯盟招募國內記者。那種自由派的記者現在越來越保守、保守派記者越來越傾向自由派的說法并不準確。記者們在新聞媒體中刻意增加“軟文”或者非政治情節(經常被譴責為“信息娛樂”),甚至被一些主要國家和當地的新聞媒體集團收買,這些都能看出其責任的缺失。
事實上,問題應該回到美國建立之初,許多開國元勛并不急于讓公民參與到新政府中來,沒有建立制度來保障對政府決策和行動的報道。美國記者參與是因為別的原因,雖然它最終提供了政治上的溝通,但卻同時不得不伴隨著“代議制”民主。另外,我們要記住的是新聞媒體首先是作為商業新聞公司存在的,它依靠龐大的受眾資源,從廣告主那邊獲得利潤。在大多數企業為能獲得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純利潤而感到無比欣喜時,新聞公司有時候卻能獲得高達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潤。新聞產業的特殊性使得新聞公司無法利用國外的廉價勞動力來制造產品(即新聞產品),因此當他們想壓縮成本,使之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就只能雇傭較少數量的記者。結果是,記者不得不消極地去工作。他們從新聞事件的當事人那里取得新聞,而不是出去尋找或挖掘新聞。如果他們可以,新聞行政機關可能至少得在每個主要聯邦機構安排記者,而這些機構正忙于建立新的公民權利限制。
這種消極和依賴實際上解釋了美國政治新聞的大概推力和新聞設定框架的形式。固然,這些并不是唯一因素,假如記者變得積極(例如報道太多關于偷取選票的新聞),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他們會被阻止。國內廣告主可能會反對,他們不喜歡與他們不同選區的或自身有政治問題的重要人物對抗;保守的評論員和權威人士也會加入反對的隊伍中來。另外,許多記者更感興趣的是說故事而不是從事政治教育,因為客觀公正的專業準則敦促他們保留對政治的中立或者不關心。更多的記者就像美國的主流人群一樣,不習慣于思考意識形態的問題。即便政府開始對思想意識形態采取強硬手段時也甚少注意。許多長期兼有經濟聯合的右傾保守主義和左傾保守主義思想的人,或者對社會問題抱開明態度的人可能都不清楚自己的思想意識是什么。
最終,美國新聞結構的缺陷還在于沒有和新聞受眾聯系到一起。媒體沒有履行告知的義務,而且可以不根據事實妄下定論或提出反對意見。特別是在選舉期間、戰爭時期或危機的時候,大多數受眾滿足于那些報道頭條或一份報紙的“國內新聞摘要”和簡短的電視新聞節目。在美國社會中,政府的作用十分微弱和隱蔽,這使得除了定期出現在許多媒體上的天氣預報或醫學新聞,許多公民在多數情況下對新聞沒有直接的需求。沒有政治傾向的公民除了選舉期,其他時間里并不需要政治新聞。只有那些對經濟有直接和持續興趣的人才有了解政府做了什么和付出了什么的新聞需求,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從新聞刊物和其他新聞銷售點獲得所需的新聞。當然,當政府起作用時,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公民才會對政府如何提供幫助的新聞有直接需求,但是他們知道新聞媒體并不關心他們,只有在他們對中產階級感到憤慨時才會報道他們。
我所提到的新聞業對健全美國民主的貢獻的不足之處絕非偶然,但是它們能追溯到美國社會基礎結構的特性。作為結果,它們同樣難以被輕易修正。主流新聞媒介的武器是媒體的批評,但是因為他們是通過羞辱攻擊同行達成目標,所以這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事實是,記者通常能夠克服這一缺陷,例如在責任之外進行工作或一些英勇行為。這些行為事實上也是被新聞業為杰出業績而設立的一系列大獎所激勵。但是如同布萊希特(Bertoldt Brecht)在很早以前就指出的那樣,社會并不依賴于英雄。
三
那么這些新聞從業人員和大眾傳播教育工作者都干什么去了?
首先,我認為應該認真對待新聞觀念,并針對當前所存在的問題開始仔細思考,以尋求可行或潛在可行的方法。我主張對從業人員和新聞機構做一些調查實驗,一些實驗已經開始了,但是應該有更多。
其次,原有的新聞理論課程設置要跳出單純地強調其對于公眾 “信息告知功能”的框架,應重新思考新聞專業主義最終能對維持和促進美國的民主做出什么貢獻。這種重新思考將意味著淡化新聞的 “故事告知者”的身份,也使得新聞業不再像當前一樣把“新聞稿的首發”(即搶先發表新聞)當作其主要目標。這種思考應該包括:民主是否必須建立在知識化市民基礎之上;新聞信息在鼓勵或幫助公民參與政治上有多大作用;如果不大,那么應該是何種信息;記者是否且何時能夠完全地告知受眾這個國家的政治情況或其他危機等。
第三,應該努力改變對記者職業傳統意義上的臆想,即認為每個接受過良好訓練的記者都能在極短時間的觀察和毫無先前知識儲備 (除了快速的Google搜索下和在 Nexis瞄了幾眼后)的情況下報道任何題材的新聞故事。這個古老的職業臆想也許能幫助記者與一個外行的觀眾進行交流,但卻無法滿足一個21世紀的觀眾的需求。更多的新聞應該從記者的鮮活采寫中得到提煉,這樣他們才能正確地報道被深藏的美國甚至世界的經濟社會政治事件。
第四,分析和解釋雖然是個籠統的說法,但可能是實現生動報道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理想的狀態下,分析和解釋將會提供新聞的背景信息以及重要事件的起因,這些是新聞的核心所在。同樣重要的是,記者自身的分析和解釋能力很可能造就“非官方的見解”,這些見解的得出完全取決于他們的新聞采訪和分析解釋技能。之后,記者們就能發表自己的心聲,不再依賴于那些官方的和有引用價值的信息來源來發表個人見解,取代那些在事件當天就發表評論的,不論自己是否了解事件的普通專家、專欄作家及時事評論員。
第五,應該更進一步關注新聞記者和受眾之間的關系。我們或許應該開始研究以下問題,即受眾何時渴望緊跟新聞的節奏以及何時會對一些特定議題產生濃厚的興趣,并探究其原因。此外研究者們也必須關注何時受眾能對我們所傳播的信息給予關注并理解,探討受眾的關注度滯后或者理解力退化時所應采取的措施。如果以上的這些問題能得到解決,那么便能找到使新聞工作者更有影響力的方法。如果這些報道無法與普通受眾有效地溝通,或者只能與社會精英分子保持溝通的話,那么新聞工作者對于社會民主的貢獻不僅不會增加,反而會不斷降低。
第六,新聞教育機構也許也該對新聞業的經濟運營方式有所改進,或者采取更現實的方法,即借用實用型的模式,找到一個靠低利潤來運營新聞媒體公司的方法,在限制利潤的同時,又給予其他激勵措施。我仍然認為,如果立法能彌補政府干預的漏洞,政府補貼是可行的,但是新聞業也會因此淪為一棵搖錢樹,將無法履行其對民主事業的義務。——譯自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工作者》2004年春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