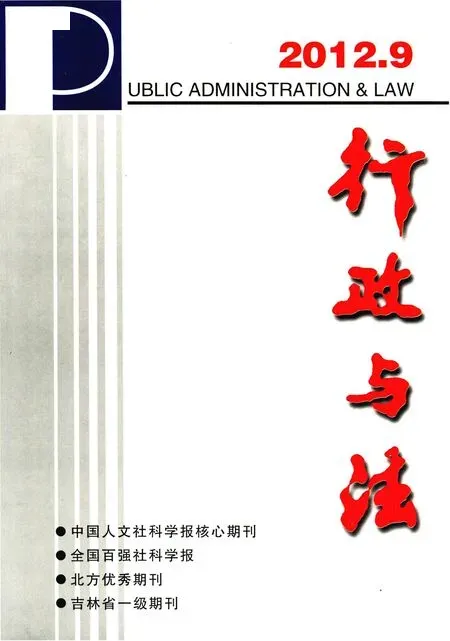試論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的構建
□ 謝勇才,汪興東
(⒈華中科技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4;⒉江西農業大學,江西 南昌 330045)
試論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的構建
□ 謝勇才1,汪興東2
(⒈華中科技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4;⒉江西農業大學,江西 南昌 330045)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征用農民土地的數量不斷增加,使得失地農民群體規模不斷擴大,由此也凸顯了征地單位與失地農民之間的諸多矛盾,因此,構建失地農民的社會救助制度就顯得尤為迫切。本文就當前失地農民的現狀、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不利因素以及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的構建等問題進行探討,以增強對構建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并為構建這一制度提供參考。
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構建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工業化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他們徘徊在城鎮和農村的邊緣,成為“務農無地、務工無崗、低保無份、創業無錢、維權無門”的“五無農民”,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可能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穩定因素。失地農民是我國當前最弱勢、最被邊緣化、最缺乏保障的群體,因此,妥善安置失地農民,保障失地農民應有的生存與發展權利,不僅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更是我國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
一、失地農民的現狀
在我國城鎮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村集體的土地大量被征用,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了他們世代耕種、賴以生存的土地,成為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失地農民。他們既不同于農村居民也不同于城鎮居民,不同于農村居民是因為他們雖然還保留著農民的身份特征卻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不同于城鎮居民是因為他們雖然身居城鎮,卻尚未被城鎮完全接納,不能享有城鎮居民所應有的權利。
目前,我國每年非農建設占用耕地約250--300萬畝,如果按全國人均耕地為1畝推算,就意味著每年大約有250萬到300萬農民變成失地農民。從1987年至2001年,全國建設用地占用耕地共3395萬畝,這還不包括各地違規占用耕地的情況。據多數研究者估計,至少有3400萬農民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1]從2001-2010年,全國建設用地占用耕地共3058.4萬畝(如圖1所示),這還不包括違規占用耕地、災毀耕地和生態退耕等情況,保守估計這10年又有3000萬左右的農民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因此,筆者認為,當前我國失地農民的數量應該在6000-7000萬人之間(如表1所示)。按照 《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提要》,2000-2030年我國占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失地或部分失地的農民將超過7800萬人,屆時我國失地農民總數將達1億人以上。[2]

表1 2001-2010中國建設占用耕地與失地農民人數情況

圖1 2001-2010中國建設占用耕地面積與失地農民人數的關系
由于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不清晰、征地補償標準偏低和農村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原因,相當一部分失地農民面臨著養老難、醫療難、再就業難和子女上學難等困難,如果不能解決好這樣規模龐大的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與發展問題,將會影響我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二、建立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經基本上實現了應保盡保,其他社會救助制度正在快速完善之中,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正在探索之中,因此,在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進程中,構建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十分必要。
(一)建立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是失地農民應對生存困境的需要
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后很可能陷入生存困境。一是因為當前我國的征地補償標準偏低,并且經過層層截留,最后分配到失地農民手中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一項調查表明,如果以成本價(征地價加上地方各級政府收取的各類費用)為100計算,則擁有集體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只得5%-10%,擁有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得25%-30%,60%-70%為政府及各部門所得。[3]二是受文化、技能、年齡、資本和政策性因素限制,失地農民再就業渠道較窄。除極少部分人被安置進工廠從事一些技術要求不高的體力勞動外,大部分失地農民不得不面臨著失地即“失業”的尷尬境地。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東部某省歷年累計200余萬失地鄉村人口中,有30萬人左右是貧困人口。西南某省20%的失地農戶僅靠土地征用補償金生活,25.6%的失地農戶最需解決的是吃飯問題,24.8%的失地農戶人均純收入低于625元,處于絕對貧困狀態。[4]
(二)建立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是維護失地農民合法權益的需要
失地農民與社會其他群體一樣,享有法律法規所賦予公民的一切權利與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由此可見,享有社會救助權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失地農民與其他居民一樣,在年老、疾病、喪失勞動能力等情況下,有權獲得政府提供的社會救助。
(三)建立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
社會的和諧穩定是以包括失地農民在內的社會所有階層之間的和諧為基礎的。當前,我國失地農民的人數在6000萬以上,已經成為城鎮社會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為推進我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經濟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然而,作為規模日漸龐大的群體,失地農民卻成為我國最弱勢、最被邊緣化、最缺乏保障的群體,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害。他們中的很多人雖然已經轉為城鎮戶口,但卻享受不到城鎮居民所應有的權利,處于極其尷尬的境地。一是失地農民群體很難真正融入城鎮社會,對所生活的城鎮社區沒有歸屬感;二是失地農民在城鎮工作、生活中經常受挫,產生了被歧視感和被剝奪感,因而誘發了他們的認同危機,容易產生消極情緒,出現一些極端的行為。據來自國土資源部的一份資料顯示,2003年上半年群眾反映征地糾紛、違法占地問題,占信訪接待部門受理總量的73%;其中,40%的上訪人訴說的是征地糾紛問題,這里面又有87%的上訪者反映的是征地補償安置問題。[5]為了保證社會的和諧穩定,構建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保證失地農民的基本生存與發展權利就成了當務之急。
(四)建立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是保證社會公平的需要
公平作為一種價值判斷標準,其內涵大致包含下列三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從制度結構、制度安排角度理解的規則公平即制度公平;二是從商品等價交換原則出發理解的公平即市場公平;三是從社會價值分配法則出發理解的公平即補償性公平。補償性公平是政府運用各種宏觀調控手段來彌補市場對收入分配調節的不足。[6]失地農民是在我國城鎮化和工業化快速發展且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缺位的情況下失去土地的,絕大部分失地農民僅僅得到了一小部分征地補償,很多失地農民雖然已經轉為城鎮戶口,但并未真正享受到城鎮居民待遇,而是成了社會弱勢群體或邊緣群體,在遭遇生存困境時,很難得到國家和社會的救助,這顯然有失社會公平。因此,建立和完善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在失地農民遭遇生存與發展困境時給予適當的扶助,是保證社會公平的需要。
三、建立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的不利因素
(一)立法滯后
目前,雖然我國已經制定了一定數量的社會救助方面的法律法規,但是多為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或者以更低層級行政文件形式出現。其立法層級較低,缺乏強制性和權威性,可操作性不強,各種變通和隨意更改現象屢見不鮮。在未出臺統一的社會救助法的情況下,已有的社會救助法律法規的救助對象主要是城鎮職工和農村貧困人口,失地農民往往被排除在外。
(二)意識淡薄
⒈政府缺位。從理論上講,對失地農民進行社會救助是各級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然而,地方政府把這項工作做好了,或許只有當事人能夠獲益,因為在當前某些地方政府還在以GDP作為主要政績考核指標的情況下,上級領導很難直接看到。并且在當前中央與地方事權和財權不匹配的情形下,許多地方政府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地方政府寧愿去抓經濟、搞建設、樹政績工程,也不愿意做事關失地農民社會救助這項工作。這是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缺位的主要原因。
⒉失地農民的集體無意識。現代社會救助是以尊重受助者自主權為前提的,采取主動申請、自愿受助的方式,即先由受助者提出申請,然后政府再給予救助。[7]而大部分失地農民由于自身文化水平較低且缺乏社會保障方面的意識,很少有人意識到社會救助是自己的一項基本權利,因此很少有人會主動要求得到社會救助。失地農民社會救助意識淡薄也是這一救助機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三)非營利組織發展滯后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非營利組織已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遠大的發展前景,其在失地農民社會救助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政府能力的不足。但當前我國的非營利組織發展還不完善,存在著組織內部管理混亂;缺乏經濟收入來源,從業人員素質不高;相關法律、法規制度不健全;沒有建立健全自律、他律、互律機制等問題,[8]在失地農民社會救助方面還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四、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的構建
(一)失地農民社會救助構建的原則
⒈公平性原則。社會救助制度的建立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使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社會成員得到及時、有效的救助,以保證他們的基本生存與發展需求。因此,社會救助應該盡可能公開化、透明化,各個環節都應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尤其是在當前我國城鄉、區域和行業等經濟發展差異巨大的情況下,社會救助的方式、內容和標準都應該在保持一定差別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縮小差別,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⒉綜合性原則。失地農民所面臨的困境主要表現在家庭生活、就業、養老、醫療、子女教育和住房等方面。構建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應該把滿足失地農民的多樣性需求作為重要目標,建立一個多層次、綜合性的社會救助體系,充分發揮社會救助體系的整體功能。社會救助制度不僅要滿足失地農民基本生存的需要,還要考慮其發展的需要;既包括物質方面的救助,也包括精神方面的救助。
⒊循序漸進原則。失地農民的社會救助應該是多層次的、綜合性的,既包括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臨時救助制度為主的基本救助制度,也包括以失業救助、教育救助、醫療救助、住房救助、法律救助等為主的專項救助制度。如果基本救助制度和專項救助制度同時建立,會需要巨額資金,將給政府財政造成較大的壓力。因此,應堅持循序漸進原則。首先,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臨時救助制度,保障失地農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其次,建立就業、教育、醫療、住房和心理等專項救助制度,救助項目由少到多、救助水平由低到高、救助范圍由小到大。這樣,能夠減緩政府因一次性投入過多資金所產生的財政壓力。
⒋政府主導與責任分擔原則。社會救助是指國家通過立法,對于因為自然和社會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生活困難,難以維持最低生活保障的社會成員,按照法定程序,以貨幣或者實物的形式進行救助,以維持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社會保障制度。[9](p85)因此,政府應該在社會救助體系的構建中發揮主導作用。在現階段乃至未來一定時期內,政府對于失地農民的社會救助制度的建設還需要給予更高程度的重視、更多的財力投入和更快的推進制度建設,以充分調動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集聚各方面資源,彌補政府力量的不足,最終促使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二)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體系的框架結構
筆者認為,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體系應該是多層次、綜合性、發展型的,它以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為基礎,以專項救助制度①筆者通過查閱文獻后發現,目前學者們多數認為專項救助制度包括失業救助、教育救助、醫療救助、住房救助和法律救助這五項制度,但筆者認為還應該包括心理救助制度。因為,失地農民是不同于傳統農民又有別于城鎮居民的邊緣性群體。一些失地農民由于“失地”而產生失意、不滿甚至恐慌、抵制情緒,而且失地農民由農村進入城市,由于生活環境的改變、自身的弱勢地位和社會配套設施的不足等原因,容易使一部分失地農民出現了生存危機感、工作挫折感、被歧視感等心理問題,急需專項的心理干預和心理輔導。為輔助,以社會互助制度為補充,在保障失地農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時,著力為其長遠發展提供救助(如圖2所示)。通過整合資源、職能和制度,形成政府主導、民政牽頭、部門協同、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資源,建立和完善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體系。

圖2 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體系框架
上述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體系具有以下顯著特征:第一,失地農民社會救助的責任主體是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尤其突出了政府在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體系中的主導作用;第二,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不再局限于最基本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還包括應對突發事件的緊急救助和保證一定生活質量的社會福利救助;同時,專項救助制度也不再局限于傳統的醫療、失業、教育、住房和法律等五項救助,還包括心理救助,為失地而產生心理問題的農民提供專門的心理輔導和干預,幫助失地農民更好地適應非農化和城鎮化生活;第三,在救助內容上,涵蓋了失地農民生存與發展的各個方面,不僅包括保障失地農民基本生活的制度,還涉及失地農民發展和維權方面的專項救助,從而使失地農民得到全方位、多層次的救助,各方面的權益都能得到維護;第四,失地農民救助資金來源于政府、社會和個人,但由于政府是失地農民社會救助的主體,救助資金主要應該來源于國家財政;第五,社會救助的目的不僅僅是保證失地農民的基本生存需求,更重要的是促進他們的發展。因此,構建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不但符合我國國情,也是解決目前日趨嚴峻的失地農民問題的現實選擇。
(三)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體系構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
⒈實行積極的社會救助。社會救助制度具有積極和消極的區別,這種區別還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積極的社會救助是指既提倡政府責任又提倡個人責任,既提供現金補貼又提供社會服務,既對現實貧困提供救助又采取措施預防貧困的發生或加劇的社會制度。在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建立和實施過程中,要注意實行積極的救助政策。如對失地農民提供就業救助時,應對其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增強其在就業市場中的競爭力,這樣,才能促進其盡快就業,從而逐步脫離貧困。
⒉發揮失地農民的可行能力。阿瑪蒂亞·森認為,一個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種自由,是實現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的實質自由 (或者用日常語言說,是實現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10](p62)因此,可行能力可以理解為一個人可選擇的空間的大小。在構建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體系過程中,應該充分考慮到失地農民的可行能力,讓失地農民有盡可能大的選擇空間,從而發揮失地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挖掘失地農民自身的潛力,進而實現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的良性發展。
⒊注意與未來失地農民社會保險的銜接。雖然當前專門針對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險制度尚未建立,但是已有一些省份開始試點,《失地農民社會保險條例》的提案也已經由民進中央于2009年上半年提交國務院。[11]筆者認為,隨著失地農民規模的逐步擴大和社會各界關注度的不斷提高,國家將逐漸重視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失地農民社會保險條例》的出臺也只是時間問題,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險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因此,在構建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的過程中,要在救助方式、內容和標準等方面堅持適度原則,為與未來失地農民社會保險的銜接預留足夠的空間。
綜上所述,建立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是我國城鎮化、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一項重要的社會保障制度,對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緩解征地矛盾,保障失地農民的權利與利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建立失地農民社會救助制度,既可以保障失地農民基本的生存權與發展權,又可以加速我國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進程。
[1]韓俊.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J].科學咨詢,2005,(07):28-29.
[2]郝悅.淺析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J].人口與經濟,2009,(S1):132.
[3]鮑海君,吳次芳.論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J].管理世界,2002,(10):38.
[4]張鳳龍,臧良.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J].行政與法,2007,(11):59.
[5]左金學,樓培敏.農村用地轉變為城鎮用地中的利益分配、相關問題及對策[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4,(01):42.
[6]周批改,徐艷紅.論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工社會救助制度的構建[J].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1):70.
[7]徐增陽,付守芳.農民工的社會救助:需求、認知與意愿[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02):9.
[8]仲偉周,曹永利.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其治理[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4(02):22-23.
[9]丁建定.社會保障概論[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0](印度)阿馬蒂亞·森.從自由看待發展[M].任賾,于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11]民進中央.關于制定《失地農民社會保險條例》的提案[EB/OL].http: //cppcc.people.com.cn,2009-07-16.
(責任編輯:高 靜)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for Off-land Peasants
Xie Yongcai,Wang Xingd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the expropriation of peasants'land and growing groups of off-land peasants continue to expand,which also highlights the many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land acquisition units and the off-land peasants,the most pressing one to solve is to provide social assistance for the farmers who have lost their land.This article explor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ff-land peasants,necessity and obstacle to established social assistance for off-land peasants and construct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for off-land peasants,in order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of off-land peasants and give it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off-land peasants;social assistance;system construction
D623.1
A
1007-8207(2012)09-0045-05
2012-05-01
謝勇才 (1988—),男,江西人,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社會保障;汪興東(1979—),男,江西人,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江西農業大學經貿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市場營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