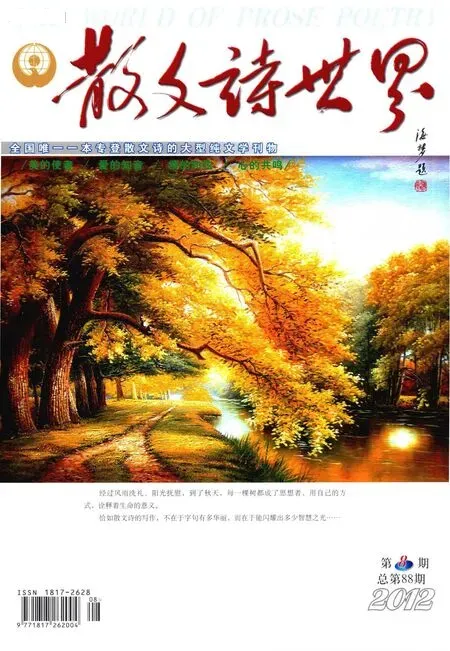曲全勝散文詩五章
山東 曲全勝
海 樹
桅,直立的桿。
一棵棵樹,一片片林。
紅。黃。藍一度交織的三角旗,遙遙展動于桅的桿尖(海樹之葉,烈烈于藍幽幽、幽藍藍的海天之間)。
陽光,潮一樣大篇幅地涌來。
咸腥的味兒扯著暖暖的氣息,如風送的音節,潮來潮去。
夜空之月,如一朵圓溜溜的艄公號子,響亮動人。
思緒在夜里行走,星星如閃耀的心事,拖瘦了你被風雨拉傷的身影。
漁女,累嗎?
男人命中有海,如同命中注定有海量的你。等待的日子,如海上充滿風浪和愛的歸期,瀟灑又豪放。
礁石背起千載的浪吟,如涌浪馱起孤舟,如你背起受傷的孤獨。
翹首望遠方。
海蠣是開放在礁石上一枚枚雪白色的花朵,斑駁的銀痕,鑲嵌著一只只耐讀的美麗。
月。每潮都被海水泡得很大,很圓。
你發漲的思緒,又一次鼓滿望歸的風帆。
漁女喲,你撫摸著身旁的兒子,如同撫摸著岸畔半截子的船樁,此時你幸福地感到一種結實。
男人的身軀,如海樹。
硬朗著最動人的風景。
岸頭柳
潮,升起來。
潔白咆哮的爪,吞噬。一道道溝溝,留下些奇型凸凹。
岸,瘦了的泥墻。
根絮斑駁,盤纏錯落。陽光下,如金屬的絲,舒展的弦。海風吹來,音韻錚錚,如吟唱的馬頭琴。
一席之地,一根軀干,支撐你疲憊的招展低垂。秋之花絮,是你苦澀的果嗎?
退了的潮,載著許多綠茵茵的絮兒,走了。
就像載了些絮語。
此時,你多像一位北方海量的女人,在潮退的瞬間,心海充滿一次漲潮的機會與渴望。
漂來的,不再是一葉孤舟了。
就像女人的歷史,
垂青在岸上。
海的訴說
月亮,涂一層粉白。
油光光的液色,浸泡得星星如顆顆生輝的燈盞,點燃晶瑩。
夜鳥拍打開寬闊的翅膀,于夜的浪尖律動。
墨綠的涌動仿佛從海之深處冒出的魅力,滿含著壓抑太久的情愫。
海,伸展升來。夜鳥在浪的脊背上寫下了瘦的爪痕,也寫下了疲憊的苦澀。是嗎?
海,訴說著。月亮,海里最亮的部分。星星是精彩中最閃光的情節。
漁女,望著久遠的藍。望著深邃的浪谷。
他在漁女筆記里深刻地寫下,男人在海上的風度是壯美的一種。然而她每次看到浪谷,都仿佛觸摸到男人硬朗的脊背(抑或感受到男人海量的呼吸)。
(遠去。海色無窮盡地遠去。)
月亮,是一彎女人的心思。
岸畔被垂柳遮蓋到崖角,打著花邊邊的浪朵涌來涌去,時而參差,時而深刻。
海,亙古以浪濤為語。
音色。在海天交響。
船 夢
顛簸的舟頁,一只駛上茫茫海域的小木船。
船會做夢嗎?船的夢會不會被苦澀的海水打濕。
海浪,傾訴著,從來沒有像今天這般洶涌后的舒緩。
海浪花漫過船頭,打濕了槳和升起的白帆,打濕了水手折疊已久曾未發出的家書。
搖動,因為浪的沖涌,海水的苦澀抽打著船身和那條潔白的吃水線。
船從來就喜歡動蕩,故鄉岸頭的白楊樹上結滿了會唱歌的水鳥,蓬勃的合歡樹下漁家女蕩起了風彩的秋千。憨厚硬朗的漁夫扛著漁網向海邊走來……
船之夢,魂斷礁叢。
曠野,岸頭柳生著春風幾度。
海里崢嶸的航標紅燈,為詩寫一路浪跡:船,是海的標簽。
船,把自己的童心與憧憬都交給海了,交給了萬里風浪。
海本來就是男人的疆場。
留下這樣的日記一頁,將燦爛一生。
礁石上,一位垂釣者
鷗鳥馱一片夕色飛來。
礁石上,一位垂釣者,伸出一竿醒著的靈感。
一只淺黃色的酒葫蘆掛在他的胸前,一頂頭笠被風吹得像海燕的翅膀,有節奏的扇動。
一條細細的銀線,系著蔚藍。
釣竿顫悠悠地伸向大海,探測海的深思嗎?
身邊金黃的竹簍里,魚兒蹦跳,魚兒的嘴里吧吧的直響,仿佛聞到了他喉嚨噴出的酒香。
好久沒有收竿了。
因為他知道大海的性格,是穩重深沉的,大海的賜予是智慧靈性與鮮活豐碩的。
夕陽西下,轉眼間,海水由粉紅色變為橘黃色,由橘黃變為淺藍色,又由淺藍色變為深藍色。
海,好神秘,好深邃。
銀絲一動,垂釣者驚喜地敏捷起竿,釣起一輪潔白鮮亮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