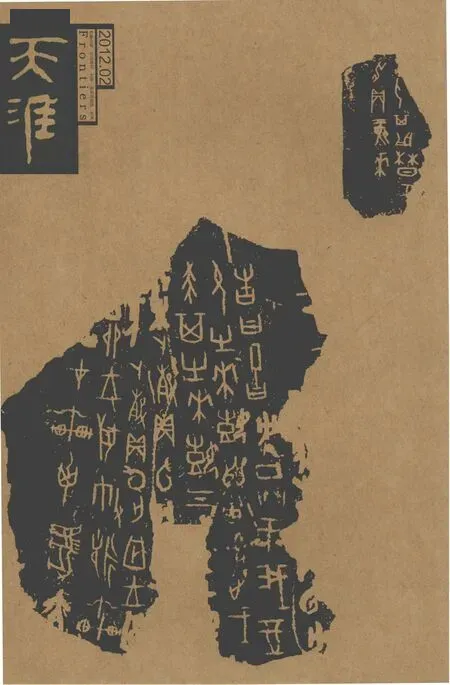今日學術體制與大學知識分子的生存
張均
今日談論學術體制與大學知識分子[此處所謂“知識分子”,僅指大學、科研機構里以專業知識為業的教師等從業人員,而不是薩義德所說的那種“代表著窮人、下層社會、沒有聲音的人、沒有代表的人、無權無勢的人”的知識分子的生存(見《知識分子論》,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95頁),那種人的出現在今日大學為小概率事件],很易流為憤慨之辭,甚至淪為對大學懷有最低信任的媒體的“共謀”。實在而言,媒體的立論方法,非我之所樂從。大約因為年近不惑,我已很不習慣僅從某種單一立場去衡事論人,哪怕它擁有正義或道德的名義。數年前,曾有媒體記者造訪,要求我就大學學術抄襲略表意見。我答曰:學術抄襲僅為稀見個案,我所在中山大學中文系,二十年來未聞一例抄襲;此種小概率事件,較之媒體之新聞“制作”,較之官場之公權力濫用,實無可論之處,若君誠關心腐敗,不妨采訪貴報總編,可以更近距離地了解媒體墮落的機制與路徑。這一說法自然不能見諸報端。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認為學界真無腐敗,或不嚴重,只不過我并不如“南方報系”那樣熱愛民國大學體制乃至民國的一切,亦不如部分知識者那樣,將今日亂象叢生之學界看得一無是處。依我有限的了解,建國六十年(尤其近三十年),我國在科技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堪稱卓越,遠非民國可相提并論。諸如載人航天、尖端武器、雜交水稻、高性能計算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核電利用等技術,實已處于世界前沿。在人文社科領域,也出現了大批優秀學者。本人偏愛史學,以我閱讀所見,中山大學桑兵、南京大學高華、四川大學羅志田等學者,實皆不可多得的重量級學者,其實力未必輸于諸多民國“大學者”。這些學術實績,非常值得肯定。這是我討論當前學術體制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我認為三十年來學術是存在嚴重問題的。從現象上看,三十年來尤其近十幾年學術的產出要低于投入,尤其低于預期。從深層看,當前學術體制作為學術生產的決定因素,其對學術的妨礙與促進幾乎同樣巨大。這與當前學術體制的設計理念、操作程序與目的訴求的復雜性有關。這種“復雜性”,在經濟上為學術研究提供了較好保障,但在價值上扭曲了學術共同體的內部認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抽去了科學探索所必須的理想主義“土壤”。
當前學術體制的“復雜性”,直接表現為政府主導的數目字管理。在中國,政府是學術的投資者,也是其裁定者。1990年代以后,隨著國家財政實力的提升,國家下撥的科研經費節節攀升。為獲取“立竿見影”式的投資回報,教育部不分學科、不分地域,針對大學、科研院所及其知識分子設計了統一的評價規則。在此體系中,從大學、研究院所到學科和知識分子個人,都被納入其投入—產出的管理程序。按照該程序,無論學校學科還是學術團隊或學者個人,都被“替換”為一系列數據:重要論文若干(理工科論文以影響因子劃分等級,人文社科則以南京大學CSSCI標準細分為一類、二類、三類等不同級別)、出版專著若干(出版社亦分國家、地方等不同等級)、獲獎若干(分國家、省部等級別,非官方獎項暫不列入)。這些統計數據,會轉化為“分數”,進而轉化為利益,被置換為從零到數以億計、百億計的不同投資等級。在這種量化管理體制中,數據突出者可以獲得“院士”或“長江學者”等學術頭銜,經費源源不斷,數據乏力者則會一文不名,甚至被大學掃地出門。這種高度差異化、競爭化的體制,構成了當前大學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其體制化之程度,空前劇烈。
這種極端功利的量化體制,對于技術領域的促進,確實收效甚巨,對于人文社科研究,也以其經費支持顯示了一定效果。但不必諱言,量化管理中的實用主義思維,對缺乏直接應用效應的基礎理論(如數學、物理學等)的發展實有限制,而面對人文研究中與當代政治有所關聯的學術領域,則顯示了極為保守和排斥的意識形態特征。甚至人為制定了數量不少的研究“禁區”,致使“研究者不得不放緩腳步,甚至繞道而行,避實就虛,遠險求安,造成不應有的損失”(湯學智:《探索更為合理的學術管理體制》,《山西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很明顯,這種體制很容易“管理”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故為求“安全”,為獲取經費支持,很多學者主動為“稻糧謀”,尋求遠離現實的課題,放棄公共關懷,甚至流于玄學化,喜歡炫弄理論術語,“不再與現實經驗有效地互動,不再承受社會運動的種種復雜挑戰”(南帆:《學術體制:遵從與突破》,《文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1期)。數量不少的學者甚至淪為“投機”分子:不是遵從自己內心的熱愛而從事學術,而是投學術管理機構之所好,僅僅為獲得經費而從事研究。與此同時,量化學術體制也引人注目導致了大學教育的滑坡。在1990年代以降的GDP“大躍進”中,教育部不甘其后。量化管理體制就是這種學術GDP追求的直接反映。在其急功近利的思維中,大學教育(尤其本科教育)實際上被邊緣化了。表面上,教育部屢屢下文要求大學重視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但由于在操作中,教學是被輕視的,教學質量不能進入考核數據,不能構成教育部所認定的學術GDP,進而也不能轉化為學術利益,因此教學首先被教育部的體制拋棄,繼而被數量頗多的大學知識分子拋棄。事實上,在大學里,教學認真、深受學生歡迎,只能使教師得到良心的安慰,而一篇一類期刊論文產生的學術效應乃至經濟效益,一輩子辛苦教學也難以及上。故從投入/產出的成本分析而言,放棄教學、專攻學術GDP就成為頭腦稍“清楚”者的必然選擇。云南“寶馬”教授尹曉冰說,大學教師“全心投入教學是毀滅自己照亮別人”,話雖偏激,卻也是實情。今日大學之所以仍還有一批熱愛講臺的知識分子存在,全賴于少數知識者的良心。教學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私人的事情,而明智者的“共識”則是敷衍教學,無意于教學方法的革新,不愿花費時間與學生交流,而力求以最少精力完成必須的教學工作量。


當前學術體制之弊,不僅在于以上因功利理念而致的三端,更在于其操作過程中“體制中的體制”對學術共同體的傷害。若說量化管理系統是看得見的體制,那么,權力、勢力對此體制的介入乃至主導,則成為另一種“看不見的體制”。后者不難想象:最近十幾年來,國家對科研的投入快速上升,已逐漸使大學從清貧單位變為各種看得見的利益的集聚地,這必然引起學界內外多方力量對利益的激烈競爭。競爭之結果,是使學術自身的規則逐漸表象化、邊緣化,而權勢角逐則成為表象之下真實運作的“潛規則”或“元規則”。
權力、勢力兩種力量之中,權力直接是當前學術界的主導性力量。在中國,權力是真理的代言人,學界亦不例外。大至國家重大科研項目的競標,中至院士、長江學者的評定,小至大學里教授職位的競爭,學術(又表現為一堆GDP數據)只是“準入”條件、“參考”條件,真正最后起決定作用的多是權力。不久前,我參加一文學研究會議,見一主持人春風得意,賣弄之辭溢于言表,頗感不適。會下才從其他學者的諷談中得知,明年教育部可能推行文科院士制,此人在學界雖僅中資(鄙人慚愧,第一次聞知其人其名),但已貴為某省最好大學之校長,兼高層關系良好,必得該省“院士”指標無疑。會上失態,實在是大好心情自然流露,“理解”起來并不困難。會下,眾學者還私議,當今學界,只要躋身大學校長、副校長之列,就有望成為“大學者”。何故?因為既為校長,就可以動用學校資源,做成其他學者想做而不可能做成的事情。譬如,只要校長于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寫成一兩篇論文,就可以經過某種“運作”發表在權威刊物之上,繼而又經過“運作”獲得各種級別的學術獎項,繼而依法炮制,成為國家級“教學名師”,“帶領”團隊申請國家級大項目。等將這些都“運作”成功,其學術GDP就非一般書齋型教授可以相提并論,而按照教育部的評價體制,校長就自然是“大學者”了。在項目評審中,權力的作用更一覽無遺。據說,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審中流行一種說法,叫“小基金大評,中基金中評,大基金不評”。意思是說,資助額度僅十幾萬元的基金(錢少得有權力者瞧不起),往往進行大規模的、民主化的評審,而資助額度達數十萬、上百萬元的杰出青年基金、重點基金,就只在“一定范圍”內評審了。所謂“一定范圍”,就是一群評委在一起“分豬肉”,去年給了你或你的學生,今年就該輪到我或我的學生了。而上千萬元的基金,索性就不評了,往往由幾個擔任評議組組長或副組長的院士提議,或由政府部門某領導拍板,直接下達給某人。而院士何以如此提議,領導何以如此拍板,除了比較不同基金申請團隊的科研實力外,還更多地牽涉到學術以外的諸多“不明”因素。這類“不明”因素,即是權力運作的灰色地帶。當然,權力畢竟是稀缺資源,多數學者并不直接是校長、國家基金或教育部評議組成員,那么作為權力的補充,勢力則以更普遍的程度主導著學術。勢力是指學界里的“圈子”或“山頭”,某些“山頭”中人未必直接擁有權力,但他們善于“攀援”權力持有者,或以師承關系相互交接,或以利益相互協同,或以性資源換取支持,在諸如項目、獎金、職稱等系列評審活動中分享權力的利潤。可以不夸張地說,在現行利益體制下,今日學界已在大概率意義上淪為“權勢者的游戲”,學術則不幸退居“次席”。

“權勢者的游戲”構成了今日學術體制的真實規則,也造就了大學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所謂“象牙塔”者,其實是“縮微版”的官場,不過涉及利益不能與政界相提并論,烈度自然也較小,但其設計理念與操作規則則大為仿佛。所謂“學術共同體”因此殊難自立。不難想象,這樣一個時代,對于大學知識分子來說,是壞的時代。但同時,它也可以說是好的時代。如果一個學者,潛心于學術,而不用心營造與各類權勢者的關系,那么他(她)的發展則會大為不利:職稱難評,項目難報,得獎基本無緣,若無意外的話,也將會在體制中被邊緣化。而由于缺乏經費資源,其學術本身的推進也會出現問題。尤其理工科,倘無充足科研經費,研究往往難以展開。甚至,這類學者即使克服諸種困難,取得突出學術成就,也往往不被學生“承認”。譬如報考博士時,很多學生會考慮:這位博士生導師是否是重要刊物主編,是否是基金評委,是否人脈廣泛?如果不是,許多學生會另選“高明”。對于這類知識分子而言,今天這個時代無疑很壞。但反過來講,對于持有權力者,對于善于“運作”者,這又無疑是很好的時代。這類知識分子,若有學術能力,則會得到超出其學術能力的充足資源。經費到手,則又可以通過開會、邀請講學、“合作研究”等多種形式,廣泛建立更多的人脈和利益協同關系,而這類關系又是獲取更多資源的良好條件,由此形成學術與關系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善于“運作”的學者,若學術資質平平,也可以以諳熟“關系就是生產力”的原則,廣結人脈,由學而官,由官再入學界,照樣可以兼為領導和學科帶頭人,甚至躋身為院士也不無可能。所以,今日大學里最光鮮者,并非皓首窮經的不問俗事的教授,而是這類學者而兼政客的雙棲人物。
對此種種“權勢者的游戲”,學者們私下里戲稱為“超現實主義”,但亦莫可奈何。這種公私雜糅的體制,對各類學者利益并不相同,但對學術自身的傷害則是共同的、持久性的。其傷害或還不在于學術資源配置的不公,而在于學術良知的流失,在于學術敬畏之心的耗散。很難想象,一個大學知識分子,若久久地熱衷于攀附或籠絡,周旋于交際和應酬,他(她)怎么可能長期保持對未知事物的無窮好奇、對知識的單純熱愛?“運作”思維發達的社會,科學探索的境界必被拉低,又怎能期望“大師”呢?那么,這種學術體制有無改變可能呢?不少研究者寄望于“教授治校”,如楊東平先生認為:“大學的核心制度、大學制度創新的根本要義,就是確立‘學術本位’的價值,在大學實行學術內行的民主管理,使教授真正擁有學術權力”,“如果一所大學仍沒有建立學術自由的價值,教授不擁有學術權力,那么無論它的樓宇多么高大、校園多么遼闊、設施多么豪華、校長是正部級還是副總理級,它也不可能是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更遑論什么世界一流。”(楊東平:《改革大學體制刻不容緩》,《南方周末》2007年3月29日)楊先生的愿望,實是尋求大學在政府之外的“化外治權”。其可能與否暫且不論,即便可能,“教授”們就真的那么可信嗎?我以為,不是所有“教授”都是蔡元培或梅貽琦。前謂“權勢者的游戲”,其中“權勢者”主要不是指政府官員,而指的正是身兼校長、院長、主任和各種評委之職的教授們。依筆者觀察,大學里部分知識分子,其城府之深,計謀之詭,角逐官位能力之強,壟斷資源欲望之盛,并不弱于政界同行,不過施展空間太小而已。設若教授們真能“治校”,出現一兩位蔡元培確有可能,但出現一大批“系霸”、“院霸”、“校霸”則必是大概率事件。當然,楊先生還講到“民主管理”。如果所謂“民主”是指每位普通大學知識分子都擁有一張選票,可以隨時通過投票罷黜院長、校長,那當然大有希望。如果“民主”只是十來位有實權的教授們“圈子”內的民主,那么有與沒有并無什么大的區別。嚴格地講,當前學界的所有評審都有比較公正民主的評審程序,但多數都被“運作”成了“權勢者的游戲”。以國人(含教授)“運作”興趣、能力之強,淺嘗輒止的“中國特色”式的民主幾乎不具備操作價值。
不過,即便是這樣的“教授治校”或學術民主在當前學界亦無實現可能。其一,現行學術體制不僅是政府規劃國家科技發展的頗見效率的積極手段,而且其實也是政府管理人文知識分子的巧妙“藝術”。例如,至今,我們的出版社、學術刊物,仍是國家嚴控的壟斷資源,在著作出版、論文發表時,學者們還要面對諸多看得見或看不見的門檻,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禁忌。在這樣一種沒有實質性的出版自由、發表自由的狀況下,真正的學術繁榮是很難的(楊守森:《學術體制與學者素質》,《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這是消極的限制方法。事實上,從積極層面上講,政府也更傾向于投資給那些文獻整理、古代典籍研究等與當代現實無涉的課題。其二,這一體制還得到了各層權力持有者的支持與維護。巨額科技研經費的下撥,并非全部流進了高科技實驗室或學者的書齋,同時也有相當比例的資金,以名目繁雜的權力尋租方式,進入了各級權力持有人的私囊。這方面,經費龐大的理工科項目更為明顯。還是在多年前,我就聽說某成果斐然的材料專家經多方“運作”,終于獲得一筆一千萬元經費的國家重大高新技術課題,但被要求私底下返給教育部相關人士三百萬元的“回扣”。此事真假不便確證,但某國家社科基金評委兼任某地方大學文學院院長(付酬如何外界不得而知,但該大學隨后即在國家社科基金評審中連年“凱歌”),則是圈內人所皆知之事。盡管如此,學界中人對此多已“司空見慣”,不以為意。至于學術刊物發表論文收取版面費、合作辦刊、以各種變相方式接受作者送禮,雖也是權力尋租之一種,但完全微小得不值一提。可以說,從上至下的各層權力持有人是喜愛現行體制的。此外,這種體制運作多年,已培養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群體,他們同時掌握了資源權和話語權。這類學者也愿意這種體制繼續維持其再生產。目前對此體制懷有不滿者,主要是在此體制中被邊緣化的和少數懷有學術公義的學者,但他們不足以撼動現行體制。
既如此,在這種“權勢者的游戲”中,今日大學知識分子是如何生存的呢?依筆者觀察,實有四種區分。一,雖操學術之業,但深知做官乃中國最快致富之職業,所以,一邊奮力打拼學術GDP,一邊緊盯大學官場,希望以學術為跳板,學而優則仕,并寄望從大學進入政府,真正步入政界。這類知識分子占相當比例。二,鐘愛學術,卻又不能不投身這場“權勢者的游戲”,用心經營各方面人脈關系,努力爭取學術資源。這類學者可能為最多數。但既為游戲,就有成功、失敗之分。其中的成功者,學術優秀,但為保證這種“優秀”,往往不得不出任行政職務,亦因此陷入了吊詭的處境:在中國,只有做了官員才能更有利獲得各種學術資源,然而一旦做官,雜事纏身,學術即幾近荒廢。等到任滿卸職,學術狀態卻難以恢復。這類學者在“道”與“勢”間頗為糾結。其中的失敗者,代價則更明顯。他們未必能成功地獲得有權力者的提攜,卻往往為了迎合項目、迎合權威刊物的風格,不斷“調整”自己,結果丟失了有價值的研究對象和獨立的自我。三,熱愛學術,也承認“權勢者的游戲”,但只愿以游戲態度對待論文、項目、獎之類,會適當爭取,但不會傻到將之視作有價值的評判標準,不會以之“自律”,更不會為之改變自己的學術方向。這類學者,其實是“以出世的心情做入世的事業”,是大學知識分子數量不多但毋寧最具智慧的一類,他們可能在利益上收獲很多或很少,但他們在學術上往往最能獲得回報。四,世事洞明,徹底放棄“權勢者的游戲”。不過這類知識分子極為稀見,而且在現實中也日漸喪失生存空間。十幾年前,我的老師一代人還相信“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學術姿態,然而今天在教育部的“指揮棒”下,這種邊緣人物已不可能生存下去,至少在中山大學這種“研究型”大學里,情況如此。按照中山大學職稱聘任制度的規定,如果一位教員,在三個任期內(九年)未能使自己職稱“升級”,那么他(她)就將被解聘。也就是說,縱使你個人甘坐十年“冷板凳”,中山大學也不給你坐了。你想鄙屑權威刊物,鄙屑項目,那中山大學只好請你到校門外去“鄙屑”了。
對權勢而不是對學問的不同態度,構成了大學知識分子的不同生態。這決定了當前學術并不樂觀的前景。由于所謂“學術共同體”整體上已被權力和勢力雙重扭曲,學術在中國喪失了必要的價值“土壤”。當然,由于中國人的可觀智商,未來技術突進可以預期,甚至出現一兩位世界級人才也不為奇(譬如獲諾貝爾獎),但中國科技不會整體性占據世界前沿,尤其在基礎理論領域。愛因斯坦這種偉大科學家的出現,需要的不僅是天才,而且還有對未知世界的深邃的愛,對知識自身的迷戀。這類天才往往疏離于俗世世界,但在“權勢者的游戲”中,這種天才尚未成長,即有可能被邊緣化,被現實利益體系拋棄。人文領域亦然。在部分缺乏現實性的人文學科(如古典文獻學、考古學之類),將來可能繼續出現一批優秀成果,但能夠影響時代的學術、能夠在歷史上占據位置的思想,必然會被體制抑制在萌芽狀態。對于這類缺乏經濟效應甚至帶有開啟民智之“不穩定”因素的學術而言,當前體制毋寧是妨礙性的,甚至是毀滅性的。
當然,我也并不以為這是歷史上最壞的時代。魯迅曾經說過:“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3卷,第17頁)當前學術體制之利弊,未必完全是當前政治或具體領導的問題,它的內部是否也飄蕩著傳統文化的“幽靈”呢?實在大可思考。譬如,倘若整個社會是如此地崇拜權力,倘若所有人群都將知識視作通向權力的路徑來“尊重”,我們又怎能指望“象牙塔”獨自舞蹈于權力之上?故我們與其像媒體那樣為謀奪眼球大力講述“學術腐敗”的故事,不如回到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我真的熱愛知識嗎?我們不妨這樣輕輕地問一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