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多米諾骨牌
舒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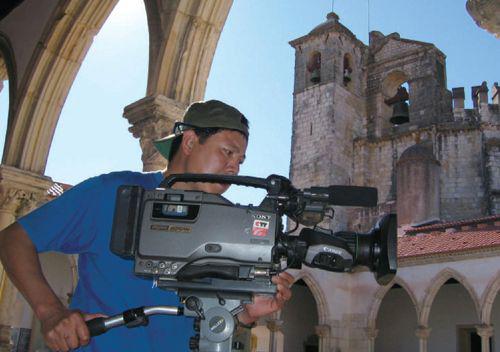

80年代的高考落榜生
上世紀80年代,高考成為一代人的人生洗禮,或因之勃發,或就此折戟。千軍萬馬前的獨木橋將當年的落榜者和他們的夢想擋住,與橋另一頭的人命運從此分岔。在當時環境下,高考失利成為了他們的人生夢魘,然而他們不能停下腳下步伐,仍然還要前行。如今的他們或消沉、或迷茫、或堅持、或珍惜。命運無常,活著也是一種勇氣,但他們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一代人的堅韌。
高考給我留下了終生陰影,我恨高考。——周鴻飛
45歲的周鴻飛夢中經常出現的一個場景是在高考前一天,依然還有很多卷子沒做,且一拿起書,發現數理化好像都沒有學過似的,心里極度煎熬。“在最著急的時候忽然醒來,仍心有余悸,大汗淋漓。等確認自己是睡在自家的床上,這才長出一口氣,心想,這輩子再也不用考試了,一下子輕松了。”
“三考落榜”遁入“死胡同”
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但對周鴻飛而言,在某種程度上則是“高考決定命運”。
周鴻飛住在一座小城里,每天早上出去買菜都會經過那座鋼筋凸露,銹跡斑斑的長江大橋,而那里有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記憶片斷。
20多年前,他經常慫恿顏孟良偷出大人的二八自行車,他們一起從縣中飆到大橋橋頭,那時正值高中,是他們追夢的年齡。
顏孟良曾是他的鐵哥們,家境好,父親是縣供銷社干部,但在校園里,卻只是一個矮小,戴著眼鏡的“小角色”。真正的“大明星”是周鴻飛,他雖只是個農村娃,但與生俱來的青春活力讓他處處散發的機靈勁,不過幾次高考,將他們倆的命運以及關系,永遠改變。
“當時社會上追捧詩人,我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就想學文科,結果被顏孟良給‘鄙視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說了一句‘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績不好的才報讀文科,我心想,誰怕誰啊。”周鴻飛撓撓頭,“事后證明我真不是學理科那塊料,最后成了‘三考學生——三次參加高考”。
周鴻飛承認,自己在學習上是有點懶,也不夠集中精力,坐不住,剛上課就想下課。但面子的問題讓他格外糾結,稀里糊涂讀了下去,結果可想而知,1985年,他連預考都沒通過。
“那一次,顏孟良也沒過。”周鴻飛苦笑,“剛開始想法很單純,既然都沒過,大家都不傷面子,一起重考唄!其實顏孟良比我慘,他是連續兩年沒過預考,我第二年是參加了正式高考的,差8分,那一年的錄取比例據說不到2.5%,你們這一代的大學錄取率就高得多,幸福啊!”
“但你們那時的大學生包分配,才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考,我們早就是畢業就失業了。”記者開起他的玩笑。
“哦,那倒是。”周鴻飛想了想,又說,“不對,你們機會多……”但久久也說不出什么。
周鴻飛沒想到的是,自己無意中已踏入了命運安排好的一條死胡同——多舛的補習、重考之路。等到第三次高考時,他信誓旦旦地告訴家人,這次行了。但發榜那天,周鴻飛三個字卻依然未能出現在縣委門口那張紅紙上,總分比上次還少了3分。走在回家的路上,五味雜陳,雙腿發軟,如遭雷擊,大病6天。此后,周鴻飛從一個活潑外向的人活脫脫變成了一個陰郁、多愁善感的人。
周鴻飛說:當時的年輕人對考大學到了瘋狂的地步。他熟悉同校復讀的兩個男生,先后復讀參加了8年高考。而那年頭是限制報考年齡的,所以這兩人每年的報考年齡都是“20歲”。“作假唄,但周圍的人都能‘理解,也沒有人會去舉報。”周鴻飛感慨,“8年,日本鬼子都投降了!他倆讀到了當年的好多同學大學畢業,有的同學還分來當過他的老師呢!”
“當時大家都很瘋狂。”周鴻飛從煙盒里里抽出一只煙,很快,一縷縷煙霧開始在他蓬松的發間繚繞,“我們班還有幾個同學,在離家兩百多里遠的地方找了一家學校復讀,主要是想避開一切熟人,他們只求高考后能金榜題名,一鳴驚人,有的人甚至不但改了名,而且把姓也改了。”
命運下的自我放逐
班主任的兒子呂萬鵬在周鴻飛眼中曾是個反例,呂家是當地生活條件比較優越的,家里為了讓他接受到最好的教育,頻頻轉學,從本地讀到涪陵,再到重慶,人們形容是“從南半球讀到北半球”,但高考還是落榜了,經受不住打擊的呂萬鵬后來去瀘州賣襪子,經常在瀘州醫學院那一帶捏著一把襪子邊走邊甩邊叫“賣襪子咯,賣襪子咯,五角錢一雙,買了襪子走”。
周鴻飛不止一次做夢,夢到自己變成了呂萬鵬,在外面賣襪子,每次醒來都是一身冷汗。但該來的始終要來,周家在農村,家里看他考了三次都不中,逐漸失去了信心。顏孟良則發了狠,從高二重新讀起,再戰兩年來準備高考。于是,一對好朋友原本平行著的的命運軌跡線由此漸行漸遠。
“母親當時在文廟給我求了一張簽,下下簽,大意是說我命中沒有功名這頂帽子,應該出去打工了,那時縣里已經有人去深圳了,有一些還賺到了錢;而顏家求到的是‘忽有魁星來點額,詞傾三峽涌波濤。許你定做蟾宮客,脫下蘭衫換紫袍。”周鴻飛言語中露出不少惆悵,“他這幾句我一輩子都記得住,自己的反而不記得了,他的確是早換了紫袍了。”
“我們被高考淘汰下的這群人的命運是殘酷的,簡單說,考上就成了干部,這是普通人唯一的出路。”周鴻飛眼神慘淡,仿佛又回到了當年,“考不上的,像我這種農村的只能當農民或者出去打工,當然,城鎮的學生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家待業,慢慢等招工,但國企人滿為患,大多數人只能進入小型集體企業,大都是一些鄉辦工廠。”
那年秋天,周鴻飛就背起鋪蓋卷,跟著家鄉的幾個熟人上了前往廣東的火車。“那時的車太擠了,我們是爬窗戶翻進的火車。”周鴻飛說,車內塞滿了人,廁所堵塞后,里面的糞水順著過道流過來,整個車廂臭氣熏天。
到了深圳他才發現,南方也不完全是天堂,找工作處處碰壁。為了節約錢,他經常穿上最厚的衣服,睡在橋洞下面。堅持了40多天后,他終于挺不住了,輾轉回到家鄉。
那時的周鴻飛萬念俱灰,“父母總是說一些話來打擊,說我怎樣沒用,我找了很多份工作都不成功,我知道這和遭受幾次高考失利的打擊,性格變得自卑有關。每當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里我會感到不安,不太敢和別人說話,其實更多的是怕說錯話做錯事,又不知道要說些什么話題。其實我很恐懼自己為什么變成了這種性格,想自己變得活潑外向些,可真的很難。”
曾有親戚介紹周鴻飛去環衛所做臨時工,大夏天里他推著垃圾車都要戴著帽子,遇到昔日同學,不敢抬頭。好在等到了縣里肉聯廠招工,周鴻飛進了工廠。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大斧頭砍豬腳,五六十公斤的桶,每天要砍40多桶,右手腫得抬都抬不起來,已經數不清我砍壞了了多少把刀。以前讀的書一點也用不上,當時真的很灰心。”周鴻飛將手中的煙用力嘬了幾口,然后,用中指,將那煙頭彈出一道拋物線。
高考陰影一生相伴
到了90年代,昔日考上大學的同學們陸續畢業了,大多分配到機關單位和大型國企,這些都不斷刺激著周鴻飛的神經。
“學生們朝夕相處,嘻嘻哈哈,但經過一場高考后,分數線以上的人成為‘天之驕子,分數線以下的人只好自謀出路,我可是用一輩子的時間才體會到了。”周鴻飛說著嘆了口氣。
周鴻飛也有過機會,廠里幾次提干,工作能力和業績都是排在前面,但往往到了最關鍵的一步,都會因學歷不夠遭到一票否決。
周鴻飛回憶,在80年代,那些考上大學的農村學生可謂“鯉魚跳龍門”,一個村甚至一個鄉的親朋好友都會奔走相告,經濟實力稍微好一點的,還要大放鞭炮,擺上酒席慶賀一番,不亞于過去中舉人的排場,而城里的學生考上大學就更不用說了。記得顏孟良考上大學時,他們家在大街上放了三掛一千頭的鞭炮,并花錢請了電影隊,在中學操場上掛起銀幕,連放三晚電影,那可是“氣焰囂張,不可一世”啊。而沒考上的那些人,家庭條件好的還有讓父母提前退休,勻出一個頂替的機會,但大多人都只有自謀出路,并且還會被人瞧不起,
“看看那些上了大學的同學們,隨便一個人都比我活得滋潤,顏孟良畢業分在了鄰縣財政局”。周鴻飛開始變得失落,雖然顏孟良也會偶爾去看看他,當年的老朋友見面后,表象上依然是熱情如故,但談論的話題卻越來越少,兩人之間已有了隱約的一絲隔膜和尷尬。
周鴻飛拖到了30多歲才結婚,但最讓他放不下的卻是當年一起復讀時的那個女孩子,她正是周鴻飛當年堅持復讀的動力。在寒冷的冬天,她總是早早起床,到學校圖書館頂著寒風排隊,僅僅是為了讓周鴻飛多睡半個小時。她話不多語,但經常會留下一張小紙條,悄悄地塞進書里:飛,你不要著急,即使你考不上我還是會跟你的。
“當時她媽看不起我,到我們家鬧過幾回。我恨自己太脆弱,因為如果自己再考不上,不知道今后會去哪里,我不能帶著她一塊兒流浪……那女孩最終考上了江蘇的一所大學,后來留校,有過一次婚姻,現在已經出國。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我一定要去復讀到考上為止。”
至于周鴻飛自己,工廠后來效益不好,6年前就買斷了工齡,被逼得二次南下廣東。他做的時間最長的是軟件銷售,每月2000元底薪外加提成。可是,讀過大學的職員工資往往比他高出很多,這給周鴻飛帶來不小“刺激”。
打工的生活并沒有想象中的美好,他最后還是決定回家,就這樣,周鴻飛的生活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每天二兩燒酒、幾碟小菜的日子。妻子白霞不止一次埋怨過他,叫他該找已官升副縣長的顏孟良看有沒有門路,但周鴻飛每次都是扔出一句話:“不管他愿不愿意幫,能不能幫,最重要的是我丟不起那人!”
周鴻飛去年得了糖尿病,妻子要他改掉常年不運動的壞習慣,多去散散步,但他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事,縣城里熟人多,且都愛在濱江路轉悠,老遇到還是覺得丟人”。
“多大點事兒啊!這么多年了,誰還記得?誰又在乎?”白霞覺得這個和自己一起生活了10多年的人愈發不可理喻。
“我在乎,因為我一直是個失敗者,尤其不想碰到顏孟良。我沒‘鴻飛,他沒‘孟良,你瞧,我們倆這名字取得多差。”周鴻飛一臉愁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