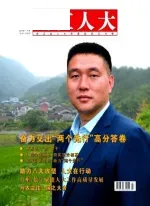信訪越萎縮,法治越成熟
2012-12-05 09:24:56文/王琳
浙江人大 2012年3期
文/王 琳

“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信訪不信法。”各地召開的“兩會”上,很多人大代表都指出,做大信訪會傷害法治。
取消信訪制度的呼吁并不“雷人”,在學界,信訪制度其實一直備受非議。因為信訪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司法的確定性和最終性,也為行政干預司法提供了一條制度管道。
但信訪制度在當下這個特殊的轉型期,又具有某種現實意義。如果我們以大歷史的視野實證觀察信訪,就會發現這一制度正在政府與社會之間發揮著一種類似減震器的奇特作用。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我國推進真正意義上的法制建設不過才30來年。一個有別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司法系統驟然融入到“三千年所未有之大變局”中來,出現不適和失范并不讓人感到意外。
這一時代背景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司法權威初立,司法公信始彰。無論是在官場潛規則上,還是在民間的文化心理上,公眾總是習慣于在司法裁判之外再去尋求更為權威的官員來“討個說法”。在這種極為普遍的民間心理未被疏導為現代公民意識之前,一味地拒絕信訪可能會導致社會的更不穩定。
隨著國家法制化程度的不斷提升,信訪也日漸與法制接軌。無論是從過去,還是從將來來看,“信訪越萎縮,法治越成熟”恐怕都將應是一條基本規律。對于大多數信訪事件而言,如果當地政府和當事單位能及時依法處理,訪民們才用不著上訪!
長遠來看,取消信訪制度應成為共識。問題只在如何取消。在民怨未得到有效渠道宣泄和紓緩時,取消信訪難免莽撞。規范執法、強化責任、放開外部監督、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這才是將來取消信訪制度的路徑選擇。
猜你喜歡
光明少年(2024年5期)2024-05-31 10:25:59
當代陜西(2022年4期)2022-04-19 12:08:5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s(2022年1期)2022-02-08 03:23:58
遼金歷史與考古(2019年0期)2020-01-06 07:44:44
娃娃畫報(2019年11期)2019-12-20 08:39:45
中國衛生(2016年7期)2016-11-13 01:06:26
中國衛生(2016年11期)2016-11-12 13:29:18
中國衛生(2016年9期)2016-11-12 13:27:58
中財法律評論(2016年0期)2016-06-01 12:17:10
中國衛生質量管理(2010年4期)2010-01-22 07:2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