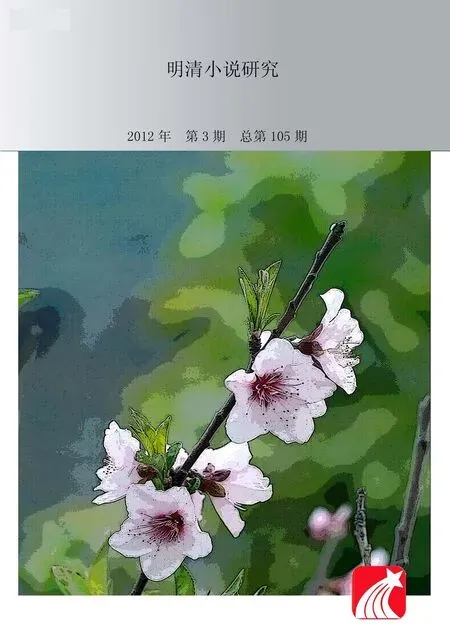明清劍俠小說文化觀剖析
··
明清兩代,劍俠小說創作十分流行。文言小說數量眾多,編輯選本風行一時,出現了在文學史上較有影響的《劍俠傳》、《續劍俠傳》等文言小說集。白話小說創作也是成績斐然,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長篇小說類型,具有比較明顯的文體特征和文化印跡。尤其在文化觀念上,其獨特而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更能突出地體現這一類型小說的“異度空間”。鑒于學術界對此研究領域的欠缺,本文擬從修行觀、生命觀、宇宙觀和情愛觀四個方面予以論述,試圖對明清劍俠小說的文化觀進行一次較為系統而全面的考察,剖析其獨特的“基本文化架構”,以便讀者能夠較為準確地理解和把握這一文學品類①。
一、道俠一體的修行觀

劍雖是神物,未經仙家“煉”過,仍不合用,須劍俠施以法力才有神通。《童之杰》中女劍俠對童之杰的寶劍這樣評價:“此道家蕩魔劍也,非吾輩所用者,故須人力,始克奏功。若吾劍之飛騰變化,則行之無阻矣。”②可見它與劍俠所煉之劍有別。劍俠所用之劍經過法力煅造,能搓劍成丸,大小隨意,且具有驅魔意識。《仙俠五花劍》中公孫大娘的五花神劍——芙蓉青劍、葵花黃劍、榴花赤劍、蘚花黑劍和桃花白劍,是她“在丹房采日精、月魄、電火、霜花并雷霆正氣而成,其質非鋼非鐵,乃是落花之液釀成。每花只取乍落的第一瓣,故得先天第一肅殺之氣,和以鉛汞,計凡千煉始成。劍質可以吹毛使斷,濡血無痕,削鐵如泥,砸石成粉”③。五花神劍由于經過劍俠公孫大娘的冶煉,可以飛行變化,具備極大神通,其中芙蓉青劍尤其了得。劇賊燕子飛得了此劍,為非作歹,眾劍仙居然無奈他何。為了制服此賊,公孫大娘又煉成霜鍔丸,花了361天時間,“這劍丸乃取百花上所受之霜,積而為液,和以鉛汞,鍛煉而成”。百花經霜而凋,以霜鍔丸破五花劍,實有天然相克之理④。霜鍔劍丸煉成后,眾劍仙終于將燕子飛鏟除。鄭官應《續劍俠傳》中收錄明代錢希言文言小說《青丘子》,較詳細地描述了劍俠“煉劍”的過程:
室中有藥鼎,高數尺,周遭封固,紫焰光騰,照耀林壑,第教生以守爐看光,添縮薪炭,不得擅離妄視而已。每晝則有玉女持稠膏一筒,投鼎中,攪和之,鼎中聲類霹靂。夜半則有青童復持稠膏,依前沃入,其聲漰湱如舊。此室之中,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應,日以為常。生偶問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對。先生已具知之,慍怒詬責,便欲驅逐出門,眾相跪請,乃止,后遂不敢發問。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計可六百余斤,分而為二,又折至七八斤而止。移至大磐石上,搗之,晝作夜息,漸漸而薄,因成鐵片。擇甲午、丙午諸日,鑄成六劍,懸于絕壁之下,以飛瀑濺激其上,日月之光華燭之。歷經旬朔,劍質始柔。此六劍各有名目,先生舉一畀生,令童子開啟腦后臂間藏之,亦無所苦。⑤
青丘子隱居深山煉劍,有專備煉劍的凈室、藥鼎,有青童玉女守爐看火,金液出爐后,又在大磐石上晝夜錘搗,并以飛瀑濺激,以日月光華照耀,方才煉成寶劍。這類詳盡的“煉劍”描寫無疑是道教冶煉金石制作丹藥過程的形象敘述。
上述煉劍屬于“外煉”,更具有宗教想象力的是“內煉”——“以氣煉劍”。《女仙外史》第8回九天玄女教唐賽兒“以氣煉劍”:
(玄女娘娘)就把劍來,如屈竹枝一般,嘩嘩剝剝粉碎若瓜子,都吞在口內,咽下丹田。瞑目坐有半日,只見玄女娘娘微微張口一呼,一道青氣約丈有七八尺,盤旋空中如虬龍攫挐之狀。飛舞一回,將氣一吸,翕然歸于掌上,是一青色彈子,付與賽兒道:“此劍也,你再吞入丹田煉它九日,就能出沒變化。”又傳以煉劍之法……賽兒將青丸吞下,按秘傳之訣,以神火鍛煉五日,覺在腹中盤曲旋繞,或伸或縮,也就張口一呼,見青炁飛向空中,長有七丈余,不覺大駭。遂忙忙吸入,再加鍛煉,只覺腹內動掣有力,不能容受,只得仍然呼出。在空中旋舞片刻,再吸入時,越不能容。賽兒知道必有差錯,乃靜候玄女駕臨。⑥
九天玄女的“以氣煉劍”法是道教“服氣術”與內丹術的夸張表述。“服氣”是道教中以氣息吐納為主的煉養方法,其理論基礎是道教生命元氣論。道教把“氣”作為生命賴以維持的根源之一。道教經典《太平經》宣揚“氣本論”,《老子想爾注》中有關于聚氣成形的修仙大法,《云笈七簽》綜論“行氣”、“調息”、“吐納”的“諸家氣法”,認為:“人與物類,皆秉一元之氣而得生成,生成長養,最尊最貴者,莫過于人之氣也。”⑦內丹修煉是以人體為鼎器,以精氣神為藥物,在意念的操作下掌握陰陽和合的火候,根據“逆而返還”的道理,使周身氣息從“有”歸“無”,達到“五氣朝元”的境界。鼎器、藥物、火候是內丹修煉的三大要素,唐賽爾就是因為沒能掌握火候,煉劍過程便出現了差錯。
“以氣煉劍”的情節雖是小說作者的藝術夸張,但有道教理論為依托。《真龍虎九仙經》中在“煉精華為劍,巡游四天下,能報恩與冤,是名為烈士”四句經文下有唐代著名道士羅公遠、葉靜能的注文。羅公注曰:“第七氣俠,唯學定息氣,便將精華煉劍,劍成如氣,仗而往來,號曰氣劍也。”葉公注曰:“俠劍者,先收精華,后起心火,肺為風鞴,肝木為炭,脾為黃泥,腎為日月精罡也。腎為水脾,土為泥模,身為爐,一息氣中,為法息成劍之氣也。”⑧經文及羅、葉兩人的注,可以看作是對“以氣煉劍”的宗教理論闡述。
除了煉劍之外,劍俠在修行中還特別重視服食丹藥,以此作為修行的重要輔助手段。中國傳統觀念一直認為食用藥物可以除病消災、延年益壽。《列仙傳》就大量記載了凡人因服食天然藥物,不饑不寒,身輕如飛,返老還童,長生不死。道教對這種服食觀念加以繼承、吸收,使之理論化,形成了效乾法坤、顛倒五行的金丹修行理論。東晉道士葛洪在《抱樸子內篇·金丹》中說:“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記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⑨葛洪還對這種“假求于外物以自堅固”的金丹養生術進行了理論探討。受此影響,小說中的劍俠往往在修行中借丹藥改變氣質,增進功力。《淞隱漫錄·姚云纖》寫姚云纖學劍:“尼啟甲得紅白丸各一,令齋戒沐浴,然后吞之。十日后,自覺身輕捷如猿猱,力能舉重物。每晨于庭中舞雙劍,人但見萬道寒光,絕不睹其身;空中有鷹隼過,飛劍擲之,無不下墮。”⑩《仙俠五花劍》中白素云是一個嬌怯怯的女子,學不得劍術,紅線便給她吃了一粒金丹,使其易筋換骨,氣質大變。《綠野仙蹤》冷于冰向徒弟介紹丹藥在修行中的作用:
丹藥乃天地至精之氣所萃結,非人世寶物可比,不產于山,定產于海。既系珍品,自有龍蛇等類相守,更兼妖魔外道,凡通知人性者,皆欲得此一物食之,為修煉捷徑,較采日精月華,其功效倍速。仙家到內丹胎成時,而必取自于外丹者,蓋非此不能絕陰氣,歸純陽也。
小說第93回又詳細介紹各種仙丹在修行中的作用。此類服食仙丹與修行相濟,增進功力,速成劍術的描寫,是劍俠小說常見的情節。
除了服食與煉劍,劍俠的修行還包括行俠人間,干預社會,這是為了“外積功德”。《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云岡縱譚俠》中劍俠韋十一娘說:“世間有做守令官,虐使小民,貪其賄又害其命的;世間有做上司官,張大威權,專好諂奉,反害正直的;世間有做將帥,只剝軍餉,不勤武事,敗壞封疆的;世間有做宰相,樹植心腹,專害異己,使賢奸倒置的;世間有做試官,私通關節,賄賂徇私,黑白混淆,使不才僥幸,才士屈抑的。此皆吾術所必誅者也。”《綠野仙蹤》火龍真人收冷于冰為弟子,特意叮囑:“凡有益于民生社稷者,可量力行為,以立功德。”并借冷于冰之口稱:“修行一道,全要廣積陰功,不專靠寧神煉氣。”第45回更明確指出:“玄門一途,總以渡脫仙才為功德第一……其次莫如救濟眾生,斬妖除逆。”小說中的劍俠總是把扶正祛邪、解救生靈作為修行的必要功課,自覺地擔當起“替天行道救蒼生”的重任。《墨余錄·河海客》中總憲公子依仗權勢,強搶民女,欺壓百姓。劍俠河海客身居海外,特意趕來為民除害,他對總憲公子說:“余本越人,幼學劍于太華山,術既成, 即遨游海內,專理人間不平事。今聞汝父子惡稔已極,特來除之。”《剪燈余話·青城舞劍錄》中真無本、文固虛兩位劍俠,隱居深山修道,但仍關心國事,時常出山誅殺惡人,亦仙亦俠,所謂“英雄回首即神仙”。劍俠修行,既要內煉為本,又需外積功德,內外兼修,才能功德圓滿。
服食與煉劍是內煉氣質,替天行道、干預社會是外修功德,不論是“內煉”還是“外修”,劍俠的修行都與道教密切相關。內煉氣質采用的各種手段,如服食丹藥,行氣導引,吐納調息,以及內丹修煉的“和合陰陽”、養心煉神等都是道教的煉養方技,而外修功德也與道教的“救世濟物”的修道信仰相通。道教宣稱:“積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憫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主張“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甚至認為“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由此可見,劍俠的替天行道與道教的救世濟物實是同質異構。
就修行理念、修行實踐而言,道與俠是融為一體的。道教貴生重氣,修心養命,形神俱煉,追求永恒,為此創造了多姿多彩的煉養方技。劍俠修煉“劍術”雖是意欲掌握救世濟民之術,但最終目的還是通過修煉超越生命,成為與世長存的劍仙。除了修行目的與道教一致外,劍俠修行的手段也完全照搬道教煉養方技,劍俠修行的過程就是修道成仙的過程,仙俠走在同一條路上。
二、超越自然的生命觀
在世界萬事萬物中,生命是最神秘、最重要的客觀存在。從本質上看,生命涵蓋了“形”與“神”兩個方面,探討“形”與“神”的關系就是劍俠小說生命觀的首要問題。“形”指的是生命的形體樣態,包括軀體的外在形狀和鑄成軀體的諸多器官、血液、筋脈等;“神”指的是軀體內部的指揮系統。“形”是物質性的客觀存在,而“神”則是精神活動;“形”與“神”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荀子·天論》云:“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這種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使軀體具有意識,生命得以維持。
按照大自然的規律,個體生命有一個從誕生趨向消亡的過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小說中劍俠修煉劍術的目的是超越生死,邁向永恒。《綠野仙蹤》的冷于冰在經歷了仕途失敗和師友病亡之后,對現世人生產生了幻滅感,“覺得人生世上,驅名逐利,毫無趣味”。第5回他對眾人說:“我如今四大皆空,看眼前的夫妻兒女,無非是水月鏡花,就是金珠田產,也都是電光泡影。總活到百歲,也脫不過死之一字。苦海汪洋,回頭是岸。”于是棄家訪道,立志成仙,最終在火龍真人的指導下成就仙業。《亦復如是·何配耀》中道人用劍術除去何配耀附身惡魔,并“索紙七張,每張上各畫一圈,其大者可徑尺,依次疊小,至如一粒粟。曰:‘先以大圈粘壁上,終日兀對,令心不出圈外,七日內心氣可足。若功力不懈,七圈皆用,效當自知。’何如法行之,至四十九日,心地忽然明澈,飄然而去,不知所終”。修煉“劍術”可以超凡入圣,得道成仙,有限的生命個體通過勤學苦修,堅持不懈,可以超越自然,長生久視,這是劍俠小說對生命形態的一種詮釋,反映了明清劍俠小說超越自然的生命觀。
在明清劍俠小說中,劍俠的成仙得道大都是形神一致的,即以肉體凡胎修成神仙。但也有形神分離的。《七劍十三俠》里草上飛焦大鵬在趙王莊陣亡,劍俠傀儡生在他陣亡之時,將他的靈魂度回山去煉魂七日,煉成仙道。之所以如此,書中寫道:“但因余七妖術厲害,凡胎肉骨,都不能進去破他,須要脫了凡胎,方能前進。”焦大鵬脫了凡胎后,跟隨玄貞子煉成劍術,“他本是無影無形的,因傀儡生把他魂靈煉過,要現形便與凡人無二”,因此不怕天羅地網、迷魂妖法,立下奇功。焦大鵬的成道過程是“形”“神”分離,兵解成仙。對此,小說有一番解釋:
你道怎的為兵解成仙?仙家有一派流傳,要度脫凡人成仙,必要此人死于刀兵,可脫凡胎,這就名為兵解。并非是旁門左道,不過是個外功。與玄貞子內功一道,略有分別。內功是凡胎肉骨,亦可飛升;外功必須脫了凡胎,方能成功。二者雖有內外之分,并無高低之別。
小說將棄尸成道與肉身成道都視為玄門正宗,沒有高低差別,只是修道方法不同而已。在小說中,“兵解”又稱“尸解”,有諸多描寫,如《遁窟讕言·飛劍將軍》中劍俠吳思演死于刀兵,“吳之親丁來收其尸,納之棺中,載至蘇州鄉間喚人舁于冢上,舉之覺甚輕,啟而視之,已無所有,惟留常日所用一劍而已”。《淞隱漫錄·廖劍仙》中劍俠廖蘅仙“將沒時,晨起見白猿至,嘆曰:‘我其死乎?’即服衣冠,危坐堂中,近矚之,則已體冰氣絕。及殮,有雙劍出自鼻中,直入霄漢而杳。人以為尸解云”。《淞隱漫錄·許玉林匕首》中劍俠許玉林與妻子雙雙死于匕首,親友為其辦喪事,“及舉槥入土,輕若無物,異而啟視之,并空棺也。人咸以為生與女皆劍俠者流,游戲人間,借尸解仙去”。《徐笠云》一篇對尸解的描述更為形象、具體。小說中一幼婦與僧通奸,并與之合謀殺死丈夫,事發后,按律當斬。“棄市之日,婦與僧神色揚揚自若,首雖隕地,身猶僵立不仆,腔中絕無滴血;群見有小人二自腔出,仿佛僧與婦狀,冉冉上升。生亦目睹,忿然曰:‘豈有修成劍術而為此壞法亂紀之事乎!’擲劍向空,二小人隨劍俱墮,身首異處,倏忽入地而沒,旋即尸仆血流”。幼婦與僧煉魔入道,企圖借兵解飛升,卻被徐笠云以劍術阻止。篇中幼婦與和尚的“神”被描繪成小人般的形體,脫離肉身,冉冉升空,這類無形的“神”凝聚成為有形的嬰兒的描寫,對后世劍俠小說影響極大。
明清劍俠小說對生命形態的描述有著濃郁的宗教文化色彩。生命中的“形”與“神”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各種宗教高度關注并反復闡述的問題。道教認為,生命以“道”為始基,因道化氣,以“氣”為生。《長生胎元神用經》云:“炁結為形,形是受炁之本宗,炁是形之根元”,“神以炁為母,母即以神為子,子因呼吸之炁而成形,故為母也。形炁既立,而后有神,神聚為子也”。“炁”同“氣”,在道教經典中常常出現。生命中的“形”與“神”都是因“氣”而生,成為生命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兩種要素。對于兩者的相輔相成,《西升經·神生章》這樣闡述:“蓋神去于形謂之死,而形非道不生,形資神以生故也。有生必先無離形,而形全者神全,神資形以成故也。形神之相須,猶有無之相為利用而不可偏廢。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所以道教主張形神俱煉,性命雙修,超越生死,肉身成仙。
佛教也關注生命中的“形”與“神”。佛教認為,世間的一切事物,包括各種物質現象、精神活動,都是因緣和合而生,都在遷流轉變之中,所有的一切都是變化無常,沒有常住不變、永恒靜止的事物。佛教稱為“諸行無常”。既然世間的一切都是變化無常的,那么就不存在能獨立自生、永恒不變的精神主宰,這就是“諸法無我”。佛教所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但佛教在否定“我”(精神主宰,或曰靈魂)的存在的同時,又肯定眾生“業力”的存在。“業力”是人們一生思維和行動的總和,是眾生生死流轉的動力。人的生命消亡了,但其“業力”不會消亡,而且還會引起相應的果報,決定著輪回轉生者的命運。這就是佛教宣揚的因果報應、六道輪回。“業力”既然不會隨著生命的結束而消失,并有一定的支配意志,從本質上說與靈魂就沒有差別。
道教與佛教對形神關系的認識有所不同,南北朝時期著名的道士陶弘景在《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中這樣論述:
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假令為仙者,以藥石煉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眾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云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
依據上文,對于形神,佛教是“非離非合”:人在輪回之中,精神與肉體必定結合,故曰“非離”;但佛教追求的解脫之道,是要超越輪回,擺脫肉體對精神的束縛,故曰“非合”。道教不同,它追求的是個體的長生不死,企圖維持形體的永存,必須形神兼備,舉形升虛,所謂“欲合則乘云駕龍”。但是修煉到一定程度,修道者就可以超越凡人的生存方式,精神可以自由地離開肉體,飛升上界,所謂“欲離則尸解化質”。“亦離亦合”的狀態,是指修道者可以對“形”“神”自我控制,自由分離,自由重合,從而達到沖破生存困境、超越生命極限的理想境地。
明清劍俠小說的生命觀雖有佛教的元素,但其主要內容還是反映出道教的生命哲學。尤其在《徐笠云》一篇中,幼婦與和尚離形尸解后,真神化作小人冉冉飛升,十分形象地描繪出道教生命演化理想。老子《道德經》云:“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受老子思想的啟發,道教采用逆向復歸的理論指導修煉實踐。道教第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解釋說:“吾身妙于嬰兒,天地妙于無極,道體妙于大樸。”道教將人生修煉目標比作嬰兒,并與天地、道體相提并論。對這種逆向復歸的終極目標,道教典籍提出了修煉程序:“萬物含三,三歸二,二歸一。知此道者,怡神守形,養形煉精,積精化氣,煉氣合神,煉神返虛,金丹乃成,只在先天地之一物耳。”“萬物含三”指萬物都包含精、氣、神。道教認為,人來到世上,先天稟賦的精氣神會逐步分離,慢慢死亡,所以必須將三者煉為一體,永不分離。“三歸二”指煉精化氣,“二歸一”是煉氣化神,直至煉神返虛。進入這個層面,精氣神凝結而成的元嬰之體就可以出現了。劍俠小說對生命演化進程的形象描述是荒誕的,但其致力于沖破生命有限的努力,則具有人類對生命超越的終極關懷的普遍意義。
三、仙凡混容的宇宙觀
明清劍俠小說營造的世界,可以說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平面世界。說它是平面世界,是因為劍俠的修煉、替天行道以及仙魔斗法等都是在同一個世界里展開;說它較為復雜,是因為在這同一層面里,還存在著相對的仙凡之別,如層次的高低、距離的遠近等。
在這個層面里,仙和凡是混容雜處在一起的。劍仙往往以平凡困苦的姿態,甚至是邋遢的面容出現于塵世。《獪園·青丘子》中劍俠青丘子,隱于武當山修道,其弟子王生上山尋師,“至則室廬如故,扃戶無人”,一日,“忽于荊南道上見先生溷跡丐者之中”。《池北偶談·女俠》中女劍俠隱身于偏僻的尼庵中,經常騎著黑驢行走于道上。《曠園雜志·瞽女琵琶》中女劍俠裝扮成盲女,“挾琵琶漫游遍宇內”。《耳食錄·王黃胡子》中某劍俠棲身于豪族公宅,與眾人吃飯時常坐末位,神態癃憊,衣冠了鳥。《耳食錄·何生》中女劍俠“雄服游戲人間”,衣冠襤褸,“以貧自晦,遂不為人識”。《聊齋志異·俠女》篇中俠女與其母親在市井中租住一陋室,母女倆靠針線活艱難度日。《李汧公窮邸遇俠客》中的劍俠隱身市井,行蹤詭秘,衣著隨便,“也不做甚生理,每日出去吃得爛醉方歸”。劍俠游戲塵世的目的是考察人心,賞善伐惡,度化有緣,積累功德。他們必須與凡人打成一片,置身于凡人的世界,如此,方能識透人心,分別善惡,了解世情,辨別真偽,真正做到替天行道。
劍俠雖然與凡人混雜在同一世界,但他們總是巧妙偽裝,不以真面目示人,一旦身份暴露,他們就飄然遠去,脫離凡人的視線,不知所終。劍俠隱身修道之處雖然與普通人處于同一層面,但卻有高低、險峻與平易之別,不是向道心切、毅力堅定的有緣人,是無法找到劍俠的存身住所的。《獪園·青丘子》中的王生,“好尋名山,博采方術,有高蹈遐舉之想”,所以只身踏入深山,尋覓仙跡。他“踐丹危,履翠險,或下或高,且數十里。隱映若有洞門在斷崖絕澗中,水流花開,風氣似春”,終于尋到神仙處所。經其祖王重陽的指點,他又坐船入楚,抵達江陵,尋至武當山下,“負囊獨上,緣磴躋攀”,幾經周折,方能得拜劍俠青丘子為師。《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云岡縱譚俠》中程元玉跟隨劍俠韋十一娘師徒前往其修道處云岡山頂,“過了兩個崗子,前見一山陡絕,四周并無聯屬,高峰插手云外……(三人)攀蘿附木,一路走上。到了陡絕處,韋與青霞共來扶掖,數步一歇。程元玉氣喘當不得,他兩個就如平地一般。程元玉抬頭看高處,恰似在云霧里,及到得高處,云霧又在下面了。約莫有十數里,方得石磴。磴有百來級,級盡方是平地”。韋十一娘師徒煉劍的山崖,十分陡峭,“下臨絕壑,窅不可測。試一俯,神魂飛蕩,毛發森豎,滿身生起寒栗子來”。《夜雨秋燈錄·郁線云》中女劍仙長公主選擇林木幽深的都梁山上修行,《剪燈余話·青城舞劍錄》中真無本、文固虛兩位劍俠在遠離塵世的青城山中煉劍。《淞濱瑣話·粉城公主》篇中,女劍俠粉城公主住地桃花奴,須飄洋過海,再翻越十余座山嶺方能到達。
劍俠修行為何一定要選擇高山峻嶺、絕壁危崖呢?這是因為高山危崖人跡罕至,杜絕喧囂,浩瀚深邃,氣象萬千,參天的古樹,飛瀉的山泉,幽深的洞穴,奇異的叢巖,其聲色光影閃動著生命的靈性,高聳險峻更匯集了天地日月精華。《抱樸子·明本》稱:中世以來,求仙訪道者皆飄然絕跡幽隱,“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為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凈也”。于是,遠離紅塵而又孕育著無限生機意趣的大自然就成了劍俠修煉劍術、打通天界與人間的中轉站。
劍俠入深山修煉,除了脫塵離俗、親近自然之外,在深層意義上,還與中國上古社會普遍流傳的入山尋仙、上山升天的思維認識有關。《淮南子》、《拾遺記》等書對此有較為具體的描述:
昆侖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淮南子·墜形訓》
昆侖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云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像。四面有風,群仙常駕龍乘鶴游戲其間。
《拾遺記》
在古人的思維模式中,山與天是最為接近的,登山而上便可入天界,甚至可成神仙。這種山天相通的思維模式的產生,“蓋因高山云霧繚繞,山天相接,似隱似現,極易令人產生飄然于天國仙境的聯想與幻想之故”。
劍俠的修行處所盡管偏僻遙遠、陡峭險峻,普通人或遭逢意外,亂走誤撞(如《粉城公主》中的任生),或一心向道,堅定尋找(如《青丘子》中的王生),或經人指點,相隨前往(如《劍俠》中尋找失金的官吏),或主人相邀,扶助隨行(如《韋十一娘》中的程元玉),總能步入劍俠的生活領地。這是因為劍俠與凡人的生活空間處在同一個層面,兩者雖然有地勢高低、難易之不同,環境喧鬧與寂靜的差別,卻處在同一片天地間。
在明清劍俠小說里,沒有天庭和地獄的描寫,所有的故事都在凡人的世界里展開。《何生》篇,寫劍俠了奴姊妹本是天界紫蘭宮的捧劍使者,因舞劍誤傷守宮之鶴,“故謫墮人間,使主游俠之事”。謫墮期滿,兩女重返天庭,與何生從此“殆無相見之期矣”。這篇小說提及天庭,但并沒展開描寫。小說中,劍俠是在天界中犯有過錯的神仙降謫人間,一旦期滿便返回天庭,不再干預塵事,與凡人也不能再有往來。天界和人世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至于地獄的描述,在明清劍俠小說中更是難覓蹤跡了。
明清劍俠小說中天庭和地獄的缺失,表明劍俠的活動天地是一個單層面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仙凡之間雖有距離和高低的阻隔,但彼此有較多的交往與溝通,劍俠甚至易容變貌混跡于凡人社會。這種單層面空間的營構,使得劍俠的活動范圍被局限在塵世中,其命運和活動內容都與蕓蕓眾生緊密關聯,因此格外關注這個世間的動亂和災難,自覺地承擔起替天行道、誅惡降魔的責任。這種單層面空間的設置,使得劍俠小說與神魔小說之間有了相對清晰的分野。
四、自相矛盾的情愛觀
愛情,是人類最美好的情感,也是文學作品中歷久彌新的題材,但在古代劍俠小說中卻舉步維艱。唐宋時期的劍俠小說幾乎沒有男女情感內容的描寫,偶爾涉及,也是或憑借神術,成全別人的愛情;或言及婚姻,卻無愛情可言;或借婚姻為掩護,事成之后棄之如敝屣,勇于“斷愛”,毫不留情,基本上沒有愛情火花的閃爍。之所以如此,一是出于宗教的因素,所謂“恩愛害道,譬如毒藥”。二是源自敘事策略。即用凡人的視角來描述劍俠,刻意不觸及其生活方式,尤其是情感世界,以增加劍俠的神秘性。
至清代,這種“俠不言情”的創作格局被打破,劍俠擺脫了“無情”的生活狀態,開始在愛情世界里漫游。以劍結緣是清代文言劍俠小說的言情模式。在具體演述時分成兩種套路:一是雌雄雙劍配姻緣。《許玉林匕首》中許琳和妻子皆有奇遇,各得到一把匕首,兩刀長短一樣,許琳的刀文凸而顯出,銘陽文,其妻之刀文凹而深入,銘陰文,兩人因此結為夫妻。《虞初廣志·李涼州》篇敘李涼州得遇奇人,獲贈寶劍,此劍“出世五百年,尚未得偶”,后入滇中,遇一戎裝女郎,家中也有一把寶劍,兩劍“一雌一雄,毫發俱肖,合之吻合無間”,兩人遂成佳偶。二是男女比劍成連理。《遁窟讕言·老僧》中衛文莊“體魄瑰偉,豐神清拔”,精通劍術,聞西安有奇女子仇慕娘比武招親,欣然前往。比武場上,兩情相悅,結為伉儷。《淞隱漫錄·女俠》篇敘劍俠潘叔明性情豪邁,精通劍術,匹馬裹糧,游走四方,在山東道上遇綠林豪杰,潘叔明與女劍俠程楞仙飛劍相斗,各自傾心,英雄美女,喜結良緣。《淞隱漫錄·倩云》中秦雨衫夜入盜窟遭遇倩云,比劍后拜倩云為師,終至鸞鳳和鳴。在男女比劍的敘述中,女子的劍術總是高于男子,對愛情的態度也較男方主動,這種柔弱與剛強的對比描寫,很好地襯托了女俠的颯爽英姿、似水柔情。
以劍結緣是劍俠之間的言情模式,而劍俠與平常人之間的相愛更注重人的品性、才情。《何生》與《廣寒宮掃花女》中的女俠原是仙女下凡,男服裝扮游戲人間,衣衫襤褸,無人相顧,而何生與鄭生卻送錢送物,關懷體貼,從而使仙女頓生眷戀之情,不但在危急關頭出手解圍,而且主動示愛。正如《廣寒宮掃花女》中女俠所言:“余雄服游戲塵寰,物色奇士,殊無知我者。君乃與我金,贈我衣。俠之所在,即情之所鐘也。”《淞隱漫錄·姚云纖》寫女劍俠姚云纖與孫公子談論詩詞曲賦、地理風情及音樂,且聯詩斗酒,賞花看月,相見恨晚。《虞初廣志·柳珊》中女劍俠柳珊,從小父母雙亡,賣身撫署,撫軍欲將她嫁給幕僚李生,李生因未有母命不從,撫軍以勢相壓,李生直面頂撞。柳珊見李生據理力爭,很有骨氣,怦然心動,在李生遭劫難時盡殲盜匪,并委身下嫁。《淞濱瑣話·劍氣珠光傳》描寫俠女白如虹與才子隨照乘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白如虹隨父出門經商,隨生誓不他娶,照料白母,尋訪如虹,如虹也絕不別嫁,等待隨生。兩人久經磨難,愛心始終如一,終于苦盡甘來,別后重逢,成就姻緣。在此類言情模式中,劍俠多為女性,喜歡女扮男裝,男方都是普通人,有才情,有骨氣,有俠心,最終贏得俠女的愛情。
清代劍俠小說第一次為讀者營造了劍俠的情愛大廈,她給原本過于虛幻、神秘的劍俠世界增添了生機和詩意,尤其是女劍俠的情愛追求和情感流露,更是如同美妙動人的樂曲,在讀者心中產生強烈的震顫。女俠溫文爾雅,儀態萬方,豪爽不失嫵媚,主動伴以矜持,愛意纏綿而又英姿颯爽,真可謂:紅衣劍膽芳魂在,柔情俠骨動人心。
如果我們整體審視清代劍俠小說有關情愛內容的話,那么就會發現這一時期小說的創作者對待愛情的態度是矛盾的,并不全是贊美,也有貶低、排斥。《廖劍仙》敘廖蘅仙跟隨一程姓老翁學習“劍術”,道術將成時,有一美女前來擾亂清修,“廖心幾動,急自遏制,念此淫娃壞我大道,盍不殺卻?忽覺鼻中奇癢,一道白光突出,美人已杳。啟目視之,座下死一九尾狐”。老翁對廖蘅仙不為情惑的行為贊不絕口:“子不犯色戒,真俠士也。再修三百年,可成劍仙。”《澆愁集·俠女登仙》中女劍俠張青奴對馮生說:“實告君,我劍仙張青奴也。向從妙手空空兒學技,見玉面郎君美,偶動凡念,師怒,責罰塵世立功德三十萬。”這兩篇小說都將“情愛”視為修道的障礙。
有些作品試圖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徐笠云》篇,徐笠云與劍仙呂端之女互相愛慕,而此女“惟因劍術已成,將登仙籍,不愿再履塵世”,就換呂端的侄女莼香前來與徐笠云“以了前緣”,這是用偷梁換柱的方法來化解“情”與“道”的對立。而《淞隱漫錄·劍仙聶碧云》中的聶碧云“雖與士人為伉儷,而食宿自別,察之,似絕無所染者,群疑為非常人”。小說描述的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戀愛,試圖以“靈”“肉”分離的辦法來調和“情”與“道”的內在沖突。此種柏拉圖式的戀愛方式為民國年間的小說家承襲,創出所謂有名無實、違反人性的 “合籍雙修”的劍俠夫妻模式。
情欲與修道相沖突觀念由來已久。在明清劍俠小說中,“情欲”常被用來作為考驗修道者是否心誠的手段。明胡汝嘉《韋十一娘傳》中,韋十一娘拜趙道姑學藝,師誡:不得飲酒、淫欲。半夜,“有男子逾垣而入,貌絕美 ”,以武力逼其犯淫戒,韋十一娘說:“死即死耳,吾志不可奪也。”男子收劍而笑道:“可以知子之心矣。”原來男子是道姑變化,來考察韋十一娘是否心誠志堅。情欲與修道的水火不容,源自中國人傳統觀念中對元陽的迷信,認為守住元陽,保護真陰,勤修煉養,就能得道飛升;而泄了元陽,只能歷經劫難,轉世重修。所以,在劍俠小說中童男童女在修道時總是事半功倍。既然情愛是修道的障礙,劍俠的生存狀態就只能是無情。另一方面,劍俠對情欲的排斥,還根源于“萬惡淫為首”的封建禮教道德觀。在中國古代社會,男女關系要符合禮,“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責任重大,且始終與道德密切相關。至于男女相悅的“情”則被視為放縱的表現,與“禮”是不相容的,因此情欲必須克制,甚至滅絕。于是,在劍俠小說中,正直的劍俠不僅不犯色戒,而且對淫蕩之徒總是深惡痛絕,必欲剿滅而后快。
除了上述修行觀、生命觀、宇宙觀和情愛觀四個方面以外,明清劍俠小說還有著濃厚的宿命意識,在價值觀念上,表現出以仁為本,善惡分明,重視倫理等道德傾向,以致在“劍術”描寫中也有著正邪之分。總的來說,明清劍俠小說的文化觀是豐富多彩的,體現出多元化的格局,它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元素,而道教文化起著主導作用。在具體的文本表述中,這些文化形態通過小說描寫的人物和情節生動形象地呈現出來,從而彰顯了這一文學品類獨特的藝術魅力。
注:
① 劍俠小說是武俠小說重要的分支,“劍術”與俠義構成其基本的敘事內容,二者缺一不可。此類小說的產生,有其獨特的文化淵源,藝術表現上,也有其鮮明的個性特征。關于劍俠小說的界定范圍與演變趨勢,請參閱拙文《古代小說中劍俠形象的歷史與文化淵源》(《文學遺產》2009年第3期)、《明清長篇劍俠小說的演變及文化特征》(《文學遺產》2010年第3期)。
②[清]長白浩歌子《螢窗異草》三編卷2,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頁。
③④ [清]海上劍癡《仙俠五花劍》(與《宋太祖三下南唐》合刊),華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322頁。
⑥[清]呂熊《女仙外史》,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頁。
⑦《道藏》第22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383頁。
⑧《道藏》第4冊,第3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