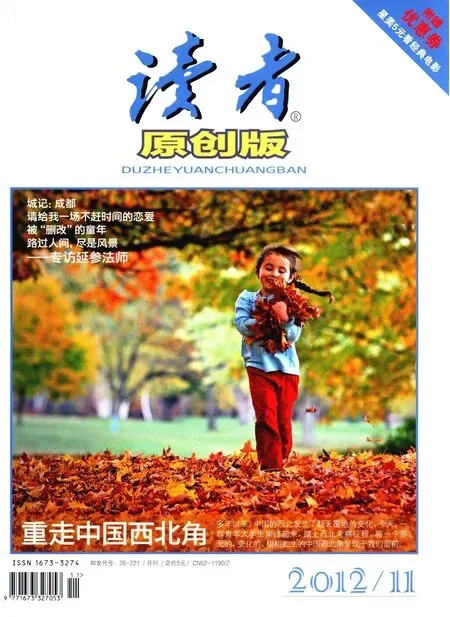家在黃土高坡
文 _ 張笑陽
車開始爬山。爬上了一座山,抬頭又是一座山;繞過了一道彎,轉眼又是一道彎,車里的我們像篩石子一樣被顛來甩去。這里本沒有路,走的車多了,也便成了“路”。走過的車當然不是寶馬、奧迪,它們身價太高、底盤太低,而多是拖拉機、摩托車、貨車,當然偶爾也有我們這些來“訪貧問苦”的越野車。我慶幸這里前一天下了場雨,路上還稍有泥濘,否則我們就會被車揚起的黃土包圍了。是的,平日的路上可能是半尺厚的黃土。這里是中國西北角的一角,曾經的革命根據地的一塊,陜甘交界的隴東一隅,據說是黃土高原土層最厚的一片黃土。
這里的景致,怎么說呢?滿眼連綿不絕的黃土塬,很……厚重。聽聽秦腔里吼的那些片段吧,就是那樣的感覺。只有偶爾在山洼洼里突然出現的一樹杏花、一戶人家,能讓你的心里倏忽婉約一下。
山上“越野”快一小時后,我們到達目的地—一個居住比較分散的小村落。在中華田園犬叫聲的歡迎下,我們深入數戶人家的窯洞,親切探望了常年駐守在這里的“386199部隊”,送上慰問品,與他們促膝交談,就糧食生產、飼養牲畜、修梯田、用電、吃水、治病、打工、小額貸款等問題進行了交流,同時看望了他們飼養的驢、羊、雞、豬、土蜂,提了提騾子馱著去山下拉水的輪胎改制的橡膠桶,揭了揭鍋蓋,并與一家窯洞墻上的謝霆鋒、許晴進行了眼神交流。情形和電視新聞里你常看到的差不多,不過可真沒有挨個去問“你幸福嗎”。但有戶人家的一個六七歲的小孩,我們卻無法與他眼神交流—一場腦膜炎后他失明了,基本不能視物。臉上有笑容,眼中無神采,等待爸爸在外打工掙錢后到西安的大醫院去治療。他家窯洞的墻壁上掛著一個“山寨”芭比娃娃,也許是爸爸帶回來的,腿還是那么長,睫毛還是那么卷,眼睛還是那么亮……
從一戶兒子在縣城上中學、丈夫因病喪失勞動力、全靠妻子一人務農、前年剛用嫁女兒的彩禮錢箍起新窯洞的人家里出來,陣陣涼風從塬上吹過。望著遠處的山梁,二十多年前的旋律就在頭腦中襲來:“我家住在黃土高坡,日頭從坡上走過。照著我的窯洞,曬著我的胳膊,還有我的牛跟著我。不管過去了多少歲月,祖祖輩輩留下我。留下我一望無際唱著歌,還有身邊這條黃河。”能留下嗎?當留守的婦孺期盼著城里務工的丈夫、兒女從黃土高坡上接走他們后,也許只有幾位老人會堅守在這里,最終與相伴一輩子的黃土融為一體。這樣的村莊將漸漸消失,和一輩輩人一樣,留給后代的只是記憶和傳說。
“該走了!”陪同的鄉干部喊道,“快下雨了,一下雨路爛了山都下不去了!”走吧。離窯洞一兩百米外的山梁上,中石油的“磕頭機”也在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工作著,不過它刨出來的可是很值錢的石油。這些農人的祖輩當初選中這塊“寶地”定居時,怎么也不會知道一兩百米厚的黃土下竟然有“黑金”。今天的后輩倒是知道了,而且“磕頭機”天天就在眼前和他們一起勞作著,可似乎和他們也沒有太大的關系,距離也不僅僅是兩個山梁。
山高路遠,還是唱起歌兒趕路吧:“我家住在黃土高坡 ,大風從坡上刮過,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我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