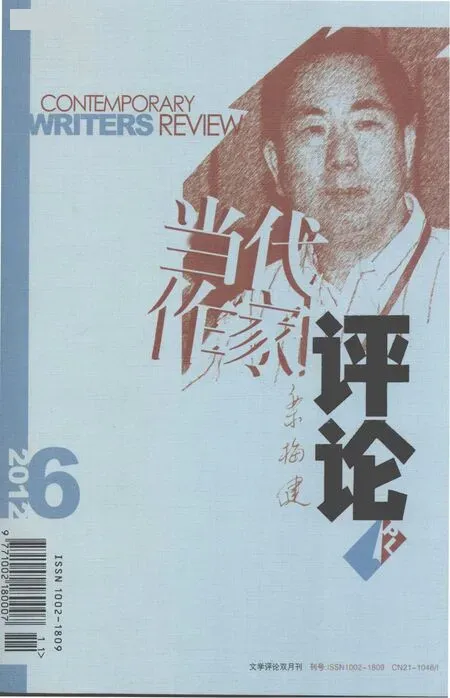“十七年文學”:紅線黑線有異,實行專政則一——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文藝界的“撥亂反正”
王彬彬
一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印了《文藝情況匯報》第一一六號,其中,有《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一文,介紹了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抓評彈的長編新書目建設和培養農村故事員的做法”。十二月十二日,毛澤東看了介紹上海的這篇文章,決定將此件批給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和第二書記劉仁,并寫了一段批語。批語很快以《關于文學藝術的批示》為題公開發表,全文如下: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是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這是毛澤東“文革”前關于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中的第一個。這個批示,對中共建政十幾年來的文學藝術是基本否定的。在否定這十幾年的文學藝術時,也說了這樣一句話,“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很清楚,在整個批示中,這只是一句用來緩沖語氣的話。“收效甚微”、“死人統治”、“問題也不少”、“問題就更大了”、“還是大問題”、“咄咄怪事”等一個接一個的判斷、反詰,十分明確地顯示了對這十幾年的文學藝術總體上的不滿,那句用來緩沖語氣的話,絲毫不能改變毛澤東對十幾年來的文學藝術的整體否定。但是,這句實際上是可有可無的話,在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卻被人反復提及。
這個批示當然是打向文藝界的一記悶棍。文藝界的領導自然惶恐不安。文化部黨組立即對近年工作進行了反思。一九六四年三月下旬,中宣部決定在全國文聯和各協會全體干部中進行“整風”。五月八日,中宣部寫出了《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報告”還是草稿,尚未定稿,江青便將其送到毛澤東手上。六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報告”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這就是毛澤東“文革”前關于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中的第二個。①關于“兩個批示”的出籠,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第1220-1222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最近幾年”下面的重點號,為毛澤東本人親加。較之半年前作出的第一個批示,第二個批示態度更嚴肅了,語氣更嚴厲了,遣詞造句更見斟酌挑揀,對十五年來的文學藝術的否定也更為明確。政治上的上綱上線,使得第二個批示寒氣逼人。在“最近幾年”下面加上重點號,是在強調文藝界“變修”的狀況愈演愈烈。用兩個括弧,為自己留一點余地,也是經過考慮的。刊物只有“少數幾個好的”,但還是“據說”,有可能一個“好的”也沒有。但“不是一切人”都壞,卻是一個很肯定的判斷:當然要保住一些人,要救出一些人,不然,下面的整風、下面的革命,由誰來發動、帶領呢?
一九六六年二月上旬,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集軍隊文藝方面的領導進行所謂“座談”。會后,炮制出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陳晉的《文人毛澤東》一書,對這《紀要》的形成過程有詳細的敘述。江青在上海炮制《紀要》時,毛澤東正駐蹕杭州。“毛澤東曾三次對‘紀要’作了重要修改。”二月二十八日,江青將《紀要》鉛印稿送毛澤東審閱,數千字的《紀要》,毛澤東“修改有十一處”,特別重要的是,把標題改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就把林彪綁在了戰車上。除了改,毛澤東還單獨加寫了這樣一段:“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占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斗爭這個決定后,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斗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修改《紀要》。三月十四日,江青把第二稿寄給毛澤東,毛澤東作了第二次修改。這一次,又改動了“十幾處”。第二稿退還江青后,江青又組織人弄出了第三稿,并再送毛澤東。毛澤東又作了第三次修改。這一次,“主要有四處改動”。三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把第三次修改過的稿子退江青。這第三稿才算是定稿。②陳晉:《文人毛澤東》,第595-59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毫無疑問,毛澤東對這個《紀要》是極其重視的,對《紀要》表達的觀點,是完全認同的。毛澤東是《紀要》的真正策劃者。
二
這個《紀要》,最核心的內容,是對中共建政十七年來文學藝術的根本否定。《紀要》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即認為十七年來,在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具體表現為“黑八論”:“寫真實”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現實主義深化”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時代精神匯合”論、“離經叛道”論、反“火藥味”論。
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現了許多頗具中國特色的政治用語,“揭批”就是其中之一。所謂“揭批”,應該是揭露與批判的合稱。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被捕,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揭批“四人幫”的高潮也隨之興起。不過,由于“兩個凡是”的制約,這一時期對“四人幫”的揭批,其實舉步維艱。十多年里,江青等人的言行,與毛澤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只要是毛澤東說過的話、認可過的事,便都揭不得、批不得。揭批的空間就很小了。在文藝界,對“四人幫”的揭批,從“《創業》事件”開其端。這一方面因為此次事件發生未久,另一方面也因為在“《創業》事件”中,毛澤東沒有站在“四人幫”一邊。張天民編劇、于彥夫導演的電影《創業》,表現的是大慶油田會戰中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世界觀斗爭,也歌頌了艱苦奮斗的精神。一九七五年初,《創業》在部分城市上映,江青認為影片有嚴重問題,下達了封殺令,并宣稱要追查背景。緊接著,江青策劃的批判文章,給《創業》羅列了十條罪狀。編劇張天民給毛澤東寫信申訴。十來年了,文藝天地里,就幾個“樣板戲”唱個不停,連毛澤東也覺得太單調乏味了。這回,他決定支持張天民一下。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毛澤東在張天民的信上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江青說這是“鄧小平逼著主席批的”。張春橋則說:“主席說無大錯,那還有中錯和小錯嘛!”在九月間的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江青大罵張天民“謊報軍情”,威逼張再給毛澤東寫信認錯。①見潘旭瀾主編《新中國文學辭典》,第469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四人幫”垮臺時,此事剛剛過去,毛澤東又可說委婉地批評了江青們。從這件事上揭批“四人幫”,既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又在政治上十分安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的《解放軍報》,發表了杜書瀛、楊志杰、朱兵三人共同署名的長文《圍繞電影〈創業〉展開的一場嚴重斗爭》。文章這樣開頭:“從去年起,圍繞著彩色故事片《創業》展開了一場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②杜書瀛、楊志杰、朱兵:《圍繞電影〈創業〉展開的一場嚴重斗爭》,《解放軍報》1976年11月5日。文章從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高度,細致地揭露了“四人幫”對《創業》的企圖扼殺,處處強調“四人幫”與“毛主席指示”的“對抗”。對抗“毛主席”、反對“毛主席”,被認為是“四人幫”一貫的行徑、最大的罪孽。這篇文章長達萬余字,而發表時距“四人幫”被抓捕不到一個月,應該是文藝界最早揭批“四人幫”的有分量的長文了。
文藝界從“十七年”走過來的一些人,尤其是在那時期曾或長或短地擔任文藝界領導職務者,對“文藝黑線專政”論自然有著腹誹。但是,這個“文藝黑線專政”論與毛澤東的關系太密切,在“四人幫”垮臺后一年多的時間里,仍無人敢對之表示質疑。是在教育界的示范下,文藝界才大起膽子,在對“十七年文藝”的評價上“撥亂反正”的。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會,開了三個半月。這樣的馬拉松會議,在那時期并不罕見。這次會議的“成果”,是炮制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紀要》對“文革”前十七年間的教育工作做了兩個基本估計:一、十七年間,在教育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二、十七年間,大多數教師和培養的學生,“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毛澤東圈閱了這個《紀要》,認可了這種估計。這“兩個估計”,自然也成了壓在教育界頭上的兩座大山。然而,由于《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經過毛澤東的御批,“教育戰線”對“四人幫”的揭批,也遲遲不敢碰這兩個“估計”。一九七七年,鄧小平最后一次落而后起,對教育界的“撥亂反正”十分重視,積極策劃恢復高考招生制度。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此次講話后以“關于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鄧小平的講話,一開始就對“兩個估計”提出質疑:“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鄧小平進而肯定了“十七年”中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雖然有鄧小平“身先士卒”,教育部還是不敢貿然“跟進”。究其原因,在于鄧小平那時還似乎立足未穩,還有些前程未卜,教育部的頭兒怕跟著鄧小平“犯錯誤”。在鄧小平的強力支持、催促下,教育部才敢于明確推翻“兩個估計”。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組”的文章《教育戰線上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文章強調:十七年間,“教育戰線”上占“主導”地位的是“紅線”,而不是所謂的“黑線專政”;至于教育界的知識分子,是“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對象”。①教育部大批判組:《教育戰線上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8日。
教育界對“兩個估計”的否定,給了有關方面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勇氣。兩天后的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編輯部邀請文藝界人士座談。座談會的目的是推翻“文藝黑線專政”論,為“十七年文學”從政治上、藝術上平反,恢復名譽。茅盾、劉白羽、張光年、賀敬之、冰心、呂驥、蔡若虹、李季、馮牧等人參加了座談。參加會議者,回去后都寫了文章。此后一段時間,《人民日報》陸續發表了這些文章。茅盾、劉白羽的文章率先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報》發表。茅盾文章為《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神枷鎖》,劉白羽文章為《從“文藝黑線專政”到陰謀文藝》。這是最早的兩篇明確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文章。十一月二十七日,蔡若虹的《揭穿“文藝黑線專政”論的陰謀》和馮牧的《炮制“黑線專政”論是為了實行法西斯專政》兩文又在《人民日報》同時發表;十一月三十日,李季的文章《毛主席的革命文藝隊伍是一支好隊伍——斥“四人幫”對文藝隊伍的誹謗和誣蔑》在《人民日報》發表;十二月二日,賀敬之的長文《必須徹底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在《人民日報》發表;十二月四日,冰心的文章《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流毒不可低估》在《人民日報》發表;十二月五日,呂驥的文章《“黑線專政”論是為篡黨奪權制造輿論》在《人民日報》發表;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張光年的長文《駁“文藝黑線專政”論——從所謂“文藝黑線”的“黑八論”談起》和李春光的短文《斬草必須除根》。
三
在《人民日報》的帶動下,其他報刊也行動起來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七日,在《人民日報》發表張光年和李春光文章的同時,《光明日報》發表了曹禺的文章《不容抹煞的十七年》,同一天,上海的《文匯報》也發表了秦怡的文章《徹底推倒“文藝黑線專政”論》。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一日,《光明日報》又發表了陶鈍的長文《揭批“四人幫”摧殘曲藝的罪行——批“文藝黑線專政”論》。報紙之外,相關刊物這一時期也發表了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文章。一九七七年第三期的《上海文藝》(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出版)發表了羅蓀的文章《“文藝黑線專政”論必須批判》;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的《解放軍文藝》發表魏巍的文章《騙局·陰謀·鐐銬》。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文學》編輯部在北京召開大型座談會,在北京的文學界人士一百余人參加了座談。編輯部負責人張光年主持了會議。座談會的主題是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同時也研討如何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會議期間,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為《人民文學》題詞:“堅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而奮斗”。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文化部部長黃鎮、全國文聯副主席茅盾都到會講話。全國文聯主席郭沫若以書面的方式參加了座談。會后,署名“文化部批判組”的萬字長文《一場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斗爭——批判“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在《紅旗》雜志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發表,這是一篇特別有分量的文章。而一九七八年二月六日的《人民日報》則發表了署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評論組”的萬字長文《“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出籠和破滅》。
為了“批倒批臭”這“文藝黑線專政”論,當時的文藝界是花了大力氣的。茅盾的文章,這樣開頭:“人民日報編輯部這個座談會非常及時,非常必要。教育界的同志們已經開過這樣的座談會,憤怒聲討‘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我們也迫切需要揭發和批判‘四人幫’炮制‘文藝黑線專政’論的罪惡陰謀,徹底批判‘四人幫’在文藝理論上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本質,肅清其流毒。”①茅盾:《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神枷鎖》,《人民日報》1977年11月25日。在否定、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前,先強調教育界已經推倒了“兩個估計”,這種做法為后來的不少文章所效仿。這說明,沒有教育界率先否定“兩個估計”,文藝界是不敢去碰這欽定的“黑線專政”論的。既然教育界可以推翻“兩個估計”,文藝界就也可以否定“黑線專政”論——這是可以公開、明確地表達的意見。援教育界之例,更有著不便公開、明確地表達的意思:“兩個估計”也是經“毛主席”圈閱的,教育界能推翻它,那么,同樣經過“毛主席”認可的“黑線專政”論,文藝界就也能否定它了。茅盾接著說:“‘四人幫’為了他們篡黨奪權的需要,大肆污蔑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文藝戰線,稱之為‘黑線專政’,這是狂妄地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在十七年中的主導地位,狂妄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藝領域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②茅盾:《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神枷鎖》,《人民日報》1977年11月25日。把“毛主席”與“四人幫”嚴格區分開來;把“毛主席”從“四人幫”的軀體上切割下來并讓其成為“四人幫”的對立面,把“文藝黑線專政”論說成是對“毛主席”的“狂妄反對”,是茅盾的話語策略,此后的揭批文章,都運用和光大了這種策略。強調在“十七年”間“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占“主導地位”,這一口徑是對鄧小平的套用,也為此后的揭批文章所襲用。所謂占“主導地位”,直白地說,就是在“十七年”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處于“專政”地位,是“紅線專政”而不是“黑線專政”。一般的文章,在強調“十七年”里是“紅線”在“主導”時,避免了用“專政”一詞,但也有人干脆棄“主導”而用“專政”,賀敬之就是如此:“特別重要的是,十七年的文藝領導權始終是牢牢掌握在毛主席和黨中央手里的。是無產階級在專資產階級的政。十七年文藝戰線的所有斗爭,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的。這是最根本的事實。‘四人幫’歪曲事實,顛倒敵我,把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說成是資產階級的領導權,把我們黨對文藝的領導全盤否定,這就是從根本上否定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③賀敬之:《必須徹底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人民日報》1977年12月2日。在“十七年”里,文藝界是無產階級在“專”資產階級的“政”,是一條“紅線”在“專”一條“黑線”的“政”,這其實是當時各地揭批文章共同強調的。
讓毛澤東與“文藝黑線專政”論脫鉤,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但又是必須做到的事。沒有這種脫鉤,揭批在當時就無法展開,“黑線專政”論就無法否定,“十七年文藝”就無法擺脫污名。毛澤東深度介入了江青炮制的《紀要》,毛澤東完全贊成“文藝黑線專政”的說法,這是文藝界盡人皆知的。但是,所有的揭批文章,都必須絕對不提及此事,都必須認定毛澤東與《紀要》、與“黑線專政”論沒有任何關系。署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評論組”的長文《“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出籠和破滅》,一開始就這樣定調:“江青勾結林彪炮制的‘文藝黑線專政’論,就是這樣一個假左真右的典型”。“江青勾結林彪”,所以產生了《紀要》。賬,只能算在江青、林彪頭上。這篇文章,對《紀要》的出籠經過,說得很詳細,甚至敘述了一些細節,甚至有這樣的深層揭露:“隨后,江青把她的那個親信(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四人幫’搞‘三箭齊發’時,江青安插在部隊搞‘放火燒荒’的那個‘縱火犯’)從北京再次叫到上海。江青一個,陳伯達一個,張春橋一個,加上那個親信,就是這么幾個志同道合的‘老伙計’,又聚在上海的陰暗角落,精心炮制出那個丑化無產階級專政的‘文藝黑線專政’論。”①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評論組:《“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出籠和破滅》,《人民日報》1978年2月6日。(括號中話為原文所有——引者按)這說明,對《紀要》出籠的過程,文藝界當時就知道得非常清楚,毛澤東與《紀要》的關系,自然也為人知曉。絕不提毛澤東與“文藝黑線專政”論的關系,并不意味著不提毛澤東這尊神。相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出籠和破滅》,時時請出毛澤東與“四人幫”對照,處處借助毛澤東揭批江青。在揭批的過程中,堅定明確地把毛澤東作為“四人幫”的對立面,堅定明確地把“黑線專政”論定位為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是所有文章共同的基調。
四
那時候,在毛澤東與《紀要》之間進行切割,還不算很難的事。毛澤東與《紀要》的關系,毛澤東對《紀要》三次精心修改,當時并未向社會公布,并不曾見諸任何文字,在作切割時,裝作不知即可。真正困難的,是如何面對毛澤東“文革”前針對文藝界的“兩個批示”。人們心里都清楚,“兩個批示”其實已經對“十七年文藝”基本否定了,“文藝黑線專政”的指控,在“兩個批示”中已經表達了,江青們炮制的《紀要》,不過是把“兩個批示”的觀點細致化、系統化而已。“兩個批示”影響巨大、無人不曉。要推倒“文藝黑線專政”論卻又避“兩個批示”而不談,是不可能的。要為“十七年文藝”恢復名譽卻又不理順“兩個批示”與“十七年文藝”的關系,是不能自圓其說的。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當文藝界著手推翻“黑線專政”論時,“兩個批示”是橫亙在眼前的兩大障礙物。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說,比起教育界推翻“兩個估計”來,文藝界推翻“黑線專政”論要艱難得多。
政治往往就是修辭的游戲。署名“文化部批判組”的長文《一場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斗爭——批判“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這樣強調了“四人幫”對“兩個批示”的歪曲篡改:“‘四人幫’特別是集中歪曲、篡改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對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他們不僅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對兩個批示妄加解釋,而且公然斷章取義,為其制造‘文藝黑線專政’論尋找‘根據’。一九六六年七月,江青伙同陳伯達,借重新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機,在編者按中引用批示時,故意把‘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這句話全部砍掉;公然把批示中的‘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改成了‘文藝界’。在以后的許多文章、講話中,他們多次照此篡改,并且作了許多歪曲解釋,造成了極大的混亂。”①文化部批判組:《一場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斗爭——批判“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紅旗》1978年第1期。如果以摳字眼的方式,認定“四人幫”歪曲篡改“兩個批示”,也能說得過去。但那句被“砍掉”的話,實在只是一句用來緩和語氣的話,而把“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改成“文藝界”,也不算十分離譜。但這畢竟是一種“把柄”。許多揭批文章,都以此為證,說明“四人幫”對“兩個批示”的歪曲。
僅僅以個別字句為證,說明“四人幫”對“兩個批示”的歪曲,還不能對“兩個批示”和“黑線專政”論進行有效的切割。于是,《一場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斗爭——批判‘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又作了這樣的強調:要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才能理解“兩個批示”的精神實質。所謂當時的“歷史條件”,就是“三年困難時期”,“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對文藝界進行了嚴重干擾破壞,使得文藝界的確出現了一些“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毒草”。而毛澤東正是針對此種現象而作出了“兩個批示”。在這特定時期,“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與“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文藝界有過一場較量,結果,當然是“毛主席”戰勝了“劉少奇”。許多揭批文章,都這樣強調“兩個批示”是在特定時期、特定語境中對文藝界的否定。把整個“十七年文藝”的歷史,解釋成“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歷史,更是許多揭批文章共同的套路。例如,馮牧的文章寫道:“一個十分清楚確定、無可辯駁的事實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潮確實對文藝戰線有過破壞和侵襲,而且在六十年代的某些部門(如像毛主席批評過的戲劇部門)表現得也的確很嚴重,但是,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文藝戰線卻始終沒有占過主導地位,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藝黑線專政’。”②馮牧:《炮制“黑線專政”論是為了實行法西斯專政》,《人民日報》1977年11月27日。為“十七年文藝”平反,不能把“十七年”說成是風平浪靜,要強調這期間是貫穿著激烈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但是,是“無產階級”戰勝了“資產階級”,是“正確路線”對“錯誤路線”實施了“專政”。羅蓀的文章,列舉了“十七年來文藝戰線上”存在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一九五一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對《紅樓夢》研究中“資產階級傾向”的批判;一九五五年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一九五七年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斗爭……羅蓀強調:“在這歷次的斗爭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始終起著主導作用,從而取得斗爭的勝利”。③羅蓀:《“文藝黑線專政”論必須批判》,《上海文藝》1977年第3期。
江青們認為“十七年”文藝界是“黑線專政”。“黑線”的具體內容,則是“黑八論”。在推翻這“黑線專政”論的過程中,如何處置這“黑八論”,也是一個問題。正面肯定這八種觀點,為它們去污名化,是一種方式。但在當時的情形下,這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只有在承認這“八論”的確很“黑”的前提下,強調這“黑八論”在“十七年”里是受到嚴厲批判的,是并沒有成為氣候的,是談不上對文藝界進行“專政”的。張光年的文章,主要就是論述“黑八論”在“十七年”里怎樣受到鄙棄。張光年逐一道來:“寫真實”論,“這是胡風集團在文藝上的代表性論點”,而一九五五年,“打退了他們的猖狂進攻”,當然也把“寫真實”論批倒了批臭了;“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這是一種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觀點,是‘寫真實’論的翻版”,而從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文藝界對這種觀點“進行了義正辭嚴的深入批判”;“中間人物”論和“現實主義深化”論,“這是在三年困難期間,在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嚴重影響下,產生出來的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謬論”,而“毛主席及時覺察了這種右傾機會主義逆流的危害性,指示中國作家協會查一查”,于是,中國作協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對之“揭發和批判”,《文藝報》也發表了批判文章①張光年:《駁“文藝黑線專政”論——從所謂“文藝黑線”的“黑八論”談起》,《人民日報》1977年12月7日。……張光年的文章,表明他們與江青們都認為“十七年”的文藝界存在著一條“黑線”,區別只在于,江青們認為這條“黑線”在文藝界實施了“專政”,而張光年們則認為這條“黑線”是被“專政”,至于對“黑線”實行“專政”者,當然是那條“紅線”。
五
如今讀這些意在“撥亂反正”的文章,時常忍俊不禁。例如,“文化部批判組”的文章寫道:“‘四人幫’……甚至把毛主席親筆加進一些文件和文章里的話也當作‘文藝黑線’的‘謬論’加以‘批判’,真是猖狂到了極點!”②文化部批判組:《一場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斗爭——批判“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紅旗》1978年第1期。在“十七年”里,許多關于文藝的文件、文章,都經過毛澤東批閱、修改。不少文件、文章里,都有些話實際出自毛澤東手筆。江青們要徹底否定“十七年”,就必須對這類文件、文章進行批判,而在批判的時候,自然不能把毛澤東加上的話分離出來,只能把毛澤東修改之事當成并不存在。當他們批判這些文件、文章時,實際上也批判了毛澤東加進去的那些話。“文化部批判組”的文章對這一點進行揭批,實在特別引人發笑。因為在這一點上,對“四人幫”的揭批者,與“四人幫”堪稱異曲同工,甚至更“工”。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是“百步笑五十步”。“文革”前的有些文件、文章,雖然經過毛澤東修改,但是,沒有哪一份關于文藝的文件、文章,像江青等人炮制的《紀要》那樣令毛澤東上心。《紀要》經過毛澤東三次精心修改,重要改動累計數十處,還加上了大段的話。當茅盾、劉白羽、張光年等人以及“文化部批判組”批判《紀要》時,那些出自毛澤東之手的話,當然也一起受到了批判。當時,甚至現在,也都有人認為,這是“猖狂到了極點”的。
在推倒“文藝黑線專政”論的過程中,冰心和曹禺的文章顯得很特別。推倒“文藝黑線專政”論,目的是為“十七年文藝”平反,因此,肯定、歌頌“十七年文藝”,是題中應有之義。既然要論證“四人幫”的“黑線專政”論是對“十七年文藝”的誣蔑,那“十七年文藝”的“輝煌成就”就是必須的論據。羅列“十七年文藝”的“輝煌成就”并歌頌之,許多揭批文章都是這樣做的。但是,冰心和曹禺的文章卻十分另類。冰心參加《人民日報》召開的座談會后,寫了短文《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流毒不可低估》。文章只說對這“黑線專政”論的“流毒和影響,我們絕不能小看,絕不能低估”,并無片言只語明確地肯定、贊美“十七年文藝”。避開對“十七年文藝”的評價,卻又要批判“四人幫”對“十七年文藝”的“誣蔑”,文章如何做呢?冰心別出心裁地說了一件“文革”期間江青對“兒歌園地”的摧殘。一九七四年,江青插手“兒歌園地”,讓兒歌變得非驢非馬。冰心以自己一個外孫為例,說明江青一伙“連天真爛漫的孩子都不放過”。說完這件事后,冰心又說“四人幫”一伙“在文風上也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然后以自己“最近看到的一首詩”為例,說明“四人幫”一伙“說假話、說空話、說絕話”的流毒有多么嚴重。①謝冰心:《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流毒不可低估》,《人民日報》,1977年12月4日文章的核心內容就是這兩件事。嚴格說來,冰心的文章其實是文不對題的。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冰心寫這篇文章時的心態。批判“四人幫”,冰心無疑是樂意的。推翻“文藝黑線專政”論,冰心自然也是贊成的。但是,肯定、贊美“十七年”,冰心是猶豫的,是不樂意的,是難以做到的。冰心參加了座談會,同意寫批判文章,表明她對“文革”、對江青一伙滿懷痛恨,樂意加入揭批的行列。但是,“十七年文藝”在冰心的記憶中也絕不是美好的。江青一伙說“十七年”的文藝界被“黑線”所“專政”,固然可笑。但是,正如賀敬之等人所說的,“十七年”間,文藝界的確有一條政治路線在“主導”著,在“專政”著。“紅線”也好,“黑線”也罷,有一條“線”在規范著、約束著所有人。而只要文藝界被某種力量所“專政”,就絕不能說是合理的,就絕不應該得到肯定、贊美。不愿意肯定、贊美“十七年”,卻又愿意寫文章批判“四人幫”對“十七年”的“誣蔑”,冰心便只能以“旁門左道”的方式成文。文章雖然短小,其實煞費苦心。
同樣耐人尋味的,是曹禺的文章。曹禺的文章題為《不容抹煞的十七年》。按理,應該正面列舉“十七年”的“輝煌成就”,才算是合乎題義。但是,曹禺的文章,也可謂別出機杼。那“十七年”,留給曹禺的,有著太多不愉快的記憶。在那“十七年”,曹禺有著太多的苦悶、彷徨。一個如此優秀的劇作家,在“十七年”里正值盛年,創作成就卻乏善可陳。曹禺自身的遭遇,曹禺自身的失敗,就證明著那“十七年”是不值得肯定的。進入五十年代,曹禺以自我批判自我否定開始新的藝術人生,以修改《雷雨》、《日出》、《北京人》這些舊作和杰作開始自己在新時代的戲劇生涯。在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后,一九五一年,曹禺開始寫《明朗的天》。田本相在《曹禺傳》說,曹禺后來對此有這樣的回憶:“盡管當時我很吃力,但仍然是很想去適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是硬著頭皮去寫的,但現在看來,是相當被動的,我那時也說不清是怎樣一種味道。”②田本相:《曹禺傳》,第379、472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那時,曹禺可謂被“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樣一種荒謬的鐵則所束縛、所“專政”。這樣寫出的東西,當然與那些舊作不可同日而語。畫家黃永玉曾說“十七年”里的曹禺“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③田本相:《曹禺傳》,第379、472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對于自己的萎縮、衰退,曹禺當然比任何人都清楚,也肯定比任何人都痛心。既如此,要他由衷地肯定、贊美“十七年”,那是不可能的。但曹禺畢竟與冰心不同。在“十七年”里,他曾有過“勢位”,現在,“四人幫”打倒了,他還可能再有“勢位”。他難以像冰心那樣,連一句肯定、贊美“十七年”的套話都不說。在《不容抹煞的十七年》這篇批判文章中,開頭和結尾部分有幾句肯定“十七年”的套話,文章主體部分,則是對周恩來的回憶和懷念。曹禺述說著周恩來來看戲時怎樣平易近人,平日里對自己怎樣關心愛護。一篇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卻主要是在懷念周恩來;一篇本該為“十七年文藝”評功擺好的文章,卻主要是在敘述與周恩來接觸時的細節,也打的是“擦邊球”。
當時批判“黑線專政”論、為“十七年文藝”極力辯護者,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希望文藝重返“十七年”的軌道。他們覺得理應如此。他們認為必須如此。他們相信不能不如此。然而,歷史的發展,有時還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就在他們奮力推翻“黑線專政”論、一心想讓文藝回到“十七年”的“正道”時,“傷痕文藝”在悄然興起。“傷痕文藝”中的許多作品,雖然帶著“十七年文藝”的遺風,有的甚至不無“文革文藝”的痕跡,但也明顯地撐破了“十七年文藝”的規范,在總體上,不但是對“文革文藝”的否定,也與“十七年文藝”揮手告別。政治也好,經濟也好,文化也好,重返“十七年”,只能是鬧劇。這樣的鬧劇,還真不難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