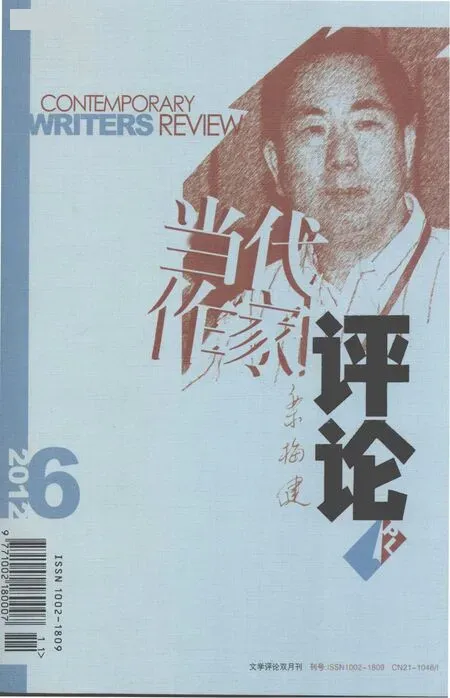“文革”期間的手抄本通俗小說研究
王 璐
一、小 引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文學史對于“文革”文學的揭示早已不僅僅局限于絕對效忠于“文革”政治的主流文學。在被主流意識形態嚴格控制的共名時代,還有一些接近自在狀態的文學實踐從幾乎不可忍受的重荷中幸存下來,提供了與當時公開文學完全不同的作品,手抄本通俗小說便是這些存在于主流文學話語之外①當然,這里必須說明的是,“存在于主流文學話語之外”并非指的是與主流文學話語無所干系。“文革”潛流文學中那些看似存在于主流文學話語之外的文學現象其實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浸淫。手抄本通俗小說與主流文學話語的糾纏關系也甚為復雜,后文將論述到這一點。的文學現象中的一種。
通俗小說歷來難入學者法眼,在業已浮出地表的“文革”手抄本作品中,通俗小說比起后來早成神話的朦朧詩等,雖然當年同樣被默默“手抄”過,但受到的關注卻無法與之同日而語。也許是因為認準了其文學含金量的低微,文學史對于簡陋粗疏的“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發掘、研究往往只有只言片語,即便是談到手抄本小說,述及的對象也多為像《波動》、《公開的情書》這樣思想上、藝術上在當時看來具有絕對先鋒性的小說。②文學史對手抄本小說的研究現狀可見三本文學史教材: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修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其中,《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對“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中的《一只繡花鞋》、《第二次握手》終于有了相對深入的個案分析,這也給筆者寫作本文帶來一定的啟發。然而,一部作品的文學藝術價值與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并不能等同視之,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即使某階段作家作品甚少乃至全無,它同樣也是小說創作的一種態勢……某種特殊階段的‘創作空白’也應使之進入研究視野,這是‘史’的研究的需要”。③陳大康:《明代小說史·序言》,第9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同理,手抄本通俗小說雖然文學價值不高,但它在寫作和傳播過程中引發了那么多讀者形形色色的閱讀體驗,對這枚文化化石的勘探,關乎的其實是我們對于“文革”歷史的想象與認知。對于文學史和集體記憶而言,手抄本通俗小說作為精神檔案的價值應該并不低于其他的手抄本作品,它的意義也不可能僅僅局限于文學領域。也就是說,手抄本通俗小說雖然并非反映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嚴肅思考,但卻是那個時代精神現象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有機組成。這些作品的創作過程、傳播形式和內容能指性符號遠遠超過作品本身帶給文學史的文本意義,從中折射的文化心態也未嘗不聯系著我們的今天。正因為如此,筆者不揣淺陋,擬以此文來對“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作一番詳細考察,以期厘清其流播遷衍的線索,挖掘特定時代下這股文學現象的內部信息,充實和豐富現有的歷史總結和文學斷言。
在進入正式論述之前,筆者不得不對本文研究的基石,即自己所閱讀的“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文本作一番說明。按理說,研究“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應盡可能以最充分的依據,找到離創作真實最接近、最原始的版本,這樣才能還原與澄清“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真實面目,作出恰切定位。然而當年以“手抄”方式流傳的文本今天能夠進入文學史的研究視野,又必然是已經公開出版的。這就帶來了一些問題。首先需要謹慎的是,市場上的各種所謂手抄本小說真假相混,殊難辨認。基于這種警覺,筆者的閱讀文本主要采自《暗流:“文革”手抄文存》①白士弘編:《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這本正式的出版物,書中提供了大量看來較為可信的介紹及圖片,有原始抄本作為證據。其次,在創作和發表之間的這一較長的時間差使得這些公開出版的文本,“無論其內容,還是發表方式,事實上已不是‘文革’中的那些‘手抄本’,后者的原來面貌已無法重現”。②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183頁。雖然如此,我們考察“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創作方式、敘事邏輯、閱讀心理等等方面,以現今出版的較為可靠③所謂“可靠”,即這些已經出版了的“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雖然不是原本,甚至經過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但它們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來抄本的基本面貌。的“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為材料,還原到這些作品醞釀和形成的時代背景下去閱讀和理解,還是可以追索到很多耐人尋味的信息。
二、接力傳抄下的炮制——“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創作特點及基本面貌
手抄本作為書籍存在樣式的式微,不只是緣于今日大規模批量生產的印刷工業的突飛猛進,就是在活字印刷術發明的早期也出現了不可挽回的頹勢。④冉云飛:《手抄本的流亡》,第67頁,鄭州,大象出版社,1998。在文學史上,別種樣式的文學作品,一般并非定要刊印成書以后才能在世間廣為流傳,然而篇幅相對較長的通俗小說則不然。⑤見陳大康《明代小說史》,第159-160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可是,歷史的演進過程又總不斷遭遇著尷尬,在堂堂二十世紀的中國大陸,“手抄”這種最原始的文學傳播樣式曾經成為通俗文學的主要傳播樣式存在過。
“文革”時期,文學作品失去正常的創作和發表條件,許多文學作品不得不通過人工抄寫的方式流傳,在這其中,通俗小說的傳抄行為最為熱烈,傳播范圍也最為廣泛。“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原創者和傳抄者以當時社會底層的“知識青年”和城里工廠的青年工人為主體,其影響遍及部隊、工廠、學校。人們以日記本或工作手冊之類的紙制品作為載體,⑥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手抄本的“本”并非書本的本的字面意義,而是其傳播的載體,各種本子也是那個時代的紀念物。見白士弘編《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17頁。自發而隱秘地于密友之間傳抄小說。這種非常態時期特殊的傳播、接受方式使“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具有一些鮮明的特點。
如果不是只孤立地考察作品而是同時又注意它的社會影響,那么從作家到廣大讀者欣賞作品便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過程。通常情況下,創作與閱讀是該過程中最主要的兩個既相互聯系又相對獨立的環節。但“文革”時期,手抄本通俗小說的創作和閱讀卻呈現出同一性的過程。即它的流傳過程也是創作過程,抄寫者既是通俗小說的閱讀者,也是它的創作者,可謂一身二任。著名的手抄本小說《一只繡花鞋》的主要創作者張寶瑞回憶當年的傳抄現象時說:“抄的過程他們也加工,他要覺得這個詞不合適,他就給改了,或者增加點兒細節都有可能。所以手抄本實際上是群體勞動,逐步被加工。”①馮成平、張寶瑞:《文化饑渴:對話寶瑞》,第103、102頁,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8。轟動一時的手抄本小說《第二次握手》在原創者張揚那里,一直是以《歸來》為名,一九七九年該小說正式出版之時,考慮到大多數中國人對傳抄中的改題更感親切,經原作者同意,出版社遵循了讀者的意愿。這部小說成了文學史罕見的“由讀者取名而不是作者取名”的作品。②見張揚《我與〈第二次握手〉》,第263-264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無論是作品題目的竄改還是小說內容的增減,正是由于存在著傳抄者根據自己文字功底、生活經驗和審美好惡對小說進行再加工、再創作的現象,同一部手抄本小說會有不同的版本出現。所以有人說:“當手抄本風靡起來時,我曾經讀過至少十幾個不同版本的《少女之心》(拙劣的和比較不拙劣的)……這些版本因抄寫者加入了自己的感受與想象而變得面目全非。”③朱大可:《記憶的紅皮書》,第86-87頁,廣州,花城出版社,2008。造成“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版本不固定的原因還來自于其口頭創作與書面創作相結合的創作方式。跟那些在紙面上進行原創的小說不同,手抄本通俗小說中有很多是即興創作于唇齒之間的。換句話說,這些作品實際上是某種談資的延伸或物化,而它們之所以又會被興沖沖地傳抄,恐怕也主要是為了獲取其中的談資。據張寶瑞回憶,當年,他坐在鍋爐邊,映著熊熊爐火,對圍坐在周圍的工友們“邊侃邊編”,以先講后記的方式誕生了他的那些小說,而他所說的故事也隨著口口轉述傳播開來。④馮成平、張寶瑞:《文化饑渴:對話寶瑞》,第103、102頁,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8。文字和口頭故事間的相互轉換使得有些“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從一開始就并不具備一個穩定的原本。
在對創作階群和寫作、傳播特點進行了上述考量之后,“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一些基本面貌也就變得不難理解了。比如,它是被作為“文革”時期的談資和消遣之物的,而不難想見,若非經過說書先生那般長期正規的訓練,要生動而完整地轉述故事內容便是極難做到的事,因而很多由口頭故事落實成文的“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大多結構單純、情節簡單、文字粗糙,這也是集體創作特有的面貌。當閱讀環節擴張其功能來補充創作領域的不足時,雖然本為讀者的抄寫者的修改加工不無合理之處,但他們的書寫動機、文化水準與藝術品位都極大地影響了手抄本的文學價值。于是,這類作品雖然也具有一般通俗小說共有的故事性、娛樂性、趣味性等特點,卻不能媲美于柯南·道爾的活靈活現,也無法媲美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絲絲入扣。很多作品雖然注意將兇殺、恐怖、艷情等諸種因素摻雜在一起引人入勝,卻總在敘事的過程中表現出構思的潦草及想象的謬誤。由此才會出現“人聲雜亂”的“特快軟席車廂”⑤⑥ 白士弘編:《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71、231頁。(《葉飛三下江南》),才會有大阪街頭日本特務所開的蘇制“伏爾加”小汽車⑥(《一百個美女的塑像》)。在《一縷金黃色的長發》里,那個美麗的女特務蔣宛梅,竟能一下子把一整瓶白蘭地給灌下去,而下酒之物則不過是一塊膩人的巧克力。由此可知,無論抄寫者還是故事的聽講人,其實都并不了解白蘭地酒的烈度和用途,也對巧克力之外的西餐飲食所知甚少。這些都極大地影響了“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文學品格。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一提。一般說來,通俗小說都具有著精神產品和文化商品的雙重屬性。在“文革”中,專制的文化政策使手抄本通俗小說失去了出版營利的可能,盡管如此,它卻似乎并沒有因此失去“文化商品”的屬性。當時手抄本通俗小說的善講者在群眾中極受歡迎和尊重。比如,云南有一個姓沈的上海知青,就因為會講故事,能把《一雙繡花鞋》講得繪聲繪色,很多知青農場都爭先恐后做上好吃的請他講,講了這家講那家,吃了總場吃分場。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這位知青因此蹭了不少“有肉的飯”吃。①見何德麟《〈一只繡花鞋〉背后的故事》,《紅巖春秋》2009年第6期,第76頁。這里足見手抄本通俗小說在民間受到的歡迎。當然,比起傳抄所要承擔的巨大政治風險,比起“非法閱讀”所付出的沉重代價,②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當然要數由《第二次握手》的傳抄所引發的“文字獄”,見張揚《我與〈第二次握手〉》。這些所得之福已顯得微乎其微。
三、對主流觀念的迎合與偏離——“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文本分析
“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創作方式和傳抄階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文學價值的低微,從這方面說,跟其他手抄本作品比如說當代朦朧詩的“圣地”——白洋淀的文化產品相比,這些筆觸粗疏、內容蕪雜的故事書,盡管當年同樣以手抄的形式存在過,卻既不需要也無資格享受一個文飾的過去。盡管如此,我們卻不應小覷或漠視這些看似無聊的故事文本。因為要深入了解它們當年廣為流行的原因,必然離不開對文本敘事邏輯、構成要素等的勘探。
“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創作并非采取與國家政權和現實社會制度自覺對立的立場;相反,文本更多表現出的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迎合,是對時代共名的演繹。“大批判、肅煞、顛覆、嗜血成性、拙劣的迎附政治語境、神經質的圖解階級斗爭觀、空洞浮夸等大標語式的信息符號仍是手抄本的主流。”③白士弘編:《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16-17、23、207-208頁。《一只繡花鞋》、《葉飛三下江南》、《一縷金黃色的頭發》、《地下堡壘的覆滅》、《遠東之花》這些小說在在都與現實社會政治情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文革”政治的匪夷所思與云譎波詭為民間想象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此類故事發生地多選北京、南京、重慶、上海、武漢、廣州等地。究其原因,正如有的學者分析的,“是案發地便于詮釋階級斗爭的理論——因為以上地名多與國民黨舊政權中樞相關聯,重慶、南京是舊政體的首都,暗藏的‘歷史垃圾’自然多;上海、廣州又同是帝國主義分子經營多年的半殖民地,潛伏特務自然就不會少”,④白士弘編:《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16-17、23、207-208頁。作為“全國人民心臟”的北京和武漢、南京的長江大橋更是為鋪寫與敵特的斗爭提供了最好的案發地。受“主流文學”創作規范的影響,敵我對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對立邏輯支撐著小說的整體構架。在上述“反特”偵探題材(這是“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主要的一類)的小說中,俯拾即是這樣的主流政治話語:“毛主席教導我們,敵人絕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做最后的掙扎,要進行破壞和搗亂,我們要毫不留情地把他們消滅干凈”⑤白士弘編:《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16-17、23、207-208頁。(《地下堡壘的覆滅》),“我們是兩個階級戰壕里的人,你是國民黨,我是共產黨”,“我們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你是資產階級的小姐,我是無產階級的戰士”。⑥張寶瑞:《一只繡花鞋》,第260-261頁,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敵我界線的分明體現出時代政治對“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思想、主題的巨大影響和約束,這種約束同樣體現在各小說的人物塑造上。手抄本通俗小說里的“我方”主要人物大多與當時的主流觀念相對應,是絕對的“無產階級英雄典型”。他們大都具有外向性格,在近于虛構的客觀世界中從事維護人民利益的反特斗爭,“他們沒有時間也根本不需要進行更多的反省和懷疑,因為馬克思主義能夠為實現正確目標提供正確的指導”。①〔美〕羅德里克·麥史法夸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第632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龍飛、葉飛、陳剛、沈楠這些小說的主角,都是被主流意識形態徹底規訓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龍飛藝高人膽大,數次深入敵人巢穴尋找梅花圖(《一只繡花鞋》);葉飛三下江南,與敵人巧妙周旋,制服一路行兇的特務,挫敗階級敵人的驚天陰謀(《葉飛三下江南》);陳剛遠赴南洋,擒獲王牌女特務“遠東之花”,駕駛戰斗機凱旋歸國(《遠東之花》)……在對這些故事的描繪中,雖然摻雜了偵探、恐怖、艷情等元素,卻在敘事邏輯和人物刻畫等關鍵環節緊隨“主流文學”的創作理念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畢竟不像“主流文學”那般強調直接的社會功利性與立竿見影的政治作用。因而在深受“主流文學”的影響之余,還是存活了相當部分的異質因素,這些因素構成了對主流政治宣傳的顛覆。比如,很多小說雖然在主題觀念、人物塑造等方面屈從于主流政治觀念,但并不死盯著現實政治不放,而是將敘述的興奮點放在情節的刺激、氣氛的恐怖和事件的神秘上。像看守醫院太平間老頭裝著發報機的假駝背(《一只繡花鞋》)、零點時廢墟里的笑聲(《綠色的尸體》)、被挖去裝有微型照相機的左眼的女尸(《一只繡花鞋》)、玻璃窗外的一張灰臉(《一縷金黃色的頭發》),等等,在這里,小說以不顧客觀可能性限制的離奇描述來逗引讀者的心理緊張和閱讀欲望,其傳奇、偵探色彩十足無疑偏離了“文革”“主流文學”的創作規范,沖淡了小說的政治意義。再如,這類小說時常在敘述之中插入大量非政治而極具吸引力的元素(這些元素往往也是這類粗制小說最具“文學性”的地方),它們的存在實際上使得作品主題領域和人物塑造上所依附的主流意識形態被懸置和延宕。《一只繡花鞋》中,龍飛跟蹤一個前來接頭的梅花黨成員到五臺山時,對五臺山風景和古跡的介紹;肖克與路明在破案之余互講的笑話;破案人員追蹤敵特所到之處對異國風貌的描繪……“當小說的情節發展滯留于大量地理風貌、名勝古跡、奇風異俗、神話傳說、歷史典故、政治秘聞、破案技巧、故事笑話之類的內容,這時候小說已構成了對‘階級斗爭’內容的消解”。②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修訂本),第342頁。《一百個美女的塑像》、《三○三號房間的秘密》、《遠東之花》等故事將發生地放置于日本、法國、新加坡等資本主義的國度,包含了傳抄者對于“對立世界”的想象。這些想象往往又暗含著對于異質世界的驚羨之情和向往之意,形成了對“文革”政治理念和道德內涵的消解。
“文革”中,人的政治以外的意義被忽視。“主流文學”通常將每個人都組織到一個特定的政治目標中去,為那個政治目標服務,而個人生活、成長乃至愛情在社會生活中的正當地位從不被關注。整個“文革”時代,社會輿論否定男女情愛,甚至抹煞兩性區別,像愛情這種更具私人性質的生活描寫,更是被排斥在“主流文學”之外。不僅八個“樣板戲”,主流作品中的正面英雄都是不存在“愛情生活”的。在“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涉及愛情關系的作品里,《一只繡花鞋》中的正面英雄龍飛和其妻子南云之間就僅僅表現出階級同志的情感,然而還是有相當一部分手抄本通俗小說展現出了和“主流文學”殊異的面目。盡管《九級浪》、《少女之心》、《曼娜回憶錄》和《第二次握手》在藝術上參差不齊,但它們都毫無例外地涉及了愛情。《九級浪》中,作者把我們領入司馬麗的內心世界,展現了她與男性間的愛情糾葛和心靈的絕望掙扎。①見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中相關介紹,第76-79 頁,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少女之心》中裸露的情愛描繪早已成了一代人的閱讀記憶,在廣大青少年中發揮了類似于性啟蒙讀物的作用。②見白士弘編《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27-28、19頁。而《曼娜回憶錄》和《第二次握手》中關于人物間愛情故事的描繪則顯得更為精細動人。這些手抄本通俗小說在一個拒絕、否定個體需求和情感價值的年代實現了個人性文學表達的回歸,使人的生命屬性獲得了自然釋放,表現出對政治禁忌的突破和超越。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即使是在這些以男女之愛為表現對象的小說里,主流意識形態還是無孔不入地決定著敘事的發展。在手抄本小說《第二次握手》中,雖然對優秀知識分子和杰出科學家的歌頌已構成了和“主流文學”創作規范的“根本任務”論的直接沖突,對蘇冠蘭與丁潔瓊之間愛情故事的描繪也體現了可貴的犯忌之勇,然而整部小說表現的還是一種“正確的”政治,那就是:主流意識形態決定著個人的人生選擇——“小我”的感情必須服從“大我”的理想,個人的真正感情必須按政治標準來過濾和消解。小說中,蘇冠蘭放棄對丁潔瓊的等待而選擇葉玉菡是革命的需要,是對政治的服從。丁潔瓊這樣一位祖國急需的科技人才發現自己苦苦等待的情人背棄諾言后哀痛欲絕,準備離開北京之時,又是政治的力量影響了她的去留——周恩來的出場顯然代表了黨和國家,感情的矛盾糾纏最終是以高級領導人的力量來彌合的。“丁潔瓊、蘇冠蘭、葉玉菡誰也沒有獲得愛情,然而這種男女之愛的缺陷在對‘祖國’的愛情中得到補償,三人無法解決的矛盾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象征性地解決了。”③李揚:《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第342頁,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愛國主義”這面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政治旗幟在此再一次發揮了作用,知識分子在政治的恩威并施下又一次被“馴化”,表現出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臣服與皈依。這樣的處理邏輯,本質上并沒有偏離“主流文學”所確立的敘事框架,體現出政治話語強力壓制個人生活的粗暴本質。
由此可見,“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既有著公式化的敘述,又有對“文革”主流意識形態非對抗性的錯位和逃逸,其個人性文學表達的精華和霸權話語的糟粕夾雜在一起,構成了這些故事文本獨特的藏污納垢之態。政治敘事、歷史傳奇、個人體驗的經緯橫豎糾纏,造成了手抄本通俗小說各種文化成分并存的奇觀,使文本呈現出一種多層次性:對主流敘事成規的因襲和文本裂隙中的異質元素夾雜相成,曖昧不清。
四、專制時代里的逆流——“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創作心理和接受心態
在《暗流:“文革”手抄文存》這本書的序言中,代序者對手抄本通俗小說有過這樣的評判,他說:“手抄本之于中國當代精神生活流變史和個人記憶的撞擊與烙印無異于填鴨式滲入民族記憶之中的文集、語錄,其影響幾乎浸淫了那一代人整個精神和心智的成長期,那種公式化的敘事和粗暴的霸權話語,甚或影響他們一生且延及后世。”④見白士弘編《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第27-28、19頁。文化專制和話語霸權嚴重帶菌者的身份的確讓手抄本通俗小說“難辭其咎”。然而,如果回到當年此類小說的誕生現場,對這一文學現象進行一番掘地三尺的考量,手抄本小說所呈現的這番面貌似乎又讓人不忍厚責。
盡管從可能性的角度說,文學可以超越現實社會進行更為深入的精神探索,我們對于手抄本等當年非公開的文學創作現象的研究本來也就暗含著我們對于文學的期待和寄望。然而,文學的現實卻總又呈現出一種命定的束縛,就像某位學者所說的,“任何作家都無法超越自己所處的年代,其創作只能與當代的社會狀態相適應,創作受到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小說觀的制約”。①陳大康:《明代小說史》,第20頁。新中國成立后持續有效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和規訓,已成功構建了一套主流政治話語;“文革”前期的大批斗、大串聯、大規模武斗,也極大地渲染了全民革命的社會氛圍。“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在這樣的時代土壤中產生,它來自時代,為這個時代所造就,就必然會受到這個時代的影響和約束。更何況,當我們已經確定,產生于“文革”結束后的“傷痕”、“反思”文學,其語言風格、敘述方式等都與“文革”“主流文學”有極大的類似時,就毋寧說身處“文革”期的手抄本了。在這里,文學在非常年代里的極端敗壞體現出了政治對文學的致命傷害:中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文學難以找到任何避身之所,政治“是非”的觀念已深深烙印在民眾心中,成為內化的規范。除了受時代氛圍不自覺浸淫的原因,“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之所以攜帶了大量的政治毒素,恐怕也是創作者的自我保護意識使然。在那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手抄本通俗小說如果不模仿或偽裝成革命的套路,傳抄者難免不遭殃。于是,不單內容的敘述框架要“追求”安全,就是在包裝上,也出現了被“加上‘毛選’的塑料封套,偽裝成革命圣典”的《少女之心》。②見朱大可《記憶的紅皮書》,第87頁。
雖然手抄本通俗小說在“文革”中始終為當時政權所不容,在一九七四年,江青集團還發動了一場全國范圍的對“地下文學”的圍剿,“一時間,破字猜謎,煩瑣考證,大抓影射,羅織構陷之風盛行,文字獄遍及全國”,③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第293-295頁。不少傳抄者受牽連入獄,但是手抄本通俗小說卻一直有著龐大的讀者群。人們“不辭勞苦”地拿著生命作抵押,秘密傳抄這些手抄本小說,以獲得比別人更多的手抄本為榮。他們夜里打著手電躲在被窩里偷偷傳看,用隨手可得的馬糞紙奮筆謄寫,在路邊墻角賊頭賊腦地“接頭交易”。每個人都成了手抄本的自發創作者和推廣者。④見粲然《手抄本:相見不如懷念》,《往事》2004年第4期。這種傳抄閱讀的空前盛況恰恰反映了那個時代“主流文學”的匱乏和貧血。人們在難耐的文化饑荒里表現出極端的精神饑渴,故而以手抄本通俗小說作為應急式的補償。然而,僅僅以“自娛、自賞與自我宣泄”來涵蓋當年傳抄者的創作、接受心理,從而對手抄本“通俗小說”蓋棺定論還太過表淺。如果我們對手抄本通俗小說在“文革”時代的流行進行更為深入的考察,特別是這種文學現象所聯結的那個時代潛在的社會心理,我們也許還能發現某些更具特殊性的文化心態以及這種心態與當時的政治變化間的特殊關聯。
如果說“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在文本內容上不與現實政治自覺對立,那么它的傳播方式——“手抄”則無疑是一種潛在的集體反抗。當印刷文本為政府壟斷和控制時,“手抄”就不再是一種簡單的交際手段和傳播方式,尤其在文化專制的背景下,它實際上是一種思想行為,是對時代的反抗。如古代社會里《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等作品的流傳,手抄行為就曾經作為傳播媒介而對文化專制政治表現出抗爭,使地下文本成為沖破封建禁忌制度堅冰的春潮。在越少動筆就越安全的“文革”年代,大張旗鼓地去抄寫這類很可能招災惹禍的可疑小說,正顯示著普通民眾某種難以遏止的心理沖動和頑強的表達意識。這種接力傳抄既悄悄地潛伏于地下,又熱烈得不可控制,正因為如此,它才不單是一種大膽的個人行為,還更表現出一種集體的越軌。傳抄者在傳播和閱讀的過程中,會體會到“逾矩”所帶來的犯罪欣悅感,這在壓抑荒蕪的年代里無疑刺激了人們的神經,充當了某種代償性的宣泄渠道,而這種行為本身就成了反抗社會壓抑的手段,構成了對“文革”政治的挑戰。需要說明的是,我們肯定這種突破禁忌的行為并非是要給與這種挑戰形式本身多么高的評價,在產生了印刷文明的國度,文學傳播以這樣的方式進行無疑是一種倒退。然而這種抗禁行為在當時卻的的確確有著不容忽視的歷史價值,在默默積累的對于荒謬政治的反撥中,它承擔了一份叛逆者的角色。正像有的學者分析的:“并不是一次抓捕‘四人幫’的高層突發事變,而是千百萬人民水滴石穿的地下抄寫行為,才真正傳遞出和積攢著否定‘文革’的民意基礎。”①劉東:《黑天的故事——“文革”時代的地下手抄本》,《開放時代》2005年第6期,第152頁。這樣一種來自民間地火的文學趨勢發展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門廣場的詩歌運動時達到了火山爆發的程度,于是,一個舊時代的喪鐘也終于敲響了。
從這個角度考慮,當我們再一次回到“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具體文本,不要急于根據其對“主流文學”創作規范的迎合與否來裁判它們,而是以其來管窺當時人們獨特的文化心理,我們便可以看到,在那個幾近文化沙漠的時代背后,洶涌著怎樣的狂想和偏見、恐懼與希望,它們又怎樣凝聚著終結“文革”的力量。
在情感壓抑、生活封閉的年代,人們的獵奇和窺探之心反倒異常強烈,表現在“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中,是對政治文化秘密和生命秘密的不倦探求。“文革”時代,雖說人們最怕談論的是政治消息,最想打聽的其實也正是政治消息。各種“反特”題材的手抄本小說迎合階級斗爭的時代氛圍,描寫公安人員與炸長江大橋、炸密云水庫的破壞分子的周旋斗爭,其實都是當時各類神秘傳聞的翻版,是對政治斗爭的民間理解與民間想象。而隨著作品對我敵特人員深入到臺灣、海外等地破案經歷的描繪,讀者便更加由此窺見到資本主義“腐朽世界”的繁榮景象。革命是要求摒棄物質享受的,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更是應該拒之千里,但“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卻在那個對立的世界里展開了豐富的幻想,進行了細致的描摹,這其中不無把玩、向往之意。這種對于異質世界的偷嘗禁果式的憧憬正悄悄地升騰于革命的廢墟之上。小說的描寫既暗合了人們的心思,又在煽動著他們對于封閉肅殺、禁錮重重的社會現實的不滿。“文革”中成為禁區的男女情感問題,在手抄本通俗小說中卻是“大放異彩”。對于那些在感情的沙漠中奄奄一息的讀者而言,纏綿悱惻的情愛故事不啻于一頓豐饒的情感大餐。于是,《第二次握手》、《曼娜回憶錄》、《少女之心》等手抄本小說的出現,完成了對人們備受扭曲和創傷的情愛原欲的激活。它們和“反特”題材中作為階級敵人的美女特務形象一起,向當時正處于極度情愛干渴中的人們,提供了唯一敢于領受的情色享受。這些小說中的愛情想象和性描寫實際上是用文學的方式反抗了“文革”壓抑人性的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是對革命的禁欲主義的僭越。
禁錮與禁忌總是伴隨著超常的欲望。在一個人性被禁錮的時代,人們尋奇探秘和情愛享受等基本欲求竟是靠著這類手抄本去滿足的,這恐怕為實施“禁欲主義”的權力人物所始料不及。這一現象表現了社會禁忌造成的荒謬以及給民眾帶來的精神傷害和人性扭曲,而它更有歷史意義的地方則在于對當時政治環境變化的配合。只要看看手抄本通俗小說在“文革”中受到的截然對立的評價——它在文藝整頓中受到的圍剿和在民間受到的歡迎,便可以想見,在專制的政治現實的背后,人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疏離和叛逆之心正在怎樣暗流涌動。在荒蕪的歲月里,在黑暗和高壓下,這種百姓意志默默積累、掙扎不息,終于使那場荼毒生靈的革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這或許是“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更深切的文化意味。
五、結 語
對“文革”手抄本通俗小說的一步步勘探把我們帶入了“文革”年代最為隱秘精微的底層,感受到那個時代精神潛流的默默洶涌,于是我們對于那場革命的理解也有了更為立體化的可能。在一個毫無自由可言的專制環境里,手抄本通俗小說以其粗糙、野性、活潑的形態生氣勃勃地生長,證明著文學不亡的事實,也宣告了主流意識形態企圖制造的“大一統”局面的失敗。然而又因為它與時代政治意味不盡的關聯,在政治語境因素淡化、政治形勢扭轉之后,在新時代有了新的需要表達的情緒、話題之后,手抄本通俗小說便難逃衰休的命運。然而,我們卻不該輕視這些手抄本小說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新故事的崛起和之后通俗文藝的發展所作出的土壤優化的貢獻,依靠它所培養出的廣大讀者群和一支龐大的群眾性創作隊伍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八十年代文學復蘇的努力。可即使如此,我們仍很難不去為之抱恨:如果手抄本通俗小說能夠更具文學品格,更富精神內涵,那么“文革”后中國小說的發展也許還能獲得一個更高的起點和稍微豐厚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