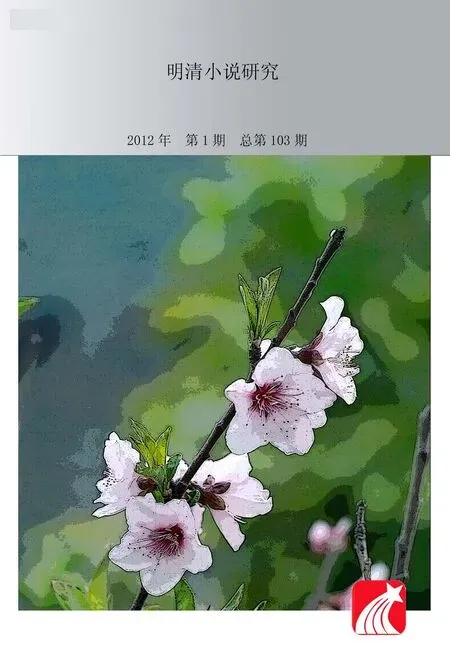日本漢文小說的發展及其理論探析
··
所謂日本漢文小說,主要指從日本江戶(1600-1868)時代中期至明治(1868-1912)時代后期,日本作家以漢字作為敘述和書寫的工具,模仿中國小說,描寫和反映日本的風土人情及社會生活的敘事文學作品。對于日本漢文小說的研究,在日本,始于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其研究多為零散的對于單部(篇)作品或某一類作品的考證和介紹。上世紀90年代,我國學者開始涉足這一領域并取得驕人成績。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開展:一是對作品進行收集和整理,最重要的成果是2003年在臺灣出版的《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全五冊);二是對作品進行較為深入的個案或綜合研究,其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王三慶的《日本漢文小說研究初稿》、孫虎堂的《日本漢文小說研究》等。這些研究,多關注中國古代小說在日本的傳播、日本漢文小說的內容、文體和藝術特點等,而少有涉及日本漢文小說家的小說觀念,以及其與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關聯等問題,而這卻是深入探討日本漢文小說發展及其美學風格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本文將以此為分析重點而展開。
一、日本漢文小說興盛的原因
毋庸置疑,要寫作漢文小說,首先要有嫻熟運用漢字進行敘述和書寫的能力,以及對于漢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的能力。漢字傳入日本的時間,最早可追溯至漢代。據《后漢書·東夷傳》記載,建武中元二年(57),后漢光武帝賜印綬與委(倭)奴國王,這應該是日本邂逅漢字的最早記錄。日本歷史學家坂本太郎認為:“在漢代時各倭國與漢通交就需要以漢字為媒介,邪馬臺國(按:日本統一之前位于九州的部族國家)與魏通交時,顯然已有國書的收受和爵號的授予。盡管人數很少,范圍很窄,但已經理解和使用漢字了”①。到了公元5世紀,日本人對漢字的使用就已經比較自如,《宋書·蠻夷傳》記載了順帝升明二年(478)倭王武的上表文,用的是較為標準的四字句式,可以看出是對六朝四六駢體文的模仿。
關于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史的記載,最早見于日本《古事記》(712)中。其在應神天皇(約3世紀末)“文化的傳來”一節稱,朝鮮百濟博士王仁將中國的漢文典籍《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帶到了日本。此后,從公元7世紀初至9世紀前半葉的200多年里,日本先后向中國派遣了4批遣隋使和15批遣唐使。這些人士不僅在華學習中國的政治、法律、儒學、佛學以及文學藝術等,而且在他們歸國之時,還從中國帶回了大量文化典籍,這些典籍對日本的政治、宗教及文化制度的建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平安朝(794-1192)后期,漢文化的影響一度被削弱,但是隨著鐮倉(1192-1333)、室町(1333-1573)幕府的建立,中國文化又再度成為日本學習和借鑒的對象。下至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同樣倡導和獎掖漢學②,在幕府文教政策的推動下,各級學校都開設了漢文教育課程,一些著名學者如荻生徂徠甚至身體力行進行漢語的普及教育工作③。如果說,在江戶時代以前,儒學和漢文化更多的是掌握在皇室、公卿貴族、武家、高級僧侶及上層文人的手中,那么到了江戶時代,尤其是江戶時代的后期,儒學和漢文化則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這種普及,為日本漢文小說的興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日本的漢文學創作,是日本古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漢文小說創作形成一定氣候,并能以整體形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是江戶時代中期至明治時代間的事情。筆者認為這種變化與當時大量中國小說作品的輸入以及隨之而來的對中國小說文學樣式的接受及模仿有直接的關聯。中國小說東傳日本并不始于江戶時代。據約成書于公元9世紀末的日本第一部敕編書籍目錄——《本朝見在書目錄》(后改稱為《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記載,當時傳入日本的漢籍達1579部,其中收錄的中國古小說有40余種,諸如《山海經》、《列仙傳》、《十洲記》、《神異經》、《西京雜記》、《洞冥記》、《博物記》、《搜神記》、《拾遺記》、《搜神后記》、《世說新語》等重要的漢魏六朝小說,都已囊括其中,此外還有唐代前期傳奇《游仙窟》和佚事小說《朝野僉載》等。但是,相對于1500多部以儒家經典、佛教經典和符合儒家文教理念的詩文作品為主的漢籍而言,這40余種古小說的存在,其影響是微小的,而且即使有影響,也僅限于詩文的創作活動中④。這說明,在奈良、平安時代,雖然已經有了中國小說的傳入,但是受中國古代以詩文為文學正宗的影響,小說這種文學樣式并沒有引起日本文人的重視。
江戶時代,日本實行鎖國政策。但即使如此,文化書籍東傳日本仍然呈現井噴之勢。有學者根據江戶時代日本海關記錄的渡來書目《赍來書目》、《書籍元帳》、《落札帳》等進行整理統計,認為江戶時期以商品名義從長崎港輸入的中國書籍至少有7893種,而不以商品名義輸入的則不計其數⑤。毫無疑問,在這些書籍中,小說作品當占有相當數量。唐本屋田中清兵衛的《唐本目錄》和《舶載書目》記載了其當年輸入中國小說的一些情況:
● 享保十二年(1727)進口中國小說十四部
● 寬保元年(1741)進口中國小說十二部
● 寶歷四年(1754)九號船載來中國小說三十部⑥
在18世紀中葉,僅一家專營中國書籍的書店,其一年進口中國的小說就可多達十余部至三十部,由此不難推想日本全國的情形。此外,我們還可從一些單部作品的輸入情況,來推知那個時代中國小說在日本的熱銷和受歡迎的程度。《剪燈新話》和《剪燈余話》是廣受日本讀者喜愛的中國小說,據學者研究,這兩部小說最早傳入日本的時間應不晚于16世紀中葉,甚至還可能在更早的15世紀末⑦。但是,直至18世紀末,這兩部小說仍被大量從中國進口。據大庭修《江戶時代唐船載來書研究》資料編“商船載來書目”記載顯示,僅寬正六年(1794),日本就一次性購進這兩部書達30部30套。
18世紀中葉,大阪書林的秋水園主人曾為“初讀舶來小說者”編輯了一部中國俗語辭書,名曰《小說字匯》。這部工具書所征引的書籍以當時流傳于日本的中國白話小說為主,共159種。在今天看來,這些書目不全然是小說,有些甚至不是文學作品,但從一國對于他國小說接受的角度著眼,我們仍不能不驚訝和感嘆于這一時期日本對于中國小說輸入的多和廣。楊彬博士在比較和研究了《小說字匯》涉及的小說書目、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中的小說書目、魯迅收錄在《集外集拾遺補編》中的根據日本友人辛島驍提供的《內閣文庫書目》(日本)抄錄的小說書目,以及董康的《書舶庸譚》、孫楷第的《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后,得出結論說:在1791年以前,傳入日本的中國小說應該不少于200種,如果考慮到之后傳入的情況,則數字還要增加,并且認為“舉凡中國小說所能產生的類型,幾乎全部加入過東傳的行列”,而中國古代通俗小說則“幾乎全部流傳到古代日本”⑧。
中國小說作品的大量輸入,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日本讀者對于中國小說喜愛的程度。出生于享保十九年(1734)的皆川淇園,曾在其文章中記載了其與弟及友人讀《水滸傳》等中國小說的逸事:
余與弟章幼時嘗聞家大人說《水滸傳》第一回“魔君出幽將生世之事”,而心愿續聞其后事,而家大人無暇及之。余兄弟請其書,枕藉以讀之,經一年后粗得通曉其大略。及十八九歲,得一百回《水滸》讀之。友人清君錦亦酷好之,每會互舉其文奇者以為談資。后又遂與君錦共讀他演奇小說,如《西游》、《西洋》、《金瓶》、《封神》、《女仙》、《禪真》等諸書,無不遍讀……最后得《平妖》讀之,與君錦、弟章玩讀不已。此距今四十余年前事也。⑨
江戶時代的漢文小說家,可以說都是中國小說的熱心讀者,或許他們正是經由閱讀、喜愛、進而發展為模擬和創作漢文小說的。岡島冠山(1674-1729)是日本著名的漢文小說翻譯家和作家,他所翻譯的一百回本《通俗忠義水滸傳》是日本最早的譯本,同時,他還根據日本史著《太平記》,翻譯并創作了漢文章回演義小說《太平記演義》,開創了日本漢文講史小說的先河。岡島冠山的門人守山祐弘在為《太平記演義》作序時說:“吾師玉成(按:玉成為岡島冠山之字)先生,同鄉長崎人也。少交華客,且從先師祖上野先生,而習學華語,已自悟入其妙境。于貫中二書(按:指《三國志演義》、《水滸傳》),通念曉析,無所不解。其余《西游記》、《西廂記》、《英烈傳》等諸家演義小說,亦皆搜抉無隱”⑩。依田百川(1833-1888)是漢文小說《譚海》和《談叢》的作者,其友人菊池純在《譚海·序》中談及中國小說對依田創作《譚海》的影響,其云:“友人依田學海(按:學海為依田百川之號)君,消夏避暑之暇,記述近古文豪武杰、佳人吉士之傳,與夫俳優名妓俠客武夫之事行,存于口碑,傳于野乘者若干篇,裒然成冊,題曰‘譚海’,蓋擬諸西人所著《如是我聞》、《聊齋志異》、《野談隨錄》等諸書,別出一家手眼者”。而依田百川在《自傳》中談及自己的學術傳統時,則特別提到了自己對《金瓶梅》、《水滸傳》等中國通俗小說的喜愛:“作文章,推韓非、蘇洵、魏禧,最喜敘事,文不甚鍛煉,而一氣貫注,自言有氣力。詩尚杜韓,好作五古,欲擬六朝,不及也。又嗜和漢小說,如《金瓶》、《水滸》、《三鏡》、《源語》,略通大意”。從依田能夠寫出《潭海》這樣的漢文小說巨作,這里的所謂“略通大意”云云,不妨視為依田自己的謙遜之語。
在日本漢文小說的創作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特別的現象,即某一部中國小說由于深受日本讀者的歡迎,以致在日本出現了一系列仿作。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世說新語》的仿作。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記載,《世說新語》一書早在平安時代就已傳入日本。江戶時期的元祿七年(1694),日本刊行了明萬歷十三年(1585)刊行的《世說新語》(王世貞序、李卓吾評點、張文圭刻本),這是日本較早有史料記載的關于翻印《世說新語》的情況。由于有了本土的翻印刻本,《世說》具備了進一步流傳開來的條件。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了模仿《世說》的系列作品——服部元喬(1682-1758)的《大東世語》、林榴岡(1681-1758)的《本朝世說》(未出版)以及角田九華(1784-1855)的《近世叢語》等。這些仿作不僅在書名上與《世說》類似,而且在體例編排上,也幾與《世說》相同。《大東世語》全書分上下二冊,所收錄的354則故事,被分別納入“德行、言語、政事”等31個門類中,與《世說》相比,僅少了“自新”、“儉嗇”、“汰侈”、“讒險”、“惑溺”五門,其體例幾乎完全襲自《世說》,對此作者自己并不諱言,明謂之為“姑假臨川氏標目,選次附之”,并且強調不設“自新”等五門的原因是“本因事而附標,不援標而選事,故亡者闕焉”。
另一被日本作家熱衷模仿的作品是清代張潮的《虞初新志》。虞初本為武帝時方士,班固《漢書·藝文志》謂其作有《虞初周說》943篇。唐代以后,時有文人墨客以“虞初”為名,編輯小說。如唐代有無名氏的《虞初志》,明代有湯顯祖編輯并評點的《續虞初志》,清代有張潮的《虞初新志》、黃承增的《廣虞初新志》、鄭澍若的《虞初續志》等。據張潮《自序》云,《虞初新志》編成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是一部裒集了作者自認為可以“怡神”、“豁目”的當代傳奇、志怪、游記、寓言、隨筆的文集。《虞初新志》是在何時傳入日本,現無確切考證,但在日本天明四年(1784)由秋水主人為“初讀舶來小說者”所編的中國俗語辭典《小說字匯》所征引的作品中,就已有該書之名,由此可以推斷該書傳入日本的時間當不晚于18世紀中葉。而現可看到的《虞初新志》在日本較早的完整刻本是文政六年(1828)由浪華河內書局刻印的版本。《虞初新志》在日本也擁有眾多讀者,并在明治初年,相繼出現仿作。由近藤元弘編輯的《日本虞初新志》,成書于明治四年(1871),并于十四年付梓。編者在其以南崧樵史之名寫作的《凡例》中談到了自己編輯此書的初衷,云:“樵史性多奇癖,故每逢異書奇傳,輒為購求借覽焉。常讀清張山來《虞初新志》及鄭醒愚(按:醒愚為鄭澍若之號)《虞初續志》,反復不措,頗有所會意也。然事皆系于西土,至本朝,未見有如此者,豈不一大憾事乎!于是就本朝名家集中,遇山來所謂‘凡可喜、可愕、可譏、可泣之事’,則隨讀隨抄,汲汲不倦,積年之久,漸得數十篇矣。”同時又對所起書名作了如許說明:“山來曰:‘虞初為漢武帝時小吏,衣黃乘輜,采訪天下異聞。以是名書,亦猶志怪之軼即《齊諧》以為名。集異之書,本《夷堅》而著號。’故樵史亦以名斯書,蓋擬山來編纂之意也”。在《日本虞初新志》出版兩年后的明治十六年(1883),又有菊池純(1819-1891)的《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志》出版。不過作者在《凡例》中強調,此書在十年前就已完成,原稿十卷,題作《消夏雜記》,明治十六年出版時,抄為三卷,改名為《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志》。雖然作者特別指出改名純粹是因為“從書賈所好”,并言此書悉出自己“一手筆墨”,不同于張山來《虞初新志》“裒集諸家之文字”,但其友人依田百川在《序》中依然指出菊池純的寫作緣起正是受到了張山來的影響:“(先生)頃讀張山來《虞初新志》,意有所感,乃遍涉群書,博纂異聞,體仿前人,文出自己,釐為若干卷”。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漢文小說的興起和繁榮,與日本長期以來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接受分不開,而江戶時代中國小說的大量輸入,則直接激發了日本作者創作漢文小說的熱情,從而興起了一輪日本漢文小說創作的熱潮。
二、日本漢文小說家的小說觀念
日本漢文小說家的小說觀念深受中國影響。在中國,寫小說而摒棄虛構,是由來已久的觀念。早在漢代,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就從史家的角度強調了小說“綴而不忘”的實錄特點。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把小說看成史著的“外傳”和附庸,反對“虛辭”,并據此而批評郭子橫的《洞冥記》和王子年的《拾遺記》“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清代紀昀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要求小說保持“博采旁搜”的“古制”,真實記錄,反對虛構,并從這一立場出發,把《聊齋志異》這類描寫“細微曲折,摹繪如生”的作品斥為“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而不予著錄。
隨著明清兩代小說創作的繁榮,在小說批評界和創作界也逐漸出現了肯定虛構的聲音。胡應麟認為,唐傳奇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盡設幻語”、“作意好奇”、“紀述多虛”,而非像六朝小說,“傳錄舛訛”,或像宋人小說,“論次多實”。謝肇淛認為:“凡為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為游戲三味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馮夢龍則強調小說創作可以“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麗其人”,因為“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亦真”也。
日本漢文小說家在小說的虛實問題上,也同樣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而主張小說“據實直書”、摒棄虛構是其主流。川田剛在評論依田百川的《譚海》時,將它視為據實結撰的力作而予以標舉,并將之與狀寫牛鬼蛇神、花妖狐魅的一批中國小說如《聊齋志異》、《夜談隨錄》、《如是我聞》、《子不語》等對立起來,貶斥這些小說為“架空”而談,“率皆鄙猥荒誕,徒亂耳目”。而依田百川本人對這種觀點也是認可的。他在為菊池純的《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志·凡例》作批點時曾議論說:“仆讀西土(按:指中國)人雜著,不獨《子不語》、《志異》諸書,乃如純儒紀曉嵐、王子正諸氏,全篇鬼談怪語,居其七八,間有忠義賢奸事跡,可喜可驚之談,反使人疑為架空小說。先生此著,雖聞見過敷張者,絕無涉怪誕不稽,其識見大有超前人矣”。如前所言,紀曉嵐于小說是排斥虛構之詞的,但他所排斥的虛構,是作者“細微曲折、摹繪如生”的想象描寫,而非關乎“鬼談怪語”一類非現實的故事——事實上,他的《閱微草堂筆記》敘述的就是以“鬼談怪語”為主的故事,而這類故事也一直是中國古代小說的傳統題材。對于中國古代小說家而言,寫“鬼談怪語”的故事,自有其不同的目的和審美取向。對于魏晉六朝的作者,他們身處巫鬼神仙之風盛行的時代,其輯錄此類故事,除了有“游心寓目”的一面,更重要的是為了“發明神道之不誣”;而于紀曉嵐,其寫“鬼談怪語”,除了有“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的一面,更多的是著意勸懲,借此而指摘人事,揭橥世情。日本漢文小說家依田百川及評論家川田剛在如何對待“鬼談怪語”這類非現實題材的小說上顯然比紀曉嵐狹隘,他們只欣賞和肯定那些“絕無涉怪誕不稽”的作品,而把描寫“鬼談怪語”的小說一概視為“架空”而予以了否定。
與依田百川、川田剛相似,《日本虞初新志》的作者也強調自己的編選原則重在“實錄”,他在署名為南崧樵史的《凡例五則》中說,自己受張山來的《虞初新志》和鄭醒愚的《虞初續志》的影響,在小說篇目的選擇上,多著眼于“可喜、可愕、可譏、可泣之事”,也就是著重選擇那些記述了容易引起讀者強烈情感共鳴的故事,但他又不是完全囿于《虞初新志》和《虞初續志》的選擇范圍,而是有所揚棄——“如狐貍之妖、厲鬼之怪”,因“本邦文士概視以為荒誕不經之事”,所以“曾不上之筆端,故其所選,多屬實錄”。南崧樵史也有尚奇的一面,其云:“樵史選斯書,有名家文而不取者焉,蓋以所記之事不奇也;有不名家而收之者焉,蓋以所敘之跡可傳也。”但這種“奇”不是“鬼談怪語”式的奇,而是基于現實基礎上的凡人的“奇節偉行”。
主張“據實直書”的日本漢文小說家和批評家們雖然排斥“架空”一類的“鬼談怪語”,但是他們對于作者基于現實基礎上的虛構性描寫,卻是持肯定態度的。依田百川在《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志·序》中說:
太史公以驚天動地之才,奮翻江攪海之筆,其《史記》數十萬言,可驚可喜可泣可笑,莫不極天下之壯觀焉,而其人則圣賢豪杰,大奸巨猾,婦人孺子;其事則禮樂刑政,戰斗言論,滑稽伎藝;凡人間所有,洪纖畢備,巨細無遺。嗚呼,何其奇也!或以為史公之文奇矣,然非六國爭強之戰、劉項斗智之亂,及游俠刺客日者龜冊之奇,雖有史公之筆,何以肆其力、逞其才哉。不知史公未下筆之前,胸中早已有一部《史記》。其所謂圣賢豪杰、禮樂刑政,不過借以發胸中之蘊蓄、放筆端之光芒。故其于事也,或增或削,或點染生色,或夸張成勢,訂之經傳,有抵牾不合者。則知有文章,然后為事跡;非有事跡,然后有文章也。
依田百川認為,《史記》之所以影響非凡,并非如一般人所云,是因為司馬遷所描寫的那個風云變幻、英雄輩出的時代使“史公之筆”有了英雄用武之地,而是因為司馬遷在下筆之前,胸中早已有了一部《史記》,他所描寫和敘述的現實生活——“圣賢豪杰、禮樂刑政”,都已不是簡單地對現實的再現或模仿,而是經過了自我價值情感的燭照和滲透,即所謂“發胸中之蘊蓄”也。如此,則必然地會在行文中存在“或增或削,或點染生色,或夸張成勢”的問題,而這正是在現實基礎上的合理虛構。依田百川對于菊池純“寫偉人杰士,則電掣雷激;寫妓女艷婦,則花笑鳥啼;寫妖怪鬼神,則梟嘯鴟號。極力刻畫,活動如生,可謂化工肖物之手”的藝術表現力極為贊賞,并以《史記》的合理虛構和夸張來駁斥人們對于菊池純的質疑:“或疑其紀事與史傳有異同,又夸張甚過,不得其實。嗚呼!是因然。且不見《史記》鴻門會乎?數百衛士,不敵一噲;斗酒彘肴,殆同戲劇。又不見《張良傳》乎?赤松黃石,巧成對偶;圯上授書,事涉神怪。是史公胸中之《史記》,特借舞陽留侯以成其奇者也。”依田百川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即使是作為有實錄要求的歷史著作《史記》,它在對歷史事件進行敘述時,也難免夸張和渲染,而正是這種夸張和渲染,成就了《史記》,也成就了司馬遷“特借舞陽留侯以成其奇”的雄心和理想。由此而看,依田百川“據實直書”的主張雖然在否定“鬼談怪語”這類非現實題材的小說上比紀曉嵐顯得狹隘,但是在描寫和敘述現實題材時允許和贊賞虛構,卻又比紀曉嵐顯得通達許多。
《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志》的作者菊池純在小說的虛實問題上與依田百川的主張基本相同。其在《凡例六則》中說:“此篇仿蒲留仙《聊齋志異》之體,然彼多說鬼狐,此則據實結撰,要寓勸懲于筆墨,以為讀者炯戒而已。然至其欣然走筆,會心得意不可抑遏,不能悉據實。實中說虛,虛中存實,讀者試猜孰是實,孰是假,孰是根據,孰是演義,又是一樂事”。菊池純明言自己雖然體仿《聊齋志異》,但僅是模仿其體制結構以及描摹的細膩以至于“欣然走筆”而已,其“不能悉據實”的“實中說虛,虛中存實”,指的是不排斥基于現實基礎上的人情物理的細節性虛構,屬于《聊齋志異》式的“細微曲折,摹繪如生”的范疇,但是,菊池純一樣否定《聊齋志異》的“多說鬼狐”,明確標榜自己的作品是“據實結撰”,反對寫子虛烏有的牛鬼蛇神。
在日本漢文小說家關于虛實問題的爭論中,當然并非一邊倒的“挺實”主張,也有若干作者是標舉鬼談一類虛構的。《夜窗鬼談》的作者石川鴻齋就認為,世間之所以多奇談怪說,是因為“緣人情之所好而然”。正因為如此,所以即使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左氏傳經,屢載神怪”,下至韓昌黎、蘇東坡諸子,也莫不“好談神怪”、“弄幻玩假”。對于作者而言,他們當然知鬼談乃“描風鏤影”、“不可以正理論”的“游戲之筆”,若“叩其遭遇”,必然是“渺茫荒惑、無可準者”,但他們仍愿意“修其文,飾其語”,使其“絢爛偉麗,可喜可愛”。在《夜窗鬼談·凡例》中,石川開篇就明言其作“多系傳聞,其真偽固不可證”,而且還強調他在寫作過程中并非完全依據傳聞而寫——“不必如所聞”,而是“有裝飾”、“有省略”的,也就是強調了他自己對于素材所進行的重新整合,強調了他的寫作是在現實傳聞基礎上的虛構和再創造。為《東齊諧》作《序》的雪泥居士也與石川鴻齋同調,認為古人之所以“喜說鬼事”,或“莫不盡涉奇事怪談”,“益恣詭辯”,是因為用正常的言語文辭無法“窮理明義”,正是著眼于這一點,他強調即使是說鬼事,也不能陳陳相因,落于舊套,而要有所創新:“世之說鬼者,百人百種,不同其事。顧鬼亦去舊套,創新意,棄陳腐,演妙案,于是往往有出于意表者”。
與石川等人相類似的聲音,還時見于其他一些神怪類小說的序跋中。如《含餳紀事·序》的作者宮田明云:“螯足立極,蘆灰止水,周祖生巨跡,殷相出空桑,觸蠻國蝸角,古籍傳之,不以奇廢也”。這是從古籍“不以奇廢”的角度,說明談鬼述怪存在的合理性。另如《警醒鐵鞭·跋》的作者,則是從小說的審美和可以寓真于幻、針砭世事的視角,強調了“憑虛架空”作品的不可替代性。他認為這類作品不僅在敘事上“變幻離奇,縱橫出沒,使人目眩不能正視”,最重要的是它們能夠“托事寓言,發揮無數之見解”,諸如“政教兵刑、世態人情”,莫不“一一包羅之”。這樣的言論當然有拔高“憑虛架空”類小說的作用之嫌,但在強大的“挺實”主張中,我們也能理解其乃是出于為該類小說爭生存權的情懷。
日本漢文小說家除了關注小說的虛實問題,還關注小說的地位及作用問題。在古代中國,從秦漢時代起,小說就被置于九流十家之末,而小說的作用也被定格在了“致遠恐泥”的觀念中。這種狀況直至宋代才有所改變。南宋羅燁就認為小說是具有高度藝術感染力的藝術形式,它“說國賊懷奸從佞,遣愚夫等輩生嗔;說忠臣負屈銜冤,鐵心腸也須下淚。講鬼怪令羽士心寒膽戰;論閨怨遣佳人綠慘紅愁。說人頭廝挺,令羽士快心;言兩陣對圓,使雄夫壯志。談呂相青云得路,遣才人著意群書;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隱士如初學道。噇發跡話,使寒門發憤;講負心底,令奸漢包羞”。而這種藝術感染力的形成,羅燁認為是小說家合理設計情節的結果:“講論處不僀搭,不絮煩;敷演處有規模、有收拾。冷淡處提掇得有家數,熱鬧處敷演得越久長”。羅燁的論述,極大提高了小說家和小說藝術的地位。小說發展至明代,小說的社會地位及作用得到了進一步的重視。如馮夢龍在《古今小說·序》中指出:“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馮夢龍認為,通過說話藝人的表演,觀者和聽眾可以充分感受到小說藝術形象和故事情節的魅力,他們的情感會隨著故事的進展和人物跌宕起伏的命運而變化。在《警世通言·序》,馮夢龍甚至舉里中小兒因聽《三國志》關云長刮骨療毒的故事,創指而不呼其疼為例,說明這種感染力的力量,并由此而強調小說之不可為經史所替代的地位。
日本漢文小說家對于小說的重視與宋代以來小說在中國文人士子心目中的地位的提高不無關聯,這甚至從他們言說的角度和使用的術語就可看出這一點。《當世新話·序》作者半醉居士說,稗史小說所記錄的內容,都是“官史所不暇載”的“瑣事”,如果說官撰之史“可以識事業之盛,功績之宏”,那么小說會由于它記載了“孝子貞婦義仆節婢之逸事”、“巨盜騙拐妓女俳優之情狀”等,使其天然具備了“察閭巷之情態、民間之風俗”的功能,因此不能“等閑看過”。如果說,半醉居士以上言論還不能完全脫去小道亦有可觀者存焉的秦漢儒者之說的痕跡,那么半醉居士在談及小說的審美作用時,就畢肖模仿了宋明以來的小說者言的口吻。其云:小說于“披讀之間,或笑或泣,或罵或怒,其敘事精細,描景靈活,雖身臨其地而目見其狀者,未能得如此之詳也”。也就是說,半醉居士已經認識到了小說對于讀者的教育作用是通過作品的真切描繪及其對讀者的情感觸動而實現的。
與半醉居士言論相同者還有菊池純等一批小說作者。菊池純在《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志·自序》中把小說的審美作用比同于置身酷暑中的“忘暑”,其云:“暑當何如避焉?曰:清泉以濯其足,蘭湯以浴其身,蔽于茂樹,坐于竹蔭,羽扇搖風,而甘瓜浮水,是謂之避暑之良方而已。嗟乎!是謂避暑,未足為忘暑也。夫所謂避,猶有畏暑之意也,豈若忘之為最善乎?曰:吾所謂忘暑者,足未必濯寒泉也,身未必浴蘭湯也,茂樹也、竹蔭也、羽扇甘瓜之類也,亦未必設也。其所設者,一機一研一楮墨而已矣。夫酷暑困人,甚于毒藥猛獸。其中之者,精神困頓,筋懶骨弛,使人往往思華胥槐國之游,庸詎得朝經晝史,從事斯文,以磨淬其業乎哉!于是聚舉世稗官野乘,虞初小說,茍可以為排悶抒情之資者,裒然堆垛,取以置諸其架上,隨意抽讀。讀至忠仆義奴溲腸洞腹、殺身為仁之事行,毛骨深豎,令身坐于雪山冰海之上矣。又讀至孝子烈婦數奇落托、具嘗艱楚,與夫老賊巨盜詐世誤國、枉害忠良之傳奇,又令身在窮陰沍寒,凄風慘雨之中矣。流讀久之,恍乎忘炎暑之為何物矣”。雖然菊池純仍不能擺脫傳統儒家留下的諸如“忠仆義奴”、“孝子烈婦”之類的陳詞,但是他已經把關注的重點移向了小說閱讀中所引起的審美心理的變化,注意到了這種審美心理變化的強度甚至可以達到使人身處炎夏而“毛骨深豎”的地步。這與馮夢龍所舉里中小兒聽三國故事的例子正有異曲同工之處。
菊池純友人鹽谷誠在為《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志》作敘時,也強調了小說具有不可忽視的審美影響力,其云:“有忠臣孝子,為有兇奸猾賊焉;有美姬艷妾,為有姣童冶郎焉。或為爭斗刺擊,或為歡忻燕娛,忽而榮華,忽而窮愁,戲嫚淫褻之狀,幽魂怪異之變,舉世間可喜可駭、可哀可樂之事,而盡在于目前,使人笑泣交集,喜怒更發,殆忘其躬為旁觀也,文辭之感人,亦猶有如是者歟!”但在這篇敘文中,我們也看到即使是菊池純們所處的明治時代已經十分開明,人們大多已能接受并欣賞小說,但是社會上依然固執存在著由傳統延續下來的鄙視小說的聲音:“子顯(按:子顯為菊池純之字)講詩書,說仁義,其作文章,宜醇粹雅正,卓然有所自立,奈何效稗官虞初,改與風流才子爭工拙于字句間耶?”或許是迫于傳統的壓力,鹽谷誠對此采取的是頗為騎墻的態度,一方面贊賞和肯定《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志》“記怪、記情事、記忠孝節義、記寓言戲謔,殆亦使心笑泣交集,喜怒更發,耽然不能釋手”,并以元稹之作《鶯鶯傳》、李鄴侯之作《枕中記》為例,說明小說之不可廢,一方面又對那些貶斥的聲音予以妥協,以為“其言亦頗有理”,并將之“書以訊子顯”。
石川鴻齋的小說多為談鬼說怪。對于這類“描風鏤影”作品的功用,石川有自己獨特的認識。首先,他認為要想教育人,必須講究教育的方法,“從其所好導之,其感亦自速;若以所不好誘之,徒費辭而終無益爾”。而世間之人的“所好”在石川看來正是“尚喜說鬼”、“好談神怪”,因為神怪可以“使人為之自娛”,“使人悲喜驚怪”,欲罷不能。也正是由于世人有這樣的“所好”,才會出現“浦留仙著《志異》,其徒聞之,四方寄奇談;袁隨園編《新齊諧》,知己朋友,爭貽怪聞”的現象。其次,石川認為“奇談怪說”“亦自有勸懲誠意,聊足以警戒世”,所以當作者“投其所好”,“使讀者不倦”的時候,“循循然導之正路”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治時代,漢文小說家寫作漢文小說還有著一個十分實用的目的,那就是把漢文小說當作學習和提高漢語能力的工具,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有岡島冠山等人。岡島冠山的漢文小說創作多為白話體,這是他作為漢語教師身份有別于儒學作者的最大不同。他的漢文小說除了《太平記演義》外,其他作品主要見于《唐話纂要》(按:唐話即漢語白話)中。《唐話纂要》共六卷,是作者為當時的日本漢語學習者編著的漢語教材,并不全為小說。由于古代中國一直存在著書面的文言文和口語的白話文之分,而在明清時代,隨著中日兩國社會交往的日趨頻繁,對漢語口語的掌握越來越顯得重要,在難以直接到中國學習語言的情況下,利用白話小說來學習漢語口語,不失為一個較好的辦法。岡島冠山編纂收入了其白話小說作品的漢語教材《唐話纂要》,正是出于這一目的。
三、日本漢文小說的發展概貌
以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獻資料,日本最早的漢文小說作品是約產生在奈良(710-794)或平安時代早期的無名氏的《浦島子傳》。關于《浦島子傳》,日本17世紀著名儒學大師木下順庵曾有過如此評論:“右(《浦島子傳》)不知何人所作,奇文華靡,無檢束,想夫古之搢紳家學白香山而失于俗者。”由于該書“傳寫年久,其間誤字闕文,往往有不可讀而通焉”,故木下順庵在余暇之日,經過“反復考訂”,“誤者正之,闕者補之”,才最終成為“一篇文字”。《浦島子傳》在延喜二十年(920)曾出現“續書”——《續浦島子傳記》,但該“續書”并非通常意義上的接續前書、衍生他事的續寫,而只是在前書的基礎上踵事增華,其最大的改動,是在文末增加了大量詩篇——“代浦島子詠七言廿二韻”及“和歌絕句各十四首”,以及代龜媛詠和歌、絕句各四首。
《浦島子傳》后,在公元9世紀的弘仁年間(810-824)出現了一部以佛教故事為主要敘事內容的佛教說話集《日本靈異記》。該書分上、中、下三卷,共收錄了從雄略天皇至嵯峨天皇時期(5-10世紀)的116則故事,編撰者為奈良藥師寺僧人景戒。《日本靈異記》的語言多為四字句,其漢語表達帶有日語語法的特點。
《浦島子傳》和《日本靈異記》在題材上均屬志怪性質,與志人相關的軼事小說直至平安后期的12世紀初才出現。記載大江匡房的談話、由藤原實兼筆錄的《江談抄》(約1104-1111),是日本第一部類似于“世說體”的軼事小說,大體按事分類,有“公事”、“雜事”諸門。大江匡房知識淵博,歷仕后冷泉、后三條、白河、堀河、鳥羽五代天皇,官至中納言,晚年升為正二位,是日本院政時期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其談話錄《江談抄》生動記載了日本平安時代的朝野典故以及當時流行的中日詩歌逸聞。大江匡房在文學上除了擅長寫作漢詩,還擅長寫作極具小說意味的漢文體散文,有《游女記》、《傀儡記》、《狐媚記》等作品傳世。
漢文小說真正受到日本作家關注并投身其中,是進入江戶時代以后的事情。學者一般把1698年刊行的由寓居關東的摩訶阿賴耶撰的《日本七福神傳》視為這一時期漢文小說創作的發軔之作。從18世紀初的江戶時代中期至19世紀末的明治時代后期的近二百年時間里,陸續產生了一批漢文小說作品,標志著日本漢文小說創作進入了它的興盛期。從題材上看,這批漢文小說可以區分出若干大類。一是以描寫現實世情為主的小說,其中又可以再區分出若干小類,如側重描寫偉人、畸人、寒士、才女以及各色人等的奇聞軼事的,有服部元喬的《大東世語》(1750)、觀益道人的《如是我聞》(1832)、藤井淑的《當世新話》(1875)、蒲生重章的《近世偉人傳》(1878)、近藤元弘的《日本虞初新志》(1881)、菊池純的《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志》(1882)、依田百川的《譚海》(1884)、《談叢》(1899)等;側重描寫現實生活變遷的,有松本萬年的《文明余記,田舍繁昌記》(1875)、服部誠一的《東京新繁昌記》(1877)、石田魯門的《大阪繁昌記》(1878)、松本萬年的《新橋雜記》(1879)、菊池定的《南游記》(1883)、根木靜的《昭代余事》(1884)、高須墨浦的《涵館繁昌記》(1885)、岡田有邦的《新瀉繁昌記》(1885)等;側重描寫愛情、艷情及花街柳巷故事的,有金子強的《大東閨語》(1785)、檜垣真種的《浪華風流繁昌記》(1833)、成島柳北的《柳橋新志》(1874)、菊泄純的《京貓一斑》(1874)、三木貞一的《東都仙洞綺話》(1883)、《新橋八景佳話》(1883)、《仙洞美人禪》(1885)等。二是以描寫鬼神怪異為主的小說,如熊阪臺州的《含餳紀事》(1793)、藍澤祇的《啜茗談柄》(1827)、山井元行的《賢乎己》(1859)、中井履軒的《昔昔春秋》(1876)、石川鴻齋的《夜窗鬼談》(1889)、《東齊諧》(1894)等。三是以描寫歷史及英雄傳奇為主的小說,如岡島冠山的《太平記演義》(1719)、齋藤正謙的《海外異傳》(1850)、巖垣月洲的《西征快心編》(1857)、勢多章之的《碧血余痕》(1887)等。
20世紀初的明治末期至大正(1912-1925)及昭和(1926-1988)前期是日本漢文小說的衰落期。衰落的主要原因來自于兩個方面。首先是明治維新以來全面實行的歐化主義此時已得到了較充分的消化和吸收,出現了一批具有影響的以探索新文學創作方法為目標的理論家和作家,如二葉亭四迷、森歐外、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等,他們的存在,充分彰顯了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開啟的新文化運動的實績,克服了早期對西方文化生吞活剝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如依田百川所抨擊的:“時文學盛行,少年才子,著稗史小說,根據洋說,多鄙俚淫靡語”,從而在很大程度獲得了讀者的認可、接受和欣賞;其次是日本在明治五年(1872)、明治十二年(1879)分別制定和頒布了在日本教育史上影響重大深遠的《學制》和《教育令》,在學校組織和教學內容兩方面全面參照和效法西學,在此教育體制下,以漢學為基本內核的舊教育體制,則被視為陳規陋習而受到了排斥和鄙棄,關于這一點,在大修為依田百川的《談叢》所作的《引》文中有直接的反映,其云“近來國字改良論起焉,國語調查會置焉,逐時趨勢之徒,直把漢文為漫為縟,甚則欲廢棄之”,“世人視漢文如土芥”。據日本歷史學家阪本太郎研究,“明治四年(1871)左右,在東京的知識分子中,國學(按:指日本學)只有漢學的1/10,而漢學只有洋學的一半”。如果說,在江戶時代曾經全面盛行的漢文教育到了明治初年已經是風雨飄搖,但仍不乏影響,那么當歷史邁入到20世紀的門檻,那些曾經占據著知識分子半壁江山的漢學家們,很多或已作古,或已進入耄耋之年,在新的漢語人才難以培養產生的環境下,漢文小說創作難以為繼就是必然之勢。因此,這一階段的漢文小說作品寥若晨星,不但稀少,而且質量也難稱上乘。大略只有三木造的《西湖折柳》(1902)、釋宗演的《降魔日史》(1904)、大田道軒的《警醒集》(1905)、藤澤南岳的《游屐余痕》(1907)、菊池三九郎的《談欛》(1908)、廣田直三郎的《寒燈夜話》(1915)、信太英的《淞北夜譚》(1927)等不多的幾部。
江戶時代漢文教育的普及以及中國小說的大量傳入,直接對日本的漢文學創作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從此,日本的漢文學創作不再是江戶時代以前的漢詩文一統天下的局面,漢文小說異軍突起,在日本漢文學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從事漢文學創作的主體也不再是由皇室、公卿貴族、高級僧侶及上層文人所把持,而是表現出了明顯的平民化色彩。就漢文小說家的基本構成而言,其主要成分是文人知識分子。與江戶時代前的漢文作家相比,他們一般都沒有顯赫的官職,大多是以下帷講學、著書立說謀生,其地位較高者也僅是作為藩侯儒官或幕府將軍侍講的身份出現。日本漢文小說家不僅在語言及小說形式上接受了中國小說的影響,而且在小說觀念上,也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可以說,明清以來在中國小說界探討的主要問題,在日本漢文小說家那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響。從整體上看,日本漢文小說家大多倡導寫實,主張據實結纂,提倡寫生活中的奇人畸行。他們不反對在寫實基礎上的虛構和夸張,但卻不主張寫憑虛架空的怪力亂神。當然,日本漢文小說家中也不乏談異述怪者,但這種談異述怪已不是為了明神道之不誣,更不是為了聳人聽聞,而是為了在詼諧娛樂的同時更好地傳達作者的道德意識,以達到勸善懲惡的結果。
注:
② 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召請有“近世儒學之祖”之稱的藤原惺窩講授朱子學,并且起用藤原弟子林羅山為大學頭,主持學問所;第五代將軍綱吉在幕府設儒官,并親自講解《論語》;第八代將軍吉宗,令人將傳自琉球的《六諭衍義》加以注釋訓解,使之普及民間,同時將康熙的《圣諭十六條》以《圣諭廣訓》之名頒布。
③ 荻生徂徠(1666-1728),日本江戶中期著名儒學家,晚年曾擔任幕府將軍德川吉宗的顧問。正德元年(1711)荻生徂徠成立教授漢語的“譯社”,并編寫了漢語教材《譯荃初編》。
④ 如平安時代著名高僧空海作有《相府文庭始讀〈世說新語〉詩》,并贈與文章博士菅原清公;《萬葉集》所收錄的遣唐使少錄山上憶良的作品,明顯留有模仿《游仙窟》的痕跡;《萬葉集》的編纂者大伴家持在題為《贈坂上大娘歌》一組十五首艷歌中,有四首以《游仙窟》為題旨。
⑤ 參見王三慶《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王序》,《日本漢文小說叢刊》(以下簡稱《叢刊》)第1輯第1冊,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6頁。
⑥ 轉引自李樹果《日本讀本小說與明清小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頁。
⑦ 在禪僧景徐周麟的《翰林葫蘆集》第三卷,載有題為《讀〈鑒湖夜泛記〉》詩一首,作詩的年代約在日本文明十四年(1482),而《鑒湖夜泛記》乃《剪燈新話》卷四所收詩歌,由此推斷,《剪燈新話》應在15世紀末就已經傳入日本。參見李樹果《日本讀本小說與明清小說》,第8頁。
⑧ 楊彬《中國古代小說在日本的流播與日本古代漢文小說的考察研究》(博士后研究報告),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2005年,第57頁。
⑨ [日]皆川淇園《通俗平妖傳》日譯本《序》(1797),轉引自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頁。
⑩ [日]守山祐弘《太平記演義·序》,《叢刊》第1輯第4冊,第2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