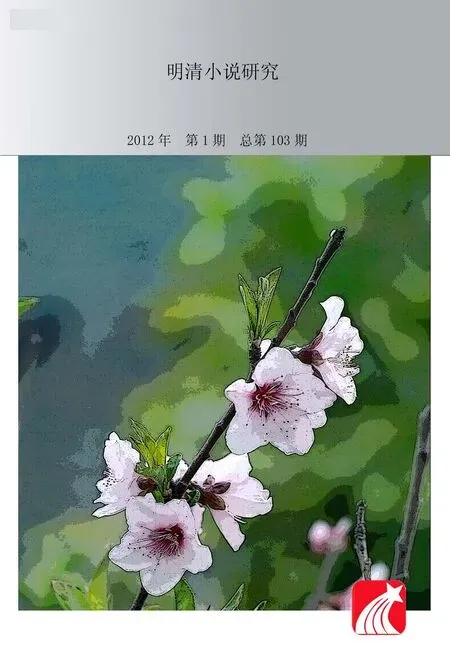論《說岳全傳》傳播與接受的價值取向
··
《說岳全傳》是岳飛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在民間傳播非常廣泛,在民眾中的影響很大,不只這部小說文本曾暢銷一時,而且還被改編成戲曲、說唱、電影等形式,在舞臺上盛演不衰。但作為民間系統的通俗小說,很長時間以來學者們似乎都忽略或誤解了這本小說,很少有正式論文談到它,某些小文章提到它時,也多是簡短的雜談。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學者們對它才能采取較寬廣的角度來分析探討,之后隨著文學理論視野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學者從多方面角度去評析這部小說,對他的評價越來越趨向于理性、客觀,它的價值也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肯定。總體而言,在《說岳全傳》的傳播接受史上,由于社會政治背景、文化思潮的變化及傳播者、接受者知識結構、道德觀等的不同,對其價值取向也呈現出不同的態度。較多的論者和讀者肯定了它的審美藝術價值、思想價值等方面。也有部分論者持否定的態度,否定其價值主要是著眼于其封建忠君思想及因果報應、封建迷信的描寫等方面。本文擬對《說岳全傳》的價值取向進行歸納總結并初步分析其產生的原因,以期更好地把握和實現《說岳全傳》的多重價值。
一、審美藝術價值
《說岳全傳》的審美藝術價值主要包括虛實關系、人物刻畫、敘事結構、悲劇價值等方面。最早肯定《說岳全傳》審美藝術價值的當屬鄭振鐸。1929年鄭振鐸于《文學周報》發表《岳傳的演化》①一文,文中認為《說岳》是所有早期岳傳的總結束,也是一部最完善的精忠傳,又引金豐的序“從來創說者,不宜盡出于虛,而亦不必盡由于實。茍事事皆虛,則過于誕妄,而無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實,則失于平庸,而無以動一時之聽”,認為“直是道破了一切歷史小說與英雄傳奇的關鍵”,《說岳全傳》比之前熊大木的《武穆演義》、于華玉的《盡忠報國傳》更為“荒誕”,“這乃是自然的進展”、“民間的需要”,“一切傳奇都不能不走到這條路上去。不荒誕便不成其為‘傳奇’,不荒誕便不能為民間讀者所深喜”,肯定了《說岳全傳》虛構情節、加強傳奇色彩的寫法,同時認為其內容也自有其好處,比前幾部小說敘述更詳盡深入,描寫更生動活潑,格外動人,盡管文章最后鄭振鐸把《說岳》與其它小說作比較,認為《說岳》的文字“頗平庸,不大耐得吟味,與諸本《說岳傳》較之,固然是高出,若置之于《水滸》、《紅樓》之列,卻頗有些‘自慚形穢’”。只就文字技巧評論《說岳全傳》的地位并不能提供一個明確而公允的論定,但鄭振鐸這篇文章首次探討并肯定了《說岳全傳》的審美藝術價值,向人們介紹了《說岳全傳》是一本值得重視的通俗小說。
1956年李厚基在《文學遺產》發表《讀〈說岳全傳〉》②一文,詳細分析了《說岳全傳》中的人物形象。李厚基認為“對于岳飛,作者自己除了表示驚奇、崇敬和贊嘆以外就沒有別的,他努力通過藝術上所特有的夸張手法把內心中對于這樣一個巍峨的英雄形象的感情,全部表達出來”,把岳飛塑造成“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正是由于作者對岳飛的“過分神化”以及“一個封建社會中的英雄人物在所難免的”原因,使得岳飛的形象也“不是完整無缺的”。而牛皋,李厚基認為作者沒有抽象地加以夸張,“這倒反使他自然可愛”,為廣大讀者所喜愛。李厚基也指出《說岳全傳》塑造人物的缺點:“《說岳》仍不能擺脫普通章回小說的窠臼:它著重追求情節的曲折離奇而忽略人物性格的描寫;因此,其它人物(即岳飛、牛皋、王佐、兀術、張邦昌、秦檜等除外的次要角色)就顯得一般化。這正是比《三國》、《水滸》、《西游》頗為遜色的地方。”李厚基的這篇文章從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對《說岳全傳》的藝術價值進行了適度客觀的評定。
除李厚基的《讀〈說岳全傳〉》之外,五六十年代還有不少文學史、小說史及專論談到《說岳全傳》,這一時期由于時代的原因在論述《說岳全傳》時,重點都在所體現的愛國主義思想方面,在分析人物形象時也多強調其愛國主義方面。但這時學者對《說岳全傳》已較能采取寬廣的角度探討,對其審美藝術價值也多有肯定。如北京大學編撰的《中國小說史》,以專論的方式詳析了《說岳全傳》中某些重要的情節內容,最后總括地評論云:“在藝術上,它克服了明代說岳演義普遍存在的生搬歷史事實的毛病,本著‘不宜盡出于虛,而亦不必盡由于實’的態度,廣泛汲取元明戲曲小說與民間說唱中的故事,進行了大膽的再創造……小說情節曲折,故事性強……作者吸收了民間講唱文學的成果,大量運用‘市語’,語言通俗曉暢而又鮮明生動”③。從《說岳》的寫作態度、方法、語言等方面肯定了其藝術價值。
二十世紀80年代之后,《說岳全傳》研究的角度與內容呈現多元化傾向,對其價值的評判也趨向理性客觀。1983年李時人的《關于〈說岳全傳〉》④一文從內容結構、創作方法、形象塑造及語言運用等方面詳細分析了《說岳全傳》的審美藝術價值。李時人說“《說岳》以岳飛的一生經歷為線索,以一個充滿矛盾和斗爭的亂世為背景,譜寫出一曲悲壯的英雄史詩”。對于《說岳全傳》虛實相生的創作手法,李時人說:“歷史文學作品都是根據作家的某種認識去再現歷史生活的,滲透著作家對歷史生活的理解,寄寓著作家的理想和愿望,因此,所有的改編加工和虛構都是藝術手段,從根本上說是為了塑造人物、突出主題。”他認為《說岳全傳》不拘泥于歷史事實的具體細節,注意藝術創造加工,使岳飛抗金故事完整生動,使岳飛由一個歷史人物上升為有血有肉的藝術形象,“整個作品波瀾起伏、跌宕多姿,十分引人入勝,藝術上頗有一些特色”。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李時人認為“《說岳》比較善于寫人物。作品著力塑造英雄岳飛,既使用神話、傳奇的手法,又注意現實和具體的描寫……多方面揭示他的高貴品質和內心世界”。另外牛皋、王佐、岳云以及秦檜、金兀術等反面形象也寫得比較生動。在語言運用方面,李時人也加以肯定:“《說岳》采用的是民間說書用的通俗藝術語言,這種語言,既適合濃墨巨筆的粗線條勾勒,又適合細膩委婉的細節刻畫,使作品通暢流走,明白如話。”李時人還肯定了《說岳全傳》善于描寫戰爭,“能因時因地寫出每場戰斗的特色”。對于《說岳全傳》善于寫戰爭,陳維仁在《漫評<說岳全傳>》中也加以肯定:“書里正面描寫戰爭的情節占了大半篇章……都寫得十分精彩。有大的戰爭場面的勾勒,也有在激戰中的許多細節刻劃,既波瀾壯闊、熱鬧紛繁,又形象生動、妙趣橫生。”⑤
1992年出版的顧歆藝的《楊家將與岳家軍系列小說》也對《說岳全傳》進行了比較詳盡的分析,探討了其多方面的價值。顧歆藝認為《說岳全傳》脈絡清晰、結構完整、重點突出,同時又情節曲折,故事性很強,很多情節寫得扣人心弦、引人入勝。人物形象典型生動,特別是英雄形象讓人久久難以忘懷。語言相當純熟流暢,且新鮮活潑,具有民間傳說的神奇色彩。顧歆藝還運用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理論肯定了《說岳全傳》虛實相生的創作方法,認為藝術真實不同于歷史真實,只要有利于主題思想的表達都是可以虛構的,“《說岳全傳》是將史實傳奇化了”⑥。顧歆藝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肯定了《說岳全傳》的審美藝術價值,認為《說岳全傳》在英雄傳奇小說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許多論者注意到牛皋的喜劇形象及反面人物金兀術,從多方面探討了他們的審美意蘊和藝術價值。羅書華的《中國傳奇喜劇英雄生成考辨》⑦認為《說岳全傳》成功地把牛皋從之前說岳故事里一員沒有突出特點的將領改造或者創造成了一個生氣盎然、人皆喜愛的喜劇英雄。趙文光在《古典歷史小說“魯莽”英雄形象特征及美學意蘊》⑧中更是認為《說岳全傳》之所以具有很強的閱讀性和吸引力,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書中所具有的“喜劇容量”。而牛皋的“魯莽”英雄形象正是這喜劇容量的載體。牛皋是小說中最為活躍的人物,而且更符合普通勞動人民的審美心理和趣味,所以深得人們的喜歡。文章還進一步分析了包括牛皋在內的“魯莽”英雄形象所蘊含的豐富的美學意蘊:“率直、真誠的人生追求,扶危救困的俠義精神、樂觀忘憂的人生理念、威武剛直的英雄理想。”孫長明、許海麗的《牛皋福將形象的成因初探》⑨中認為牛皋的形象“貼近生活、貼近人民”,“具有一定的反叛性”,“在民間具有極強的生命力”,而且牛皋的形象,“不僅活躍了情節,而且豐富了人物的類型,因此對小說結構起到了一種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因此提高了小說的欣賞價值,從而使讀者獲得全方位的審美樂趣”。王立、馮立嵩在《忠奸觀念與反面人物形象塑造》⑩一文中專門討論了金兀術的“俠義”性格,認為“金兀術具有既令人憎又有令人敬的矛盾性,充滿了多樣性的魅力”,“金兀術身上靈活多樣地寄托了各階層人們對忠、對奸、對敵、對友的正確評判的道德理想”。
也有許多論者專門從《說岳全傳》蘊含的悲劇意蘊方面揭示其審美價值,李長江的《淺析〈說岳全傳〉中岳飛的悲劇形象》認為“《說岳全傳》塑造的岳飛形象,以其剛烈執直的個性付出了英年早逝的代價,演出了一幕震撼人心的千古悲劇”。強金國在《論〈說岳全傳〉和〈楊家府演義〉的忠奸斗爭主題》中認為岳飛的愚忠“使忠奸斗爭以忠的一方徹底失敗而告終,從而給他精忠報國的一生涂上了濃厚的悲劇色彩”;“以大鵬與女士蝠、蛟精的故事來解釋岳飛和秦檜之間的斗爭,末回以大鵬歸位來結束全文的安排,曲折地表達了作者以及讀者的一種無法釋懷的情結,借用因果關系,將歷史和人生化為一種無可奈何的,卻又是可以理解的模式,透露出一定的悲劇氣氛”。
二、思想價值
《說岳全傳》的思想價值是研究者和讀者討論最多的問題。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論者在談到《說岳全傳》時特別強調其思想價值。復旦大學中文系1959年編寫的《中國文學史》這樣寫到“《說岳全傳》具有很高的思想和藝術價值”,“這部作品,通過民族英雄岳飛率兵抗敵,樹立戰功一直到風波亭被害、伸冤雪恨的故事,歌頌了堅決抗戰、熱愛祖國的民族英雄岳飛,同時也嚴厲的抨擊了妥協退讓、賣國求榮的趙宋統治階級和漢奸”,“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時代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真實情況,以崇高的愛國主義思想貫穿全書”;在分析岳飛形象時特別強調:“作者突出了岳飛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強調了體現在岳飛身上的中國人民抵抗侵略者的堅強信心與英雄氣概。”最后總結到《說岳全傳》在“人民文學歷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62年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在談到作者的創作指導思想時說“《說岳全傳》在表現愛國主義的民族思想方面,較之《水滸后傳》更加集中和突出”,“這在清朝統治極端嚴酷的時期,編者勇敢地刊布這種高度表現愛國主義思想的作品,是值得贊揚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1955級《中國小說史》:“小說以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飛一生的奮戰為中心,寫出了趙宋統治階級腐朽媚敵,外族統治者屢犯中原,人民英勇抵抗,這就使作品具有較高的思想意義”。在談到岳飛時也是強調其愛國主義方面,“他的反抗侵略的一生,他的精忠報國的精神,永遠留在人民心中,岳飛在人民中間也就成了愛國主義精神的化身”。類似的論述在當時還有許多,如成柏泉的《談談〈說岳全傳〉》、海燕的《對〈談談說岳全傳〉的意見》、王延齡的《怎樣評價〈說岳全傳〉》等,這些文章大都篇幅短小,多為隨筆性的讀書札記,論述的重點都是《說岳全傳》英雄形象的塑造和體現出來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盡管由于時代的原因,這時在肯定《說岳全傳》的思想價值時觀點有時不免偏激,但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比較多的學者關注到了《說岳全傳》,并進而采取較寬廣的角度進行分析探討。
李時人的《關于〈說岳全傳〉》在詳細分析其審美藝術價值的同時也強調了它的思想價值:“《說岳全傳》有明顯的民族意識,有悼念愛國志士,譴責漢奸賣國賊的用意”,“作者所要表彰的是岳飛的精忠報國,所要鞭撻的是秦檜的奸佞賣國,所要揭露的是兀術的橫暴侵略,而在這其中,小說又重點突出了對岳飛精忠報國的歌頌”,“《說岳》的思想內容,雖然包含一定的封建因素,但其主要傾向是愛國主義的,有歷史的積極意義”。
1980年馮英子在《重讀〈說岳全傳〉》一文中更是著重強調其思想價值:“宣傳了愛國主義精神,描寫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在侵略者面前百折不撓,九死靡悔的斗爭史實,使人感動,使人振奮,使人看到了我們民族的希望。”甚至認為“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這一點上,比有些理論文章更有說服力,更能收到效果”。陳維仁在《漫評〈說岳全傳〉》中也認為《說岳全傳》是“形象化的愛國主義教科書”,并進一步分析岳飛的形象:“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岳飛,是以愛國主義情操構成他靈魂的核心和精神的基石的”,“忠于祖國、忠于民族、忠于人民的一面,永遠放射著熠熠異彩,光耀人間”。
顧歆藝在《楊家將及岳家軍系列小說》中對《說岳全傳》的思想價值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為《說岳全傳》之所以在小說史上有一席之地,“主要還在于其感人的思想性”;“其中寄托著人民群眾對歷史是非曲直的公斷和火熱的情感”,“是借民族英雄的事跡,歌頌愛國主義精神,表達人民抗敵御侮、保衛家園的美好愿望”,同時“將忠與奸的斗爭緊密聯系抗戰與投降、愛國與賣國來寫,以賣國投降派作為民族英雄的反襯,以激烈的忠奸斗爭作為民族斗爭的一個側面,與之相輔相承,在鞭撻漢奸賣國賊的同時,突出抗戰的艱難及英雄精神的可貴”。
齊裕焜在《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英雄傳奇小說”部分中總結概括的《說岳全傳》的思想價值最具有代表性:“忠與奸、愛國與賣國、抗戰與投降是貫穿全書的主線,這樣就使全書愛憎強烈、營壘分明,突出了‘岳武穆之忠,秦檜之奸,兀術之橫’。歌頌愛國、抗戰的民族英雄,鞭撻賣國求榮的漢奸賣國賊,揭露了侵略者的橫暴殘酷,使作品具有較高的思想價值。”
《說岳全傳》成書后被改編為大量的戲曲、民間說唱等文藝形式,在民眾中間廣泛傳播,在歷代《說岳全傳》的戲曲、說唱改編中,表達的最明確最突出的主題就是反抗侵略、鞭撻權奸、精忠報國的愛國主義精神。舞臺上暢演不衰的經典曲目有《挑滑車》、《八大錘》、《朱仙鎮》、《槍挑小梁王》、《潞安州》、《戰金山》、《瘋僧掃秦》、《胡迪罵閻》等等。抗日戰爭時期,戲曲工作者更是根據抗戰形勢改編了許多宣揚抵抗侵略、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情感的岳飛戲。《說岳全傳》所表達的這種抵抗外侮、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精神正是其數百年來激勵、教育民眾,在民間盛行不衰的最重要原因。
三、關于負面價值問題
對《說岳全傳》負面價值的認定,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岳飛的忠君思想和封建倫理觀念,二是因果報應、封建迷信的描寫。復旦大學中文系1959年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在分析了《說岳全傳》的思想和藝術價值之后指出:“在岳飛身上也體現了忠君甚于忠國的迂腐觀念”,“把封建意識與愛國思想的矛盾,用忠孝不能兩全的荒謬論調做了歪曲性的解釋”,“這些都嚴重的損害了作品的思想價值”。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說岳飛“思想中還存在著封建道德和忠君思想”,這使岳飛形象的塑造“不能夠獲得更高更典型的意義”,“因果報應的思想,使作者把宋、金斗爭,岳飛、秦檜的斗爭看成是冤冤相報,前生注定的。宿命論的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蔽了外族侵略者的兇殘本質,開脫了宋朝統治者的罪行”。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在分析岳飛形象時說“作者筆下的民族英雄依然帶有嚴重的封建思想,岳飛的愚忠、愚孝、愚仁都十分突出”;“作者把岳飛與權奸強寇的矛盾,歸結為大鵬鳥、赤須龍、女士蝠之間的冤冤相報,這不僅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而且宣揚了因果報應的迷信思想”。這些都是首先肯定了《說岳全傳》的愛國主義的主題及其價值,然后指出其負面價值方面。
1983年李時人的《讀〈說岳全傳〉》在肯定了岳飛的愛國主義精神之后又比較詳細地分析了岳飛的忠君:“《說岳》寫岳飛之忠,又特別強調了岳飛的忠君,岳飛的忠君幾乎達到了愚忠的地步。書中又多次大談‘忠孝節義’等封建倫理,這些都嚴重的削弱了全書的進步思想傾向”,“正因為他既要實行和趙構妥協茍安相對立的抗戰路線,又要完全效忠于皇帝,因而陷入不可解脫的矛盾之中,終于不免以悲劇結局”。同時李時人又分析了產生這種情況的歷史原因:“在封建社會,由于人們認識的局限,一般是不敢懷疑皇權的,甚至往往把君王看成是國家和民族的象征。特別是當民族矛盾尖銳的時候,忠君和忠于民族又會暫時一致起來。作者強調宋朝皇帝的正統地位,是在明亡不久的歷史條件下,又寓有一定的民族意識,因此《說岳》贊揚岳飛的忠君和全書愛國主義思想傾向又有一定的歷史一致性。”李時人對《說岳全傳》的評價甚高,認為《說岳》有很高的思想和藝術價值,盡管他也指出了岳飛的“愚忠”,但同時認為岳飛的忠君與小說的愛國主義思想有一定的歷史一致性。
顧歆藝則明確指出岳飛的“愚忠”是《說岳全傳》的一大缺陷,降低了小說的價值:“其愚忠思想十分突出,小說甚至成為封建說教的工具,這是它的一大缺陷”;“分析忠君思想,一方面,當然是歷史的局限,因為作者是把皇帝視為國家、民族的象征,忠于皇帝也就是忠于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忠君思想是與反對侵略、維護民族利益的愛國主義思想聯系在一起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論是非、過分強調忠君思想,那么則會沖淡愛國主義的主題,同時也降低了小說的價值”。另外顧歆藝認為書中的封建迷信描寫也削弱了小說的價值:“迷信斗法在小說中屢屢出現,牛皋曾跟鮑方老祖學道,岳雷靠諸葛錦的神機妙算取勝等等”,“以因果報應統貫全書,成為小說的內在結構。將金兵南侵、北宋滅亡、南宋偏安、秦檜擅權、岳飛屈死等等,統統歸之于天數,以佛家因果、冤冤相報解釋種種社會現象,這類描寫,不僅荒唐可笑,更嚴重的是削弱和損害了作品的現實主義意義,并遮掩了民族斗爭的鋒芒”。
齊裕焜在《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中分析岳飛形象時也提到了岳飛的愚忠:“作者寫岳飛的精忠報國,主要方面應予肯定,但是,岳飛的忠,有時達到‘愚忠’的地步”,“作者也客觀地寫出了由于岳飛的愚忠而造成的悲劇,但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思想又像魔影一樣控制著作者,傳統的心理定勢使他無法完全按自己對現實的觀察如實地去描寫,最終只能用‘天命’、‘氣數’的因果報應之說,為岳飛因愚忠而造成的悲劇尋求解脫”。這是從作者的創作心態分析了岳飛“愚忠”的原因。
綜上所述,絕大多數學者和讀者都首先肯定了《說岳全傳》的價值,認為《說岳全傳》寫岳飛的精忠報國,其主要方面是愛國主義,由于歷史和作者本身的原因,岳飛的忠又有“忠君”甚至是“愚忠”的一面。但也有少數論者持不同的觀點。1982年第1期《社會科學輯刊》刊登李忠昌的《〈說岳全傳〉主題思想評價》一文,認為《說岳全傳》“從作者的整個創作傾向、謀篇布局、結構安排、細節描繪、人物塑造、版本演變上看,無一不是在刻意宣揚忠君思想”;作者“就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竭力宣揚忠君思想,為岳飛(文學形象)的‘精忠’立傳,或者說是讓岳飛用自己的一生行為譜寫的一曲忠君的贊歌”;“在《說岳全傳》里,既沒有寫出這位民族英雄的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更沒有把岳飛作為愛國的英雄形象來塑造”,“而是滿懷對忠臣孝子的崇敬之情,以忠君思想為軸心組織矛盾沖突和展開情節”。《說岳全傳》的作者是下層文人,他們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英雄形象,而這一形象也得到了民眾的歡迎,李忠昌認為他們是完全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塑造一個封建統治階級需要的“做人的楷模”,甚至“成為愚弄、奴役人民群眾的精神武器”,這顯然過于偏激。對于《說岳全傳》的查禁和流行,李忠昌這樣認為:“清乾隆年間此書遭禁,其原因也并非是宣揚了忠君,而是出于民族的自尊和偏見。后來又開禁流行,也正在于它的忠君主題利于維護封建專制統治使然。”筆者對這一觀點不能認同,《說岳全傳》曾兩次遭清政府查禁,統治階級并沒有認為此書利于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其在民間的廣泛流傳,也不是統治階級推行的結果,從《說岳全傳》的傳播接受來看,人們喜歡它更多的是因為其體現出來的抵抗侵略、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精神,特別是在清末這樣中華民族內憂外患之時,人們渴盼英雄出現,也尤為喜歡歷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借以鼓舞士氣、表達抗戰的決心,也是在殘酷的現實中尋求一種心理的安慰和揚眉吐氣的機會。
曾良在《是愛國還是忠君——評〈說岳全傳〉的主題思想》一文中表達了與李忠昌相似的觀點,認為“作者的創作意圖是宣揚忠孝節義思想,而其核心是忠君思想”;《說岳全傳》“并非歌頌愛國主義的民族英雄,而是竭力宣揚忠君思想”。李忠昌和曾良將注意力完全放在了《說岳全傳》的負面價值上,這種評價顯然有過激之嫌了。但同時曾良也承認“盡管作者的主觀意圖是宣揚岳飛的忠君思想,但客觀上《說岳全傳》流傳很廣,民眾多是從小說中了解岳飛的,并且更多地把他作為愛國主義的一面旗幟來歌頌,其愚忠思想反而降為次要地位”。
《說岳全傳》中大鵬鳥轉世、鐵背虬、女土蝠報冤、赤須龍臨凡的神話設置所涉及的因果報應,學術界歷來是持批判態度,如上文所述,即使對《說岳全傳》整體藝術水平持肯定態度的學者對這一點也頗有微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說岳全傳·前言》對此的論述更具代表性:“……在故事情節的處理上,以因果報應之說統貫全書……不僅荒唐可笑,更嚴重損害了作品的思想意義。編定者用宿命論來解釋種種社會現象。其目的無非是要人們相信,世情紛亂,起因結果,冥冥中自有安排,只要安于現狀,不怒不爭,靜候命運的擺布就是,書中這些明顯的糟粕,是應予以嚴肅批判的。”其它類似的論述尚有許多。但胡勝的《〈說岳全傳〉中的“因果報應”辨析》一文卻獨辟蹊徑,從民間果報觀念、藝術建構等方面揭示了此段因果報應設置背后值得深思的內蘊。胡勝首先分析了民間果報觀念:面對現實世界中諸多令人迷惑的不公現象,人們無法給自己滿意的答復,只好轉寄希望于自己創立的神,試圖通過神這一超自然的力量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并借此以調整自己失控的心理天平,求得一種精神上的滿足。“天道循環,報應不爽”式的道德勸戒具有震撼人心的威懾力。胡勝認為:“《說岳全傳》可以說是這種果報觀念的最好衍繹,書第八十回開篇詩‘世間缺陷亂紛紜,懊恨風波屈不伸。最是公道人心在,幻將奇語慰忠魂。’道出了果報設置乃在于昭示公道人心,彌補人世間的缺憾,為岳王伸冤。小說第七十三回寫秦檜、王氏及兩代奸相同黨在陰司中受苦,而岳王等忠臣義士都在仙府自在逍遙,表達了民眾鮮明的愛憎”;“《說岳全傳》中因果報應的實質,與其說是一種望梅止渴式的自慰,毋寧說是現實倫理世界的折光”。另外胡勝還認為從藝術建構上講,這段因果報應貫穿全書,使得整部小說的意境奇幻相生,撲朔迷離,也起到了動人視聽的效果。胡勝著眼于《說岳全傳》體現出來的普通民眾的樸素的情感與善惡觀念,對讀者理解其中的因果報應、宿命等設置頗具啟發意義。
注:
① 鄭振鐸《岳傳的演化》,《中國文學研究》(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頁。
② 李厚基《讀〈說岳全傳〉》,《光明日報》1956年4月22日第1版。
③ 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中國小說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300頁。
⑦ 羅書華《中國傳奇喜劇英雄生成考辨——牛皋、程咬金、焦廷貴》,《明清小說研究》1997年第3期。
⑧ 趙文光《古典歷史小說“魯莽”英雄形象特征及美學意蘊》,《美與時代》2003年第5期。
⑨ 孫長明、許海麗《牛皋福將形象的成因初探》,《語文學刊》2007年第17期。
⑩ 王立、馮立嵩《忠奸觀念與反面人物形象塑造》,《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