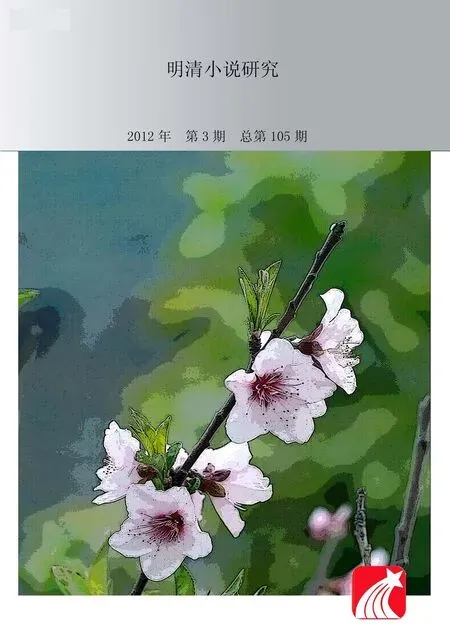孫悟空與佛家神通
··
孫悟空形象的來源,一直為章回小說《西游記》研究中一大熱點。大體而言,有四家說法:1.胡適據印度史詩《羅摩衍那》提出的哈奴曼說①,即“外來說”;2.魯迅據《古岳瀆經》提出的淮渦水神無支祁說②,即“本土說”;3.蔡國梁③、蕭兵④等綜合二說提出混血說或稱混合說;4.日本學者磯部彰等人據佛教密宗典籍提出的猴形護法神將說⑤,即“佛典說”。四種說法,均表現為一種對應式的原型考索。這種方法,在研究文人獨立創作時,是行之有效的,但對于《西游記》這樣的世代累積型創作,其存在的問題也顯而易見。
如眾周知,作為《西游記》故事的歷史原型,在唐朝初年玄奘赴印度取經的史實中,并沒有齊天大圣孫悟空的影子在。如果我們要追索章回小說《西游記》中孫悟空的雛形,則是《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的白衣秀才猴行者。“取經故事”經過了極其漫長的演變過程。而孫悟空形象,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的猴行者發端,也經歷了不知凡幾的民間藝人、書會才人、文人作家等眾人之手,其在素材來源上具有多源性,其形成過程更具有相當的復雜性。既有的研究成果,無支祁、哈奴曼、猴形神將等等,只能說是在孫悟空形象演變的過程中,通過種種渠道,有可能影響其生成的某些因子。
作為一個由“世代累積”而誕生的文學形象,考察《西游記》中孫悟空的來源,我們對于構成其形象的特征性內容,諸如火眼金睛、善能識妖、銅筋鐵骨、千里眼、順風耳、聞風鼻、七十二變化、分身術、十萬八千里筋斗云,及其超凡的降妖滅怪本領等,卻是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孫悟空的形象特征,一言以蔽之,即神通廣大,這很自然讓人想起佛教基本典籍中那俯拾即是的關于佛家神通的資料。
清初人潘耒在其《救狂砭語·與長壽院主石鐮書》中說:“神通之說,佛家有之。”佛教典籍中關于神通的記載甚多。《大乘義章》卷二十云:“神通者,就名彰目。所為神異,目之為神,作用無雍,謂之為通。”《無量壽經·法會圣眾第一》云:“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一切大圣神通已達。”佛家有“五神通”、“六神通”諸說。所謂“六神通”,包括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如意通、漏盡通。佛典認為,修四禪可以得到前五通,如《出三藏記集》卷六載康僧會《安般守意經序》中說,行禪法能夠“制天地,住壽命,猛神德,壞天兵,動三千,移諸剎,入不思議,非梵所測”;《大智度論》卷二《初品》中云,成就阿羅漢者,“得六神通,具三明智,諸禪三昧,自在出入,逆順超越”;《高僧傳》卷十一《習禪傳論》中慧皎云:“禪用力顯,屬在神通”。即以《高僧傳》為例,其卷九《神異上》列高僧4人,卷十《神異下》列高僧16人,均為負有神通異能之人。
佛家認為,神通與觀想有關,釋道安《安般注序》云:“安般者,出入也。道之所寄,無往不因;德之所寓,無往不托。是故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禪寓骸以成定也。寄息故有六階之差,寓骸故有四級之別。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級別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無欲也。無為故無形而不因,無欲故無事而不適。無形而不因,故能開物;無事而不適,故能成務。成務者,即萬有而自彼;開物者,使天下兼忘我也。”(《出三藏記集》卷六)佛教不以神通為追求,但神通有助于弘法,如《高僧傳》卷十《神異下》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強摧侮慢,挫兇銳解塵紛。”這正是佛教渲染其神通的直接目的。
茲舉佛教若干基本典籍中相關資料,對比《西游記》中孫悟空“神通”之具體表現,通過其間所存在的聯系,將有助于我們更確切地把握孫悟空形象生成的特殊過程,對于更恰切地理解孫悟空形象的文化內涵也有裨益。
一、銅筋鐵骨、水火不壞、刀劍不傷
此《西游記》中孫悟空形象特征性內容之一。第七回,孫悟空大鬧天宮被擒,“被眾天兵押去斬妖臺下,綁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槍刺劍刳,莫想傷及其身。南斗星奮令火部眾神,放火煨燒,亦不能燒著。又著雷部眾神,以雷屑釘打,越發不能傷損一毫”。太上老君將他放進八卦爐中,以文武火鍛煉,七七四十九日,火候俱全,待要開爐取丹。大圣將身一縱,跳出丹爐,蹬倒八卦爐,往外就走。第十九回,孫悟空向豬八戒賣弄自家本事,也說:“你是也不知。老孫因為鬧天宮,偷了仙丹,盜了蟠桃,竊了御酒,被小圣二郎擒住,押在斗牛宮前,眾天神把老孫斧剁錘敲,刀砍劍刺,火燒雷打,也不曾損動分毫。又被那太上老君拿了我去,放在八卦爐中,將神火鍛煉,煉做個火眼金睛,銅頭鐵臂。不信,你再筑幾下,看看疼與不疼?”
類似孫悟空這般的神通,舉漢傳佛教典籍中的例子,具體如:
1.《維摩詰經》卷中《不思議品第六》:“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于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為害。又于下方過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過恒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針鋒舉一棗葉,而無所嬈。”
2.《五燈會元》卷二:“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
3.《高僧傳》卷第十《神異下》:“釋曇始……多有異跡。……晉末朔方兇奴赫連勃勃破擭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刀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后拓跋燾……毀滅佛法……有一道人足白于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馀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喂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
舍利弗將十方世界所有大風吸納腹中,身體不變形;將十方世界壞劫末期所有大火吸納腹中,其體略不受損。行昌持劍欲害六祖惠能,屢斫無傷。曇始亦刀劍不能傷,砍斫無所損。此較之悟空銅筋鐵骨,并無稍遜。其對于孫悟空形象塑造,當有啟示意義。
二、火眼金睛、善能識妖、千里眼、順風耳、聞風鼻
此《西游記》中孫悟空形象特征性內容之二。第十五回,孫悟空向唐僧說道:“你也不知我的本事。我這雙眼,白日里常看一千里路的吉兇。像那千里之內,蜻蜓兒展翅,我也看見,何期那匹大馬,我就不見!”第二十回,在黃風嶺下,忽然起一陣旋風。孫悟空用手將這風抓一把,聞一聞,說道:“果然不是好風!這風的味道不是虎風,定是怪風,斷乎有些蹊蹺。”第二十七回,唐僧一行離開五莊觀西去,悟空跳上云端,手搭涼篷,睜眼觀看,只見正南上有一座高山,向陽處,有一片鮮紅的點子,知道是熟透了的山桃,于是前去采摘。回來,見到白骨精變成一齋僧的年輕女子,八戒與唐僧都不能辨識。悟空“睜火眼金睛觀看,認得那女子是個妖精,放下缽盂,掣鐵棒,當頭就打”。接著,妖精又變成八十歲的老婦人、老公公,均被悟空識出。第三十三回,平頂山蓮花洞二魔,變做一年紀高大的受傷道人,騙過了唐僧、沙僧,卻被孫悟空一眼看出是個妖精。
孫悟空此類神通,在漢傳佛典中可找到大量類似的例子,如:
1.《無量壽經·發大誓愿第六》法藏云:“我作佛時,所有眾生,生我國者,自知無量劫時宿命,所作善惡,皆能洞視、徹聽,知十方去來現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覺”(六、宿命通愿;七、天眼通愿;八、天耳通愿);“我作佛時,所有眾生,生我國者,皆得他心智通。若不悉知億那由他百千佛剎眾生心念者,不取正覺”(九、他心通愿)。
2.《無量壽經·菩薩修持第三十》:“依佛所行,七覺圣道,修行五眼,照真達俗,肉眼簡擇,天眼通達,法眼清凈,慧眼見真,佛言具足,覺了法性。”
3.《梵網經》卷上《十地》第六:“若佛子,菩提薩埵,體性華光地。能于一切世界中,十神通明智品,以示一切眾生種種變化。以天眼明智,知三世國土中微塵等一切色,分分成六道眾生身,一一身微塵細色,成大色,分分知。以天耳智,知十方三世六道眾生,苦樂音聲,非非音,非非聲,一切法聲。以天身智,知一切色,色非色,非男非女形。于一念中,遍十方三世國土劫量,大小國土中微塵身。以天他心智,知三世眾生心中所行,十方六道中一切眾生心心所念,苦樂善惡等事。”
4.《維摩詰經》卷上《佛國品第一》:“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凈,則佛土凈者,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凈,而是佛土不凈若此?佛知其念,即告之言:‘于意云何?日月豈不凈耶?而盲者不見。’”
5.《維摩詰經》卷上《弟子品第三》:阿那律向佛陀云:“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于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凈,與萬梵俱,放凈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我即答言:‘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庵摩勒果。’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為作相耶?無作相耶?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世尊,我時默然。彼諸梵聞其言,得未曾有,即為作禮而問曰:‘世孰有真天眼者?’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
6.《維摩詰經》卷中《不思議品第六》:“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床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眾,當于何坐?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為法來耶?求床座耶?’”
7.《楞伽經·羅婆那王勸請品第一》:“爾時,羅婆那夜叉王,以佛神力,聞佛言音,遙知如來從龍宮出,梵釋護世天龍圍繞,見海波浪,觀其眾會,藏識大海境界風動,轉識浪起,發歡喜心,于其城中高聲唱言:‘我當詣佛請入此城,令我及與諸天世人,于長夜中,得大饒益。’作是語已。即與眷屬乘花宮殿,往世尊所。”
8.《法華經·法師功德品第十九》:“爾時,佛告常精進菩薩摩訶薩:‘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以是功德莊嚴六根皆令清凈。是善男子、善女人,父母所生清凈肉眼,見于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所有山林河海,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亦見其中一切眾生,及業因緣果報生處,悉見悉知。……以是清凈耳,聞三千大千世界,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其中內外種種語言音聲。……以是清凈鼻根,聞于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內外種種諸香。……以是清凈意根……三千大千世界六趣眾生,心之所行,心所動作,心所戲論,皆悉知之。’”
9.《五燈會元》卷一:“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遍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于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于是才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10.《高僧傳》卷第九《神異上·晉鄴中竺佛圖澄》:“竺佛圖澄……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劾驗。”
11.《五燈會元》卷二:“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為嬌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為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
12.《高僧傳》卷第十《神異下·晉洛陽盤鴟山犍陀勒》:“犍陀勒……謂眾僧曰:‘洛東南有槃鴟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墌猶存,可共修立。’眾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后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眾咸驚嘆,因共修立,以勒為寺主。”
法藏比丘說,當其成佛時,要讓眾生洞曉各自往生、此身、來生之善惡果報,知悉十方世界過去、將來、現在發生的所有事情,具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依照佛陀教化,修行七種覺悟、八種圣道,修行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能夠照見諸法實相,洞悉宇宙萬法。具天眼通,可見十方三界國土中如微塵一樣之細物,及四大幻相、六道眾生身相之本色;具天耳通,可以聞聽十方三界六道眾生苦樂音聲,知苦樂音聲非苦樂音聲,乃至世間一切法聲。而清凈肉眼,能觀察到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所有山林河海,及阿鼻地獄、三界頂天;清凈耳,可以聽到三千大千世界上至頂天下到地域一切聲音;清凈鼻根,能聞到三千大千世界內外各種香氣;清凈意根,能洞察三千大千世界六道眾生內心之想法念頭。此亦孫悟空千里眼、順風耳、聞風、辨妖諸神通之所本。
三、十萬八千里筋斗云
此《西游記》中孫悟空形象特征性內容之三。第二回,敘菩提祖師傳給孫悟空騰云之法,“這朵云,捻著訣,念動真言,攢緊了拳,將身一抖,跳將起來,一筋斗就有十萬八千里路”。第十四回,孫悟空向唐僧道:“不瞞師父說,我會駕筋斗云,一個筋斗有十萬八千里路。”
孫悟空此種神通,在漢傳佛典中,也有類似例子,如:
1.《無量壽經·發大誓愿第六》法藏言:“我作佛時,所有眾生,生我國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羅密多。于一念頃,不能超過億那由他百千佛剎,周遍巡歷,供養諸佛者,不取正覺”(十、神足通;十一、遍供諸佛愿)。
2.《壇經·疑問品第三》:“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后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睹彌陀。”
3.《維摩詰經》卷下《香積佛品第十》:“時,化菩薩即于會前,升于上方,舉眾皆見其去。到眾香界,禮彼佛足……彼諸大士,見化菩薩,嘆未曾有:‘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為在何許?云何名為樂小法者?”……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神足若斯?’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眾生。’……時,化菩薩既受缽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于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
4.《法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爾時,文殊師利坐千葉蓮華大如車輪,俱來菩薩亦坐寶蓮華,從于大海娑竭羅龍宮自然涌出,住虛空中,詣靈鷲山。從蓮華下至于佛所,頭面敬禮二世尊足。”
5.《法華經·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妙音菩薩白其佛言:‘世尊,我今詣娑婆世界,皆是如來之力、如來神通游戲、如來功德智慧莊嚴。’于是妙音菩薩不起于座,身不動搖而入三昧,以三昧力于耆阇崛山去法座不遠,化作八萬四千眾寶蓮華,閻浮檀金為莖,白銀為葉,金剛為須,甄叔迦寶以為其臺。”
6.《五燈會元》卷一:“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言已,云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
7.《佛祖統記》卷九:慧威,“江陵人,依南岳行法華三昧,得解一切眾生語言陀羅尼,聞入畜禽鳥聲,必知其意。又發證神通,飛空履水,如步平地”。
法藏言,當其成佛時,令佛國眾生具神足通,剎那念起,可抵無邊凈土,周游佛國。惠能說,西方極樂世界并非遙遠,消除十惡,即行十萬里;除去八邪,又過八千里,瞬間十萬八千里可達。化身菩薩接受香積佛贈與飯食,得神通力,瞬間由眾香國到維摩詰精舍。文殊師利菩薩等坐寶蓮花上,從龍宮涌出,飛往靈鷲山法華會場。妙音菩薩其身未動,依仗定力,剎那間到娑婆世界耆阇崛山釋迦摩尼佛法座近處。達磨大師云生足下。慧威“飛空履水,如步平地”。此皆為孫悟空十萬八千里筋斗云之原料。
四、七十二般變化、分身術
此《西游記》中孫悟空形象特征性內容之四。第二回,菩提祖師傳給孫悟空七十二般變化,悟空因得了仙體,“身上有八萬四千毛羽,根根能變,應物隨心”。同回,孫悟空在花果山與混世魔王打斗,“見他兇猛,即使身外身法,拔一把毫毛,丟在口中嚼碎,望空噴去,叫一聲:‘變!’即變做三二百個小猴,周圍攢簇”。第五回,孫悟空反下天宮,天兵征剿,“大圣見天色將晚,即拔毫毛一把,丟在口中,嚼碎了噴將出去,叫聲:‘變!’就變了千百個大圣,都使的是金箍棒,打退了哪吒太子,戰敗了五個天王”。第六回,孫悟空與二郎神斗法,二郎神變得身高萬丈,孫悟空也變得與二郎身軀一般;孫悟空變作個麻雀兒,二郎神變作個餓鷹兒;悟空變作一只大鶿老,二郎變作一只大海鶴;悟空變作一只魚兒,二郎神變作個魚鷹兒;悟空變作一條水蛇,二郎神變了一只朱繡頂的灰鶴;悟空變做一只花鴇,二郎神現原身,取彈弓打去;悟空變了一座土地廟兒,二郎神再現了本相。第二十七回,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被唐僧嗔怪驅逐,孫悟空拜唐僧,唐僧不睬,他使個身外法,把腦后毫毛拔了三根,吹口仙氣,變了三個行者,連本身四個,四面圍住師父下拜。唐僧左右躲不脫,只得受了一拜。第十六回,孫悟空在觀音禪院變做一個蜜蜂兒。第十九回,孫悟空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做一條三股麻繩。第三十二回,在平頂山,孫悟空變作個蟭蟟蟲兒,跟蹤豬八戒,見八戒睡進草叢,又變作個啄木蟲兒,揸他的嘴唇。第三十四回,孫悟空變蒼蠅、變小妖、變妖母。第三十六回,行者把腰兒躬一躬,長了二丈馀高,用手展去灰塵,見是“敕建寶林寺”。第六十一回,孫悟空與牛魔王比賽變化,牛王變做一只天鵝,悟空變作一個海東青;牛王變作一只黃鷹,悟空變作一個烏鳳;牛王變作一只白鶴,悟空變作一只丹鳳;牛王變作一只香獐,悟空變作一只餓虎;魔王變作一只金錢花斑大豹,悟空變作一只金眼狻猊;牛王變作一只人熊,悟空變作一只賴象;牛王現原身成一只大白牛,連頭至尾,有千馀丈長,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悟空也現原身,抽出金箍棒來,把腰一躬,喝聲叫:“長!”長得身高萬丈,頭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血池,牙似門扇,手執一條鐵棒,著頭就打。
孫悟空此等神通,可舉漢傳佛典中幻變、分身等例子,如:
1.《無量壽經·德尊普賢第二》:“諸佛剎中,皆能示現。譬善幻師,現眾異相,于彼相中,實無可得。此諸菩薩,亦復如是,通諸法性,達眾生相,供養諸佛,開導群生。化現其身,猶如電光,裂魔見網,解諸纏縛。遠超聲聞、辟支佛地,入空、無相、無愿法門。”
2.《解深密經》卷第五《如來成所作事品第八》:“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遍于一切三千大千佛國土中,或眾推許增上王家,或眾推許大福田家,同時入胎、誕生、長大、受欲、出家、示行苦行、舍苦行已成等正覺,次第示現,是名如來示現化身方便善巧。”
3.《維摩詰經》卷中《不思議品第六》:“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升。……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圣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眾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于其中,普令得聞。”
4.《楞伽經·羅婆那王勸請品第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大海濱摩羅耶山頂楞伽城中,與大比丘眾及大菩薩眾俱。其諸菩薩摩訶薩悉已通達五法三性,諸識無我,善知境界自心現義,游戲無量自在三昧神通諸力,隨眾生心現種種形,方便調伏,一切諸佛手灌其頂,皆從種種諸佛國土而來此會。……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于彼山中復更化作無量寶山,悉以諸天百千萬億妙寶嚴飾。一一山上,皆現佛身,一一佛前,皆有羅婆那王及其眾會十方所有一切國土,皆于中現;一一國中,悉有如來,一一佛前,咸有羅婆那王并其眷屬,楞伽大城阿輸迦園,如是莊嚴,等無有異。一一皆有大慧菩薩,而興請問,佛為開示自證智境,以百千妙音說此經已,佛及諸菩薩皆于空中隱而不現。……爾時,世尊普觀眾會,以慧眼觀,非肉眼觀,如師子王奮迅回盼,欣然大笑,于其眉間、髀脅、腰頸及以肩臂德字之中,一一毛孔皆放無量妙色光明。”
5.《法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佛告諸比丘:‘爾時王者,則我身是;時仙人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舍,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十力,四無所畏,四攝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眾生,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
6.《法華經·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華德,汝但見妙音菩薩其身在此,而是菩薩現種種身,處處為諸眾生說是經典。或現梵王身,或現帝釋身,或現自在天身,或現大自在天身,或現天大將軍身,或現毗沙門天王身,或現轉輪圣王身,或現諸小王身,或現長者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宰官身,或現婆羅門身,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或現長者、居士、婦女身,或現宰官婦女身,或現婆羅門婦女身,或現童男童女身,或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而說是經。諸有地獄、餓鬼、畜生及眾難處,皆能救濟,乃至于王后宮,變為女身而說是經。”
7.《法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于是二子念其父故,涌在虛空,高七多羅樹,現種種神變,于虛空中行住坐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小復現大,于空中滅忽然在地,入地如水,履水如地,現如是等種種神變,令其父王心凈信解。”
8.《高僧傳》卷第十《神異下·梁京師釋保志》:“齊武帝謂其惑眾,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志猶在焉。志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來,金缽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慧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餉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即迎入,居之后堂。一時屏除內宴,志亦隨眾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志,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在。閣吏啟云:‘志久出在省,方以墨涂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志,遣使于龍光、罽賓二寺求之,并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
9.《五燈會元》卷一:“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于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10.《五燈會元》卷一《十二祖馬鳴尊者》:“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眾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為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音角〕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祖儼然于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
11.《五燈會元》卷二: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為女身?”
12.《五燈會元》卷二:“南陽慧忠國師……唐肅宗上元二年,敕中使孫朝進赍詔征赴京,待以師禮。……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才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么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么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么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么處!’藏無對。”
大菩薩們在十方佛界,如同幻師,能夠示現種種應身及化身。佛陀告訴曼殊室利菩薩說,如來化身,遍于一切三千大千世界佛國。得到神通的菩薩,剎那間身體長至四萬二千由旬。舍利弗以神通分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圣王身”。佛陀隨眾生之心,幻出種種形象,方便說教;又能分身,每一寶山,每一國中,每一佛前,皆有佛現。妙音菩薩能現示各種身相:梵王身、帝釋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天大將軍身、毗沙門天王身、轉輪圣王身、諸小王身、長者身、居士身、宰官身、婆羅門身,以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長者居士婦女身,宰官婦女身,婆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身等等。保志、慧忠也有分身之術。十二祖馬鳴與老人斗法,老人變一小蟲,大若蟭螟。此類神通記載,亦當為孫悟空形象塑造所取資。
五、奇方異術
此《西游記》中孫悟空形象特征性內容之五。第二十六回,孫悟空請來觀世音菩薩,用凈瓶中的甘露水,救活枯死的人參果樹。第三十九回,悟空被唐僧逼不過,駕筋斗云來到兜率宮,向太上老君討要了一粒金丹,沖灌進烏雞國國王肚里,又把雷公嘴噙著那皇帝的口唇,一口氣吹入咽喉,死去已久的烏雞國國王氣聚神歸,得以復生。第四十回,紅孩兒變化成幼兒,掛在樹上,口口聲聲喊叫救人,悟空知其為妖,怕唐僧上當,念個咒語,使了個移山縮地之法,把金箍棒往后一指,師徒過了峰頭,卻把那怪物撇下。第四十五回,孫悟空與妖道比賽求雨,指示四海龍王等各路神仙,自己將棍子為號,往上一指要刮風,第二指要布云,第三指要雷鳴電閃,第四指要下雨,第五指要大日晴天,果然一場好雨,下得那車遲城里水漫了街衢。第四十六回,孫悟空與妖道比砍頭,劊子手將他的腦袋砍下,一腳踢去三四十步遠近,只聽得肚里叫聲:“頭來!”被鹿力大仙念動咒語,將頭扯住,悟空捻著拳,掙了一掙,喝聲“長”,颼的腔子內長出一個頭來;又比剖腹剜心,悟空自己用雙手扒開肚腹,拿出腸臟來,一條條理夠多時,依然安在里面,照舊盤曲,捻著肚皮,吹口仙氣,叫:“長!”依然長合。第七十九回,比丘國國王聽信妖道,要用唐僧的心肝做藥引,孫悟空變成師父,將左手抹腹,右手持刀,唿喇的響一聲,把腹皮剖開,那里頭就骨都都的滾出一堆心來,唬得文官失色,武將身麻,那昏君唬得呆呆掙掙,口不能言,戰兢兢的教:“收了去,收了去!”
孫悟空此類神通,舉漢傳佛典中的例子,如:
1.《高僧傳》卷第九《神異上·晉鄴中竺佛圖澄》:“竺佛圖澄……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襄國城塹水源……久已干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咒愿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石虎有子名斌,后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澄乃取楊枝咒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
2.《五燈會元》卷一:“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睹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眾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祖至,先見宮墻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為?’祖曰:‘將度眾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于祖頂上。祖指之,忽在彼眾頭上。梵志等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
3.《高僧傳》卷第九《神異上·晉洛陽耆域》:“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腳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疾差不。’因取凈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柳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兩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此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咒,如咒永文法,樹尋荑發,扶疏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咒愿數千言,即有臭氣薰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垽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
4.《高僧傳》卷第十《神異下·晉長安涉公》:“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苻堅建元十二年至長安。能以秘咒咒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咒龍,俄而龍下缽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缽中觀之,咸嘆其異。堅奉為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
5.《宋高僧傳》卷二十六《唐晉州大梵寺代病師傳》:“初止今東京,次于河陽,為民救旱,按經繪八龍王,立道場。啟祝畢,投諸河。舉眾咸睹畫像沉躍不定,斯須云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眾。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雹,動傷苗稼雉堞,號為毒龍為之也。代病為誦密語,后經歲序,都亡是患。”
6.《維摩詰經》卷上《佛國品第一》:“爾時,毗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于中現。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雪山、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諸尊神宮,悉現于寶蓋中。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亦現于寶蓋中。”
圖澄求雨,醫活死人,理腸清洗;密多尊者移山之術;耆域治病、醫活枯樹;涉公、代病役使神龍降雨;佛陀運神通合攏眾多寶傘,覆蓋三千大千世界,此亦為《西游記》孫悟空降雨、治病、搬觀世音醫治人參果樹、裝天等借鑒材料。
如上所舉證之佛典,《無量壽經》有東漢月支僧人支婁迦讖譯本、曹魏時期天竺三藏康僧鎧譯本等;《梵網經》有六朝陳智文注本、隋朝智凱說灌頂記本、唐朝法藏注本等;《解深密經》有南朝宋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羅譯本、北魏時期印度僧人菩提流支譯本、南朝陳印度僧人真諦譯本、唐朝玄奘譯本等;《維摩詰經》有東漢嚴佛調譯本、吳支謙譯本、西晉竺法護譯本、后秦鳩摩羅什譯本、唐朝玄奘譯本等;《楞伽經》有劉宋時期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羅譯本、北魏時期印度僧人菩提流支譯本、唐朝實叉難陀譯本;《壇經》是唐朝僧人惠能在韶州大梵寺說法,其門人記錄整理本,今存敦煌寫本、約晚唐宋初惠昕本等;《法華經》有三國時期支疆梁接譯本、西晉竺法護譯本、后秦鳩摩羅什譯本等;《高僧傳》乃南朝梁天監年間慧皎著;《宋高僧傳》乃北宋太平興國七年贊寧撰;《五燈會元》乃南宋普濟撰;《佛祖統記》乃南宋寶祐二年至咸淳五年志磐撰。而這些著作,首先都是在中土廣為流傳,知名度極高的佛教典籍,不僅閱讀者眾,也是佛門宣講的常用書,普及率很高。其次,除了《宋高僧傳》、《五燈會元》、《佛祖統記》為宋人著作,其他在唐朝以前(包括唐朝)均盛為傳播,對于唐代中后期開始傳播的“取經故事”,自然存在發生影響的可能。其三,玄奘取經故事,其自身即屬于佛教內容范疇,在其傳播過程中,人們以盛傳的經典內容加以豐富或附會,實屬自然。
綜上可知,“取經故事”在傳播演進的過程中,曾經廣泛地吸收了佛教的各種素材,自不待言。其不斷豐富,由歷史變易為神話,章回小說中的唐僧,也已經與歷史人物玄奘,有了本質的不同。至于原本就是虛構產物、神話人物的孫悟空,從《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出現其雛形,到《西游記平話》、楊景賢《西游記雜劇》,再到章回小說《西游記》,其間包括了眾多民間無名氏的加工創造,人們根據各自的理解與知識儲備,對其加以不斷的改造、充實、豐富、更新,賦予其新的意義,所以,在其生成過程中,取材上的多源與演變的復雜,可以想見。總之,孫悟空的神通廣大,與佛教基本典籍中隨處可見的神通故事,并非偶然的巧合。從本文舉證的佛典“神通”資料,不難發現,這是孫悟空形象形成過程中重要的取材資源,其內容也最終成為孫悟空形象構成的重要元素。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ZWB007)
注:
① 胡適《〈西游記〉考證》,《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02-904頁。
②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國小說史略》(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頁。
③ 蔡國梁《孫悟空的血統》,《學林漫錄》第2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
④ 蕭兵《無支祁哈奴曼孫悟空通考》,《文學評論》1982年第5期。
⑤ [日]磯部彰《元本〈西游記〉中孫行者的形成》,《集刊東洋學》第38期,1977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