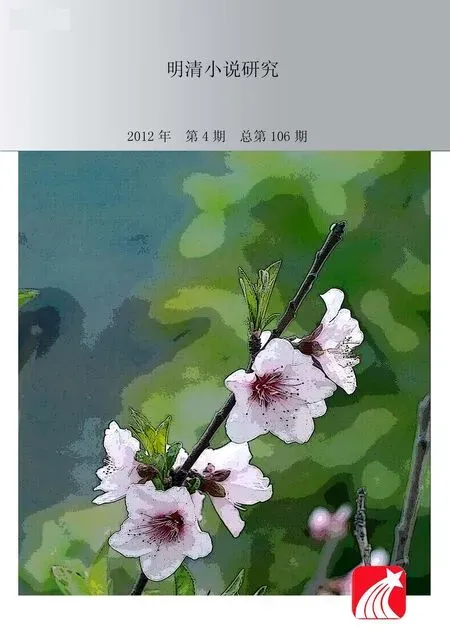從詩詞韻文運(yùn)用看《金瓶梅詞話》的民族性
··
詩詞韻文的運(yùn)用是中國古代小說十分常見的現(xiàn)象,也許正是因?yàn)椤笆殖R姟保匝芯空邆兺兴雎曰虿簧踝⒁猓瑢τ谛≌f《金瓶梅詞話》的研究也是如此。在我看來,小說大量運(yùn)用詩詞韻文,不僅是中國古代小說的一個重要特點(diǎn),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而且它還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小說強(qiáng)烈的民族性。本文以小說《金瓶梅詞話》為個案,略述粗淺之見。
(一)
之所以選擇《金瓶梅詞話》敘述這一問題,自然是因?yàn)樾≌f具有相當(dāng)?shù)拇硇浴Ec《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主要依據(jù)宋元講唱話本為基礎(chǔ)創(chuàng)作的小說不同,《金瓶梅詞話》的成書,更多融入了文人獨(dú)立創(chuàng)作的因素,盡管全篇也有不少故事情節(jié)、語言乃至詩詞韻文與宋元話本脫不了干系,但從總體上說,它們是被當(dāng)作創(chuàng)作素材或是藝術(shù)上的借用而進(jìn)入小說的。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在留存的歷史文獻(xiàn)中看到有任何“金瓶梅”三字書名的記載,而且這部文學(xué)名著出現(xiàn)的詩詞韻文似乎也特別多,每一回前都有韻文唱詞①。據(jù)1982年8月香港出版的太平書局版影印本《全本〈金瓶梅〉詞話》的初步統(tǒng)計(jì),全書200多萬字中,其他韻文暫且不計(jì),單是詩詞就有三百六十多首②,引用和化用前人詩詞的至少有二百四十多首③,散曲也有100多首。因此,這部小說出現(xiàn)的詩詞韻文絕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十分重要,應(yīng)予重視。
《金瓶梅詞話》嵌入大量詩詞韻文究竟有何重要作用?魯迅說:“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dá),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并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④尤其是詩詞韻文的引用,人物的口吻、語氣、神態(tài)、動作都鮮活起來,人物的心理與個性也活靈活現(xiàn)地表現(xiàn)無遺,以強(qiáng)烈的直觀性形態(tài)呈現(xiàn)于讀者眼簾,具有“表現(xiàn)人物內(nèi)心幽隱、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暗寓人物關(guān)系和人物命運(yùn)、烘托氣氛”⑤等重要的文學(xué)功能。對此,我以為至少有四個方面應(yīng)予關(guān)注,簡例如下:
(1)揭示主題。第六十回中,描寫李瓶兒病榻生活的七絕詩:
纖纖新月照銀屏,人在幽閨欲斷魂。
益悔風(fēng)流多不足,須知恩愛是愁恨!
“欲斷魂”句表現(xiàn)出李瓶兒內(nèi)心的哀怨悲愁,后兩句則是她一生的真實(shí)寫照,直接點(diǎn)明“勸人戒欲”的主題。又如,第一百回中的回末詩:
閑閱遺書思惘然,誰知天道有循環(huán)。
西門豪橫難存嗣,經(jīng)濟(jì)顛狂定被殲。
樓月善良終有壽,瓶梅淫佚早歸泉。
可怪金蓮遭惡報(bào),遺臭千年作話傳。
這首詩即是小說主旨的概述,對西門慶、陳經(jīng)濟(jì)、孟玉樓、吳月娘、李瓶兒、龐春梅、潘金蓮等主要人物的命運(yùn)一一作了歸結(jié):男女之欲是人性本能,然多欲少情、以欲亂禮、借欲斂財(cái),則將是縱欲亡身的結(jié)局。直接表明了戒淫節(jié)欲的態(tài)度⑥,訓(xùn)示人們對男女之歡的理性思考。
(2)刻畫人物。第四十九回寫西門慶宴請蔡御史,后留其宿夜,來至翡翠軒:
只見兩個唱的盛妝打扮,立于階下,向前花枝招飐嗑頭。蔡御史看見,欲進(jìn)不能,欲退不可,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厚愛,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游,又何別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攜手,不啻恍若劉阮之入天臺。因進(jìn)入軒內(nèi),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diǎn),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余,軒中文物尚依稀。
雨過書童開藥圃,風(fēng)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鐘何急,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不知何日是重來。
這首詩“寫盡了兩面”,不露聲色地將風(fēng)雅之狀與卑俗之心充分表現(xiàn)出來⑦,人物刻畫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又如,小說第十二回的一段駢文,把眾幫閑不惜出賣人格尊嚴(yán)而換得殘羹冷炙的丑態(tài),描繪得窮形盡相:
但見:人人動嘴,個個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蝻一齊來;擠眼掇肩,好似餓牢才打出。這個搶風(fēng)膀臂,如經(jīng)年未見酒和肴;那個連二筷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個汗流滿面,恰似與雞骨朵有冤仇;一個油抹唇邊,把豬毛皮連唾咽。吃片時,杯盤狼藉;啖良久,箸子縱橫。杯盤狼藉,如水洗之光滑;箸子縱橫,似打磨之干凈。這個稱為“食王元帥”,那個號作“凈盤將軍”。酒壺番曬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正是:珍饈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駢文的嵌入,一群靠攀結(jié)權(quán)貴、阿諛奉承而活的幫閑之貪婪本質(zhì)躍然紙上,人物形象完整清晰,深刻逼真。
(3)發(fā)展情節(jié)。如《金瓶梅詞話》第一回中的一首詞:
萬里彤云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檐,剡溪當(dāng)此際,濡滯子猷船。
頃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鹽撒粉漫連天。當(dāng)時呂蒙正,窯內(nèi)嘆無錢。
作者用“祥瑞”“瓊花”比喻,形象化地勾勒了一幅瑞雪紛飛、銀裝素裹的雪景圖。良辰美景下,小說以《世說新語·任誕》中的典故,襯托潘金蓮對武松“挑逗”的“落花有意,流水無情”⑧。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推動了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又如,第十三回中的一首七律詩:
烏兔循環(huán)似箭忙,人間佳節(jié)又重陽。
千枝紅樹妝秋色,三徑黃花吐異香。
不見登高烏帽客,還思捧酒綺羅娘。
繡簾瑣闥私相覷,從此恩情兩不忘。
這是描寫花子虛邀西門慶、應(yīng)伯爵等“十兄弟”在家中歡度重陽節(jié)之夜的情形。詩中的“思”,喻意西門慶“思想佳人”李瓶兒。尾聯(lián)表述兩人偷覷于繡簾中的微妙情感,綿綿情意,念念不忘。嵌入這首七律,堪稱佳作,有力地推進(jìn)了小說情節(jié)的發(fā)展,為李瓶兒日后“隔墻密約”作了鋪墊⑨。
(4)環(huán)境或氣氛的烘托。中間穿插大量的戲曲段子,是《金瓶梅詞話》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對于烘托人物內(nèi)心世界,推進(jìn)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性格的發(fā)展起到重要作用⑩。如小說第三十八回,金蓮每日獨(dú)守空房,“翡翠衾寒,芙蓉帳冷”,一曲《二犯江水兒》,邊彈邊唱,感嘆寂寞:
把幃屏來靠,和衣強(qiáng)睡倒。
猛聽的房檐上鐵馬兒一片聲響,只道西門慶來到,敲的門環(huán)兒響,連忙使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錯了,是外邊風(fēng)起落雪了。”婦人于是彈唱道:
聽風(fēng)聲嘹喨,雪灑窗寮,任冰花片片飄。
一回兒燈昏香盡,心里欲待去剔續(xù),見西門慶不來,又意兒懶的動旦了。唱道: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捱過今宵,怕到明朝。細(xì)尋思,這煩惱何日是了?想起來,今夜里心兒內(nèi)焦,悮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
又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閑自惱。
……
口中又唱道:
心癢痛難搔,愁懷悶自焦。讓了甜桃,去尋酸棗。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rèn)了。想起來,心兒里焦,誤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
環(huán)境描寫在氛圍的營造和人物心情的烘托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小說選取了一個特定的環(huán)境:“風(fēng)起雪飄”的室外、“夜半孤燈”的室內(nèi)——桌上“燈昏香盡”,床上“翡翠衾寒”“芙蓉帳冷”,再透過戲曲的彈唱,烘托潘金蓮內(nèi)心深處“形只影單”的凄苦之“冷”,比室外還要凜冽的“冷”!這一段凄美彈唱的穿插,使潘金蓮形象一下子豐滿起來,賦予了小說無窮魅力。
如此等等,舉不勝數(shù)。僅就以上幾例我們可以看到,《金瓶梅詞話》嵌入的大量詩詞韻文,乃是小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作者構(gòu)思時精心運(yùn)作的結(jié)晶。毫無疑問,它在小說中所起的藝術(shù)作用是相當(dāng)重要的。
(二)
前面說到,作品運(yùn)用詩詞韻文是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一種重要現(xiàn)象,不僅《金梅梅詞話》如此,在其之前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也如此,且之后的《西游記》、《儒林外史》、《紅摟夢》也同樣如此。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古代小說不僅僅長篇小說是這樣,就是大量短篇小說也具有同樣的特點(diǎn)。說明這種重要現(xiàn)象,已成為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具體文學(xué)表現(xiàn),它植根于中華民族土壤,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
詩詞韻文是中國文學(xué)的源頭和主要形式,在中國文化中有著重要地位,它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傳承和發(fā)展重任,已成為民族文化的血脈而充盈于世。以詩而言,從最早為消除勞動疲累的吟唱,到后來舞蹈的伴侶以及宮廷娛樂的需要,都有著其身影。人們甚至將它作為文化的經(jīng)典,把留存于社會的三百零五首詩,以“經(jīng)”的名義編成書冊而永澤今人。自《詩大序》提出“詩言志”的命題后,“詩”更成為歷代統(tǒng)治者和文人眼里的一種表達(dá)各種思想的武器。屈原用它抒發(fā)愛國憂時的憤怒,曹操用它抒發(fā)老驥不伏的雄心,還有那些竹林中生活的賢人,也大多用詩歌吟唱對社會的憤懣,直至陶淵明的出現(xiàn),用它作為遁入南山桃花源的門票。到了唐代,“詩”更發(fā)展成了文學(xué)的顛峰和主要的藝術(shù)形式。統(tǒng)治者用它延攬人才,文人們把它當(dāng)作幸福人生的“敲門磚”,詩浪滾滾,萬民亢奮。詞被稱作“詩余”,乃是詩的創(chuàng)作之延續(xù)和發(fā)展,在唐五代宮廷之享樂生活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成為“緣情”的華章,經(jīng)過溫庭筠、李煜、柳永、蘇軾、李清照、辛棄疾以及吳文英等人的打磨,更成為人們?nèi)胄娜肭榈奈幕d體。后來的諸宮調(diào)和散曲乃至戲曲,無不與其發(fā)生著極為密切的文體聯(lián)系。韻文作為詩詞的別類,也在同時由娛樂而迅速得到發(fā)展。所有這些,都為小說大量運(yùn)用詩詞韻文創(chuàng)造了最為基本的條件。
再從小說本身的發(fā)展來看,它是在唐代變文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誠然,文獻(xiàn)上最早被稱為“小說”的也許發(fā)生得更早,但它們僅是市井閭里間街談巷語之類,缺乏真正的文體意義,即使這些“小說”經(jīng)人整理而得到文字的記載,多數(shù)還是片言只語,從現(xiàn)代小說的意義來看,顯然與今天所定義的小說有著一個相當(dāng)距離。只有唐代變文,乃是通俗的文學(xué),僧人們出于宣傳而生動形象地講述,且往往用的是韻文吟唱方式。他們講述的那些佛本生故事中,既有情節(jié),也有人物,而且天馬行空,充滿了主觀意念,浪漫世界的虛構(gòu)以及理想世界的想象,都為小說的形成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礎(chǔ)。由唐代寺院中發(fā)生的這些“變文”,才是我國白話小說的源頭,與一些被人稱作是“文言小說”的筆記體作品劃清了界限。也正因此,它對后世白話小說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尤其是在小說的形式上,這種通俗的講唱體方式,直接為宋元小說的勃興,奠定了重要的藝術(shù)基礎(chǔ)。
至《金瓶梅詞話》誕生的晚明,已是中國小說發(fā)展的高峰時期。在它之前,已有《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著名長篇小說面世,差不多與它同時或稍后一點(diǎn),則有《西游記》、《封神演義》以及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說。在白話短篇小說方面,也有“三言兩拍”以及《歡喜冤家》等大量作品出現(xiàn),一波又一波,不時在文壇上形成了壯觀的發(fā)展景象。所有這些白話小說,都是在宋元小說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的。而宋元白話小說,又稱為話本小說,其主要特點(diǎn)是一種講唱文學(xué)。我們所說的話本,是指當(dāng)時的說話藝人,在向社會大眾講述各類新鮮有趣的故事時的一種文學(xué)底本,專供藝人們說話表演時使用。這類話本小說的一個基本特點(diǎn)是講唱,類似于現(xiàn)今茶樓或其他表演場所中常見的藝人說書一般。宋元時期的藝人,表演時邊講邊唱完整敘述某一故事。在“講”的時候,他們使用敘述體,以第三者或代言人的角色,客觀講述或評論小說中的各類故事情節(jié),而在講述完某個情節(jié)段落后要進(jìn)行吟唱,這樣的吟唱,按照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必須押韻的,其中的唱詞和韻文,用文字記錄下來,就是本文所說的詩詞韻文。《金瓶梅詞話》當(dāng)然不是話本小說,也并非供說話藝人口頭表演而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底本,它是由萬歷年代的文人獨(dú)立完成的一部文學(xué)名著。這個創(chuàng)作者是誰,由于歷史文獻(xiàn)的匱乏,我們至今還難以確定,但從學(xué)界提出的近六十位候選者來看,都是當(dāng)時社會上的大名士或是有知識的文化人,如王世貞、徐渭、屠隆等,無不是有名望的文學(xué)家,他們乃是社會精英,能夠進(jìn)入朝廷為官,詩詞歌賦的寫作當(dāng)然沒有問題。處在盛行小說等通俗文學(xué)的時代氛圍中,他們又能接觸大量的民間文學(xué),諸如小說和話本等等,大家熟知的馮夢龍和凌濛初就是這樣的人物。《金瓶梅詞話》的作者,在廣泛吸收前人創(chuàng)作的各類文學(xué)基礎(chǔ)上,綜合個人的學(xué)養(yǎng)寫作,這才完成了這部優(yōu)秀小說。在這一創(chuàng)作過程中,他既有詩詞韻文的寫作能力,又借鑒了宋元及明代初、中期時盛行的一些小說講唱體文學(xué)模式,從而完成了《金瓶梅詞話》的寫作。
由此看來,詩詞韻文在《金瓶梅詞話》中的大量運(yùn)用,并不是作者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積淀著深厚的中國文化的精神血緣,其源遠(yuǎn)流長的文化淵源清晰可尋。
(三)
對于文學(xué)的民族性,以我有限的認(rèn)識,要講清這個問題實(shí)屬不易。常識告訴我們,所謂文學(xué)的民族性,實(shí)質(zhì)上就是文學(xué)的個性。不過,這樣的個性卻是帶有民族集體的特點(diǎn),這種特點(diǎn)也就是民族的一種群體人格,也即一個民族特有的思想、情操、習(xí)慣及行為方式,這種民族文化特點(diǎn)上共同的心理素質(zhì),是在歷史的發(fā)展長河中積淀而成。這種民族性呈現(xiàn)于文學(xué)上的主要特點(diǎn),可在內(nèi)容和形式這兩個密不可分的層面上得到充分的展現(xiàn),兩者及其多種因素相互統(tǒng)一融合,并且相異于其他民族的總的個性。一部文學(xué)作品,其民族特點(diǎn)表現(xiàn)得越鮮明,表現(xiàn)手法越趨成熟,這部作品就越具民族性。也就是說,文學(xué)作品的民族特點(diǎn)愈鮮明成熟,就愈具民族性。因?yàn)槲膶W(xué)是藝術(shù)的一個門類,屬于社會意識形態(tài),它是用語言文字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會生活、表達(dá)作家思想感情,它與民族的語言文字、心理狀態(tài)、文化傳統(tǒng)等等方面都有著直接的影響。
就本文討論的小說,《金瓶梅詞話》詩詞韻文的運(yùn)用這一重要文化現(xiàn)象,顯然不能用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之一等分析輕筆帶過,而是滲透了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學(xué)的精神血脈,雖然其表象僅僅只是屬于藝術(shù)形式的范疇,然而其美學(xué)意義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文學(xué)的本身。當(dāng)我們將它與西方的古代小說相比,即會發(fā)現(xiàn)這種文化現(xiàn)象無疑是中國古代小說所獨(dú)有的,用句流行語說,即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xué)作品,也即人們常說的文學(xué)的民族性。這里試舉例說明。
《金瓶梅詞話》第二回《西門慶簾下遇金蓮,王婆子貪賄說風(fēng)情》,小說敘寫男主人公西門慶初見潘金蓮時被她的美貌折服,這也是女主人公的首次登場。小說描寫其外貌極有特點(diǎn),其中的“打扮”就用的是詩詞韻文表述:
頭上戴著油油頭發(fā)鬖髻,口面上緝著皮金,一徑里踅出香云一結(jié)。周圍小簪兒齊插,六鬢斜插一朵并頭花,排草梳兒后押。難描八字灣灣柳葉,襯在腮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夸,露菜玉酥胸?zé)o人介。毛青布大袖衫兒,折兒又短,襯湘裙碾絹綾紗。通花汗巾中兒邊搭刺,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重重紐扣,褲腿兒臟頭垂下。往下看,尖趁趁金蓮小腳,云頭巧緝山牙,老雞鞋兒白綾高低,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營鶯花,行坐處風(fēng)吹裙袴。口兒里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挑初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散,賣弄雜偏俏的冤家!
這段韻文所寫,乃是西門慶眼中潘金蓮的穿著打扮,從頭寫到腳,包括佩帶的飾件等等,一件件歷歷在目,可見西門慶觀察之細(xì)致,這倒也很能透出人物的性格。因?yàn)槲鏖T慶見到風(fēng)情萬種的潘金蓮,驚艷萬分,頓起歹心,故對她的觀察也格外細(xì)致,并且一一把她記在心里,甚至恨不得一口把她吞進(jìn)肚里。毫無疑問,這段韻文的運(yùn)用,對于刻畫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性格特征十分傳神。
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由羅玉君翻譯的法國文學(xué)名著《紅與黑》,其中也寫到小說的女主人公市長夫人德·瑞那太太外貌,這是她初次出現(xiàn)時給人留下的鮮明印象:
她是一個窈窕的少婦,長得豐滿合度,端正秀美。她年輕的時候,曾經(jīng)是本地的美人兒。山村里人個個都這么說。她有某種純潔樸素的儀態(tài),而且有像少女般的嬌艷。根據(jù)巴黎人的眼光,她這種天然的風(fēng)致和美貌,流露著無限的活潑和天真,使人想到她生就是溫柔的、甜蜜的。如果她真的明白她自己這種優(yōu)點(diǎn)的話,德·瑞那夫人要感到非常的困窘和羞恥的。因?yàn)樵谒母邼嵉男睦铮瑥膩頉]有殷勤獻(xiàn)媚,或者矯揉造作的感情。
在這段藝術(shù)描寫中,小說敘述女主人公德·瑞那夫人的美貌,盡管也使用了“秀美”“嬌艷”“美貌”和“天然”“風(fēng)致”等形容詞,為以后的情節(jié)發(fā)展作有力的鋪墊,但小說運(yùn)用的視角卻是十分客觀的,乃從第三人或叫代言者的角度去進(jìn)行細(xì)致地刻畫。小說運(yùn)用的文體全為非韻化的,句式也長短不一,充分散文化,與描寫潘金蓮的韻文文字截然不同,這里我們就可看到中西文學(xué)的區(qū)別了。同樣的情形也出現(xiàn)在俄羅斯文學(xué)中,托爾斯泰對卡列寧夫人的外貌有以下精彩的描敘:
帶著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這位婦人的風(fēng)姿,渥倫斯奇就辨別出她是屬于上流社會的。他道了聲歉,就走進(jìn)車廂去,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這并不是因?yàn)樗浅C利悾膊皇且驗(yàn)樗孔藨B(tài)上所顯露出來的端麗和溫雅,而是因?yàn)樵谒哌^他身邊時她那迷人的臉上的表情帶著幾分特別的柔情蜜意。當(dāng)他回過頭來看的時候,她也掉過頭來了。她那雙在濃密的睫毛下面顯得陰暗了的閃耀著的灰色眼睛親切而注意地盯在他的臉上,好像她在辨認(rèn)他一樣,隨后又立刻轉(zhuǎn)向走過的人群,像是在尋找著什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渥倫斯奇己經(jīng)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壓抑的生氣在她的臉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彎曲了的輕微的笑容之間掠過。仿佛有一種過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違反她的意志,時而在她的眼睛的閃光里,時而在她的微笑中顯現(xiàn)出來。她故意地竭力隱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輝,但它卻違反她的意志在隱約可辨的微笑里閃爍著。
這段文字所描寫的文學(xué)情景和上引《金瓶梅詞話》完全相同,小說也是借助于男主人公渥倫斯奇的眼光去觀察卡列寧夫人。然而,小說所采用的方式乃是客觀理性的敘述體文字,是以第三人稱的角色向讀者描述卡列寧夫人的美貌。這種形式與司湯達(dá)的《紅與黑》完全相同,而與中國古代的小說名著《金瓶梅詞話》迥異。中西文學(xué)的不同描述如此鮮明,我們在驚嘆之余則深深思考,這些都說明文學(xué)的民族性是一個客觀的存在,《金瓶梅詞話》所體現(xiàn)的這種文學(xué)的民族性,只不過是我們選擇了一個不錯的樣本而已。
誠然,在這部小說中,托爾斯泰也有詩詞韻文的運(yùn)用,不過這種運(yùn)用比起《金瓶梅詞話》簡直是不值一提。小說全書共分八部,其中的第一部有三處詩詞的運(yùn)用:一處是對古希臘抒情詩人安那克來翁之詩的引用;另一處是對奧地利音樂家斯特勞斯的歌劇《蝙蝠》中四句唱詞的引用;還有一處是兩句詩的朗誦,目前我們找不到這兩句詩的出處,有可能是作者的自創(chuàng),這里姑且算在之內(nèi)。即使這樣,也僅僅是如此。在十萬余字的篇幅中,它所占的比例則是滄海一粟,可不去說它。更為重要的是,托爾斯泰運(yùn)用這些詩句,只不過是信手拈來的隨意點(diǎn)綴,沒有什么明顯的創(chuàng)作意圖,這與《金瓶梅詞話》中詩詞韻文有目的地運(yùn)用,構(gòu)成全篇宏大的藝術(shù)結(jié)構(gòu)中的重要一環(huán)之情形迥然不同。中外文學(xué)的文化呈現(xiàn)著很大的差異性,文學(xué)的民族性,在這類世界文學(xué)名著中再一次得到深刻印證。
所有這些都說明,文學(xué)的民族性是一個民族文學(xué)藝術(shù)成熟的標(biāo)志,也是一種民族文化的形象路標(biāo)。當(dāng)然,我們所說的文學(xué)的民族性是相對于文學(xué)的世界性而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早已為歷史所證明了的一個普遍真理。民族文學(xué)是世界文學(xué)的基礎(chǔ),而世界文學(xué)也只有建立在民族文學(xué)的土壤中才能獲得認(rèn)同。文學(xué)的民族性是文學(xué)的世界性的基礎(chǔ),而文學(xué)的世界性也只有在文學(xué)的民族性充盈后才能形成。任何一個民族的優(yōu)秀文學(xué),相對于其他民族的文學(xué)來說,總是具有鮮明的個性特點(diǎn),因?yàn)樗谛纬蛇^程中,凝聚著民族文化的精華。因此,愈是具有民族性的文藝作品,也愈具有世界意義。當(dāng)然,這里提倡的文學(xué)的民族性,并不排斥吸收其他民族文學(xué)中的有益東西。
中國古代小說在表現(xiàn)本民族生活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符合本民族群眾審美理想、審美習(xí)慣的一種屬性,這種屬性突出地表現(xiàn)在本民族的杰出作家的優(yōu)秀作品中,《金瓶梅詞話》就是這樣的小說。我們在探討它的民族性時,所涉及的雖然只是小說在藝術(shù)形式上的一個小小的“點(diǎn)”,但人們可以透過小小的“點(diǎn)”,看到它所呈現(xiàn)的一種強(qiáng)烈的民族性。也正如此,小說《金瓶梅詞話》在今天已不僅僅是中國的了,它應(yīng)該是世界的,就是對它的研究,也已經(jīng)走出國門,在世界學(xué)術(shù)史上占有了自己的地位。我們今天研究小說《金瓶梅詞話》和它的民族性,其意義也正是在這里。
注:
① 陳益源、傅想容《〈金瓶梅詞話〉征引詩詞考辨》,《昆明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0年第5期。
② 潘慎《〈金瓶梅〉的詩詞創(chuàng)作和它的作者》,《太原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2年第1期。
③ 全冉粉《〈金瓶梅〉兩個版本引用化用詩詞的統(tǒng)計(jì)分析》,見http://www.mqxs.com/thread-2111-1-1.html
④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
⑤ 張進(jìn)德《〈金瓶梅詞話〉中的散曲》,《明清小說研究》2007年第1期。
⑥ 劉孝嚴(yán)《〈金瓶梅〉男女之欲描寫的文化內(nèi)涵》,《吉林大學(xué)社會科學(xué)學(xué)報(bào)》2001年第6期。
⑦ 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xué)史》,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
⑧ [宋]釋惟白《續(xù)傳燈錄·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
⑨ 楊鴻儒《細(xì)述金瓶梅》,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
⑩ 小慶《奇淫之辯,正邪之爭——鄙人妄論〈金瓶梅〉》,重慶大學(xué)民主湖論壇http://www.cqumzh.cn/bbs/viewthread.php?tid=386602wthread.php?tid=386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