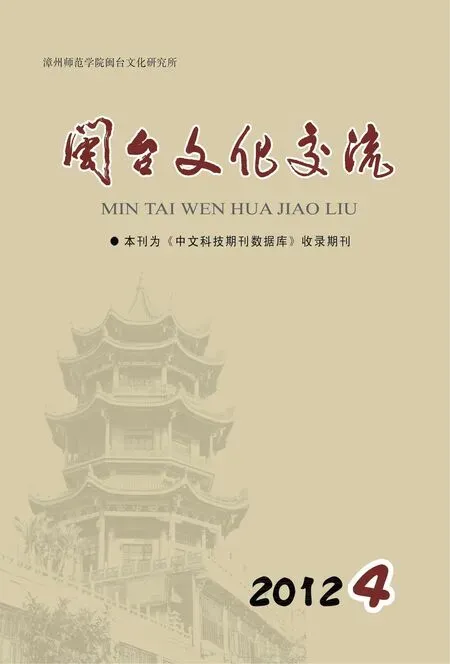淺析朱熹陳淳理學思想對漳州民俗的影響與意義*
鐘建華
南宋,理學思想能夠對于漳州地方文化產生較大的影響,主要歸結于兩方面緣由:一是宋光宗紹熙元年 (1190)“大儒”朱熹出守漳,踐行其政治抱負與理學思想傳播;二是 “北溪先生”陳淳對朱熹理學思想的繼承、身體力行與通俗化闡釋。漳州地方民俗正是在這兩位理學大家的 “窮理格物、下學上達”的理學體驗、闡釋、傳承與實踐過程中受到諸多引導與整肅,從而發生了移風易俗,乃至一直影響到后世幾百年。
一、朱熹治漳期間對漳州民俗的引導與影響
漳州世稱 “海濱鄒魯”,實是肇始于南宋,與朱熹陳淳師徒有莫大關系。首先,后世的漳州人常常夸耀本地為朱熹的過化地,并深以為豪,早在明季,漳州著名鄉賢黃道周就曾宣稱:“吾鄉海濱鄒魯,勞夫蕩槳,漁婦織網,皆能詠唱歌詩。 ”[1]《福建通志·風俗·漳州府》中關于朱熹守漳的事件則更有大段記載:“郡自朱子作牧,敦以詩書,澤以禮讓,冠婚喪祭一裁以正。其時君子以文學氣節自高,小人亦循分守業,廣好義以事其上。爭斗不施,訟獄衰息”。[2]由此可見,朱熹雖然只擔任漳州地方長官短短一年的時間,但是無論是在理學思想文化傳播,還是在地方治理與風俗規范等方面,對漳州及其后世的影響都是不容小覷的。
就漳州民俗規范而言,清代康熙版《龍溪縣志》保存了朱熹治理漳州時發布的一些文告與禁約,其中主要有 《有宋郡守朱熹曉諭詞訟教》、《曉諭居喪持服教》、《勸女道還俗教》、《喻俗文》等,[3]這里以 《喻俗文》為代表,結合其他文告內容進行歸納,從而探索朱熹如何從日常生活的各個角度對于漳州地方社會做出了約束與引導:
其一、勸喻保、伍之內,提倡孝、恭、和與順,勸戒奸、盜、飲博、打斗與論訴;恩威并施,倡揚義夫節婦,孝子順孫。
其二、保、伍之內,禁約常切水火、盜賊、斗爭,不得販賣私鹽、宰殺耕牛、賭博財物、傳習魔教;知糾并行,知而不糾并行坐罪。
其三、勸喻士民,倡揚孝悌、嚴正婚姻、親睦鄰里未可輕易論訟。
其四、勸喻官戶,以身表率,循理克己。
其五、勸喻遭喪之家,居服有禮,豐儉隨家,及時安葬。
其六、勸喻男女、寺院、民間,不得以修道為名,私創庵寺,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廝混,應及時婚姻。
其七、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之名,斂掠財物,裝弄傀儡。
從以上內容來看,涉及漳州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明南宋漳州除了存在與其他地方共性的陋俗外,還存在諸多的特殊風俗,比如傳習魔教、傳經禮佛之風甚盛,好淫祀,熱衷迎神賽會,婚姻不嚴,葬禮浮華等。對于朱熹而言,一方面是漳州地方最高長官,保障地方安寧是第一要務;另一方面,地方的治理是其理學思想的實踐與體現的最好載體。以下分析朱熹是如何在官員與理學思想大家的雙重身份下,對于漳州地方風俗做出規約與引導:
首先,發布勸喻與勒石禁約這兩種方式,是地方長官的權力所在,地方長官的身份保證了這兩種規約手段具有一定的官方權威,現存如此多文告,顯示了朱熹很重視這兩種宣傳與規范方式。
其次,朱熹在勸喻與禁約的文告中,直接標注了懲戒的手段與后果。輕微懲戒直接用 “不得”、“勸戒”、“所宜深念”這樣的勸誡語言;造成嚴重后果的則直接列舉懲罰的名目,如坐罪遭刑、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民不得應舉等;對于義夫節婦,則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恩威并施,以確保勸喻與禁約的推行效果。
其三,朱熹作為理學大家,其骨子里還是認為刑法治標不治本,而認為儒學的性本善,所提倡的 “忠孝悌節義”才是社會安寧的根本所在,因此,在這些具體的勸喻與禁約中,朱熹都是先苦口婆心的闡述他對于導致前述的勸喻與禁約內容的本原的理學看法,比如 “勸喻士民,當知此身本于父母,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愛親敬長者,皆本心之自然。”[4]等。
其四,對其他宗教與鬼神問題,朱熹秉承的是 《禮記·祭法》的原則,因此在《喻俗文》中,涉及到其他宗教與民間宗教的行為勸喻的實有三則,對于淫祀,自然直接用 “不得”加于禁止,對于正神祭祀,則 “敬鬼神而遠之”,合理簡單最好。
其五,漳州民間至今留存了許多朱熹治漳的故事傳說,其中 “塔口庵的來歷”[5]講述的是朱熹如何通過勘查與破壞了 “塔口庵”的 “美人穴”風水,來矯正當時漳州地方人倫亂、婚俗雜的民間故事,同時也解釋了漳州至今仍殘留的 “文公巾”、“文公拐”的來歷。此則民間故事可以與 《喻俗文》相印證,說明朱熹針對漳州婚俗的勸喻對于后世的影響頗大。
二、陳淳對漳州地方風俗的影響
對于朱熹理學思想直接的有力繼承者陳淳而言,師徒之間關于理學的兩次重要切磋,恰恰在某個側面反映了理學是如何從思想文化的層面落實到漳州地方社會治理的全過程:其一,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陳淳第一次求見朱熹,朱熹授以“根原”,說 “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其二,寧宗慶元五年 (1199),陳淳再謁朱熹于考亭,朱熹已寢疾,語之曰:“如公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6]這兩次指點,體現在陳淳身上,除見 《北溪字義》對程朱理學的層層闡述外,從陳淳對漳州地方治理的獻言獻策,以及當時人及其后輩對陳淳的評價,可以考析陳淳的治學與實踐所秉持的理學思想,對漳州地方風俗的引導與影響。
(一)《北溪字義》通俗化闡釋特色的價值
《北溪字義》是陳淳根據自己對于程朱理學思想的學習與現實生活的體驗相結合的產物,所謂下學上達,且傳播甚廣:“溫陵諸葛玨來莆,一目是書 (即 《北溪字義》),恨見之晚。歸,鍥板以惠同志。”“北溪翁從之游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率延之往教。”[7]實實在在地影響了一批閩地的理學思想后學者。該書對理學核心概念的闡述最大的特點除了忠實的演繹程朱的經典話語外,主要結合了陳淳對 “日用常行”的體悟。所謂 “日用常行”,簡單點說,就是日常倫理生活,人情世故、舉止行為等等。身為漳州人的陳淳,對程朱理學思想的通俗化闡釋,不可避免的帶有了漳州地方生活內容的痕跡。尤其是 《北溪字義》中的 “鬼神(神魄附)”章節,顯然與漳州地方好 “淫祀”之風的體驗有緊密的關系,因此陳淳才能夠有感而發,從程朱對于 “神鬼為陰陽二氣而來”的演繹,到孔夫子的 “敬鬼神而遠之”的解釋,一直談到 “淫祀無福”、 “非禮勿祭”等命題。[8]
(二)陳淳對漳州地方治理的建言與自我示范
“致知力行”是陳淳在其 “用功節目”章節中,對 “道理”學習的總結。“力行”對個體自我而言,在于如何 “格物致知”,以致身與事相安捍格無礙,即人情練達,即側重于 “修身”;對個人之于社會而言,在于 “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陳淳不可避免的要通過自我的行為示范,來展現自身的理學涵養;因為自己是儒者且白身,故而通過建言來表述其對漳州地方社會治理的看法。
1、《宋史·陳淳傳》對陳淳的評價,即是陳淳自我示范的最好表達
《宋史·陳淳傳》把大部分的文字都放置在陳淳如何與其師朱熹切磋理學學問上,對他個人的描述寥寥無幾,但是還是點出了其中重要的幾方面表現[9]:
其一,侍母至孝;其二,悌愛弟妹;其三,義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其四,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
“孝、悌、義”是儒學的人倫道理的根本所在,被認為是屬于人之天性,根據程朱理學的解釋,只要道學圓通,這些倫理都會自然凸顯的,尤其是孝道,是儒學倫理的根基,這點,《宋史》對陳淳的個人行為是持肯定態度的,符合其儒者風范,也符合其以身作則的儒者表率作用。而 “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然憂時論事,感慨動人。”此翻版于《論語·鄉黨第十》中稱贊孔子所謂的 “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唁唁如也。君子,椒錯如也,與與如也。”世論陳淳,謂之最大貢獻在于忠實闡釋朱子理學以及捍衛師門道統,宋史的評價大概立足于此,因此對其個人的描述顯得清寡。
2、陳淳對漳州地方風俗的建言
現存陳淳對漳州地方治理的建言在清代康熙 《龍溪縣志》里有兩則,分別是《宋陳淳上傅寺丞論民俗事》與 《又上傅寺丞書》[10],主要涉及到的地方問題有:
其一,地方健豪訟棍問題;其二,潑皮無賴折合之風;其三,盜殺耕牛與盜賊的問題;其四,驕僧大寺問題;其五,江湖游民與術士問題;其五,淫祀、作淫戲及搬弄傀儡等風俗。
陳淳認為地方最好的風俗狀態是:“民志定、民財紓、民風厚、民訟簡。”[11]對于執政者之風的贊賞則為:“闔郡四境實被賢侯安靜和平之福”。[12]陳淳作為漳州地方人士,自然比朱熹更清楚其時漳州地方風俗之弊端,因此,其回應傅寺丞的建言的內容也比朱熹更深入更切近社會問題的要害,不再是從 “孝悌”等基本問題談起,而是直接切入漳州地方當時最嚴重的擾民事件所在。陳淳的上書,含有比較強烈的 “治國平天下”的儒家面對社會的政治行為,而不再強調 “修身、齊家”這樣的偏向個體的道德倫理約束。這兩則建言都是大白話,幾乎見不到相關的理學思想的論述,是一種落實到社會實際,憂時論事且熱切盼望地方長官能夠因此切實解決漳州地方問題,進而風厲當地民俗的儒家行為作風。
3、陳淳對淫祀與搬弄傀儡尤為反感的原因分析
眾所周知,中國的儒家思想的物質基礎在于農業社會的支撐。安靜平和,四時有序、君賢民樂是儒家理想的社會狀態。而漳州地方的淫祀所帶動的一些列活動,在陳淳看來,其一方面確實擾亂了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則潛在隱藏著嚴重的社會危機與思想根源危機。
首先,淫祀不符合程朱理學里面所強調的祭祀法則,與禮相悖,即所謂的名不正言不順,因此陳淳對于漳州乃至整個閩地好淫祀,深深的不以為然,因此,在其回應傅寺丞的上言中,明確表達了應該嚴格禁止淫祀的意愿。
其次,淫祀另一個可怕的附帶活動就是搬弄傀儡或聚眾乞冬演戲。但凡祭祀以及相關的娛神活動,必然需要民眾的諸多財物支撐,才能得以開展,因此,裝神弄鬼掩護下的斂財與浪費是其中不可避免的兩大弊端。更可怕的是,地方民眾非常熱衷于這種迎神賽會,貢獻錢財也非常慷慨,而且這種活動是有組織的民眾活動。陳淳忌憚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迎神賽會一旦被人利用,引起的后果自然不堪設想。
其三,淫祀掩蓋下的迎神賽會活動,不但是娛樂神明,還娛樂了大眾。男女老少因此蜂擁蟻聚,引發的諸多作奸犯科之事,如玩物喪志、作廢本業、淫奔、斗毆、搶劫、訴訟等,概而言之,“人心 (因此)波流風靡無由而止,豈不為仁人君子德政之累?”[13]說到底,淫祀問題影響到了理學根基的穩固等大問題。
結 語
朱熹、陳淳師徒的勸喻、規約與建言,內容雖有所差異,形式也不盡相同,但是目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漳州社會安寧,民眾和平,四時有序,風清政簡。這當然是理學思想家們心目中一種理想化的社會狀態或者風俗情形,也是儒家 “以德治國”所欲達到的一種理想狀態。此種理想狀態落實到實際是要打一定折扣的,但是,我們從現存的文本記錄以及民間口傳文學來看,朱熹與陳淳師徒的一系列勸喻與建言,至少在懲治漳州地方惡僧,打擊寺院兼并經濟,整肅婚姻禮儀,打擊淫祀、淫戲,規整社會秩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此才會為后世留下相關的民間故事傳說與文化遺留,如 “(朱熹)計除開元寺惡僧”、“庵口塔的來歷”、“朱熹點破蜈蚣穴”、“文公拐”、“掛竹隔仔習俗”、“文公帕”等[14],陳淳的建言則對于漳州的淫祀與地方戲曲的禁絕有較大影響。就漳州地方社會的整體風氣而言,朱熹與陳淳師徒對漳州地方社會的引導與規約,經過后世一代代的塑造與傳承,其影響是不言而喻的,至今可見痕跡。
注釋:
[1]http://baike.baidu.com/view/5439449.htm。
[2]清·陳壽祺:《福建通志》(同治十年重刊影印本),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1147頁。
[3][4][10][11][12][13]清·康熙姜國棟修;陳遠麟、莊亨陽、蔡汝森纂:《龍溪縣志》,漳州市圖書館2005年2月影印本,282~285 頁。
[5][14]漳州市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漳州分卷(二)》,(87閩出管準印證第13~1800號,1992年 5月),85~103頁。
[6][9]元·脫脫、阿魯圖等編著:《宋史》卷四三○《列傳第一百八十九·道學四·朱氏門人·陳淳傳》,中華書局1985年6月版。
[7][8]宋·陳淳:《北溪字義》,中華書局 2011 年 3 月版,第88頁、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