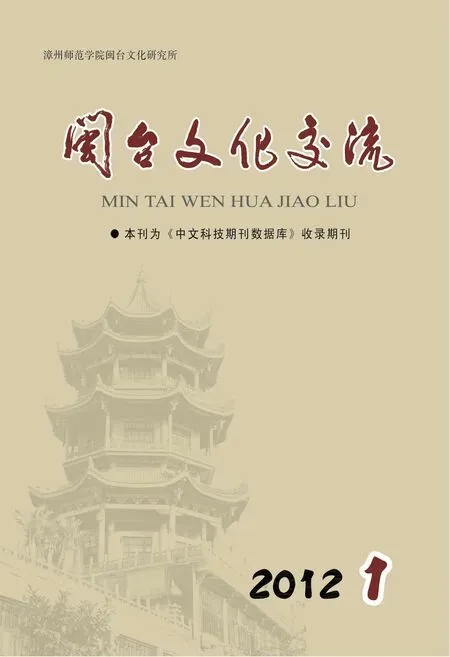千帆過盡是滄桑——由《金門百年庶民列傳》看金門百年變遷
康玉德
(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
今辛亥革命百年之際,金門縣文化局隆重出版了一套叢書,取名 《金門百年庶民列傳》。辛亥革命后,金門經歷了民初盜匪猖獗、民風愚昧時期,日軍占領時期,國民黨軍隊大量進駐后實行的戰地政務時期,解嚴后開放旅游觀光時期。不同歷史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給金門社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叢書作者通過親身采訪一個個事件的親歷者,以訪談錄的體裁,忠實記錄了不同歷史時期金門百姓所經歷的不同人生和命運,透過一篇一篇的訪談錄、一個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歷史金門社會所經歷的滄桑巨變。
這套叢書一共6本:本土篇 《風雨江山》,作者李福井,資深媒體人、文史作家,收錄采訪錄12篇,絕大多數受訪者年齡在70至90歲之間,他們生在金門,長在金門,是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婦女篇 《戰地阿嬤》,作者陳榮昌,曾任 《金門日報》采訪部主任,收錄采訪錄25篇,采訪對象都是八九十歲的婦女,她們不一定都生在金門,卻都長在金門,從她們身上可以看到逆來順受、任勞任怨的女性特有的人格特質;媳婦篇 《浯家新婦》,作者周妙真,金門技術學院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收錄采訪錄15篇,采訪對象都是晚近嫁到金門的外來新婦;經濟篇 《金色年代》,作者李福井,收錄采訪錄17篇,重點反映解除戒嚴開放觀光后金門經濟發生的變化;遷臺篇 《東渡之歌》,作者楊樹清,報告文學作家,收錄采訪錄20篇,反映當代金門人移居臺灣后各自不同的人生經歷;南洋篇 《獅城人語》,作者呂紀葆 (筆名寒川),作家,旅居新加坡,收錄采訪錄12篇,反映移居新加坡的金門人在新加坡工商界的奮斗歷程和目前他們各自的生活狀態。
五位作者共同出一套6本的叢書,如此規模金門縣文化局多年來的出書計劃中是少見的;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福建省政府主席”薛承泰,金門縣長李沃士、金門縣文化局局長李錫隆分別為叢書寫序,這樣的規格也是前所未有的,可見臺灣和金門各界對這套叢書的期盼和重視。僅憑這兩點就該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
以下筆者將根據閱讀結果所作的整理和分析,對百年金門庶民生活做一個粗淺的梳理。每篇訪談錄受訪者大多只有一個,其姓名有的書出現在正標題中,有的書出現在副標題中,筆者引文時僅以該文所屬書名和受訪者姓名指代,比如 《風雨江山》中《騾馬夫之歌——蘇天庇變調的青春》一文,以《風雨江山·蘇天庇》指代。
一、清末民初時期
清末到辛亥革命之前的金門社會,一是貧窮,二是民風愚昧。其后的辛亥革命和北伐,并不能給金門社會帶來什么深遠的影響,所以從辛亥革命開始的1911年到日軍占領金門的1937年,金門社會的狀況基本上延續了辛亥革命之前的狀態。
看看陳榮昌筆下李知的幼年窮苦生活往事:“為了尋找可供燃燒的草木,她們常常徒步越過大半個西半島……辛苦扒來的草木……背負在身上帶回家……往往壓得瘦小的母女幾乎喘不過氣。帶回家的草木,細小的就留下來當柴火燒,粗大如芒草……便拿去叫賣,好換取水肥種田。此外為了補貼家用,李知從小便跟著家人到古寧頭海邊擎蚵、剝海蚵……由于長期浸泡海水,李知的手指都長出 ‘凍子’,紅腫疼痛不堪。”(《戰地阿嬤·李知阿嬤》)。甚至于說 “早年金門到處是乞丐。”(《風雨江山·李清燦》)。
貧窮導致愚昧。如重男輕女傳統觀念下引發的交換、走私販賣孩童現象:“為得一子好傳宗接代,鄉人拿女兒換兒子。沒女兒的就用金子換。為了賺金子,金廈海域變成人口販子的天堂……海域上不時可見舢板來往,運載著從大陸各地走私的孩童……孩童被麻布袋裝著,忍受著惡劣的海上風浪,遇到政府海上盤查,人口販子為消滅證據,只能將包著孩童的麻布袋一一扔入海中。幸運逃過一劫的,成了島上鄉親認購的傳宗物。”(《戰地阿嬤·王寶玉》)
孩子是別人的,常有虐童現象。“早年,金門大戶人家時興由廈門買來女娃當 ‘妯干’(婢女)。幸運的,獲得人道對待,不幸的,則會被主人苦毒虐待。……地板掃不干凈,主人會壓著她們的頭去舔地,衣服沒洗凈,手指就會被主人用木棒狠打。辛苦工作一整天,吃的是 ‘豆細湯、咸菜尾’。有的受不了虐待之苦,乘機逃走,被抓回來后,免不了又是一陣毒打,有的還被主人用雞籠罩住,再用干草悶燒,哀號啼哭的慘狀,楊黃宛想來就痛心。”(《戰地阿嬤·楊黃宛》)
在金門謀生不易,于是很多男性青壯年遠赴南洋打工。“金門本身土地貧瘠、謀生不易,金門民眾紛紛往南洋發展,金門人稱為 ‘落番’。”(《戰地阿嬤·黃為治》)大多在各地從事繁重的苦力,如在條件惡劣的工廠里做工,或在碼頭做搬運工,或在橡膠園里從事體力,他們省吃儉用,把省下的錢寄回家鄉養活老小。可是,“有余力匯錢回家鄉的,實在少之又少。”(《戰地阿嬤·楊陳瑞吾》)再如林洪蔭唯一的弟弟“落番下南洋做工賺錢,剛到異地時還有寄錢回金,后來生活狀況不好,也就沒再寄回,最后魂歸異域。”(《戰地阿嬤·林洪蔭》)金門有句俗諺 “六亡,三在,一回頭”正是這時候下南洋苦力的寫照。當然也有少數事業有成賺了大錢后回金門蓋起洋樓或兩落、三落大厝,光宗耀祖。現今金門島上不少洋樓就是那個時候建造的。
然而凡事都有利弊兩面。“金門當年的縣衙就設在現今的清遺金門鎮總兵署里,只有十幾個黃兵,保衛衙署安全,海岸根本沒駐軍,不設防,既無電話,也沒馬路,幾成無政府狀態。”(《風雨江山·薛自然》)所以發家致富的番客成了內地賊匪的盤中肉,金門社會綁票成風。縣志記載,1925年1月至4月,金門沙美一帶,盜案就發生43起之多。如洪甜桃 “因為娘家富有、谷倉多,引來旁人眼紅,洪甜桃七、八歲大時,還發生青岐人勾結同安強盜到家里搶劫的事,祖父母任其劫掠,但求不傷害家人。”(《戰地阿嬤·洪甜桃》)1933年秋金門前水頭黃廷宙和黃順圖兩家同時遭內地強盜綁票案,李福井 《風雨江山》中有專門描述,甚至附有受害者后代保存了近八十年的陳情書和失單的影印件,從中可大致明白黃家所受巨額損失。
二、八年日據時期
1937年10月26日,日軍占領金門,開始了金門歷史上最黑暗的八年。百姓生活更加困苦。“金門百業蕭條,人民生活困苦。市區商家因為沒生意可做,都關門大吉,要買個糧食都無處可買。”(《戰地阿嬤·張淑賢》)老百姓 “沒東西吃,很辛苦,都吃地瓜葉。”(《戰地阿嬤·洪吳罔飼》)(《風雨江山·李清燦》)“那幾年金門僑匯全斷絕,依靠僑匯過日子的人家更辛苦,只能以物易物,拿出上好衣褲到鄉下和農人交換糧食,勉強維生。”(《戰地阿嬤·張淑賢》)
日軍占領金門之前,一部分金門百姓已事先逃走。“家境許可的,在日軍登陸前,大都會在家人安排下,趕緊逃往南洋避難。 ”(《戰地阿嬤·黃為治》)
日軍強行登島,一上島就濫殺無辜:“在古崗殺了一名聾子;在金門城殺害了一名男子……另一位則是后浦東門人家的丫鬟,在歐厝不幸被殺。”“村民能逃的都逃走了,不能逃的也都躲到村郊的草叢中,日軍進到村莊……手持步槍,上著刺刀,沿著村郊四周進行搜索,遇有草叢,就往草堆中亂捅。”(《戰地阿嬤·歐廷連》)還常常胡作非為:“日本人很壞,拿刀插豬、雞,說要見血,不然會 ‘衰’。”(《戰地阿嬤·洪吳罔飼》)“黃為治就曾聽過水頭女孩不幸被日本兵凌辱的事情。”(《戰地阿嬤·黃為治》)還勞民傷財,征用民工。張淑賢回憶回憶:“日本兵對百姓很嚴厲,為構筑工事,需要人力,因此到處找人做苦工,她丈夫那時也被日本軍隊強迫征調到金寧鄉安岐村一帶興建機場。”(《戰地阿嬤·張淑賢》)1945年6月日軍大佐德本光信率軍從金門出發,經由海澄、漳浦、云霄、詔安撤至潮汕地區,出發前從金門民間強行征用五百騾馬和騾夫,騾馬無一生還,當時騾馬不是普通百姓家能輕易擁有,給百姓造成巨額損失。騾夫沿途病死、累死、炸死的很多,最后能回到金門的只剩一半。這些騾夫在金門不被日軍當人看,在大陸被國民黨軍隊軍抓捕后,被認為為虎作倀,幾乎被殺。(見 《風雨江山·徐伴石》)
日軍還強迫金門百姓種植鴉片。“日本對種植鴉片控管嚴密,配了種子之后,先來看田坵的肥瘠,評估可以收成多少,分成甲、乙、丙三級。收成如不能達標,淪為丁級,那就有罪受了……鴉片籽可以留,但不許留太多,怕私種,萬一偷留偷吃被逮到……不承認打到承認,先承認了就從輕發落。”(《風雨江山·林金樹》)
然而,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以許順煌等人為代表的地下抗日分子是金門人的希望。他暗中與 “閩省綏靖公署”及 “國軍第二十五集團軍”聯絡,秘密從事地下情報工作,使金門復土救鄉團打擊日偽行動多有斬獲。尤其 “許順煌的抗日活動完全出自愛國心,不拿國家一毛錢。對于國家給的工作報酬,他還曾斥道,‘我替國家工作,是出于至誠,我不應該浪費國家的一文錢。’”(《戰地阿嬤·黃麗》)許順煌等人雖壯烈犧牲,但至誠愛國的精神將永遠激勵一代又一代金門人奮勇向前。
三、戰地政務時期
抗戰八年以日本戰敗告終,金門并沒有迎來新的改變,從1945年到1949年古寧頭戰役之前的四年時間,百姓依然生活在貧困當中。“那時候民不聊生,老百姓生活非常窮困,吃都吃不飽,穿也穿不暖,每天處在半饑餓狀態。”(《風雨江山·黃蘇源》)和抗戰之前一樣,搶劫綁票依然是這個時期困擾金門社會的一個老問題。“當年金門幾乎處在一種無政府狀態,那時有錢人回鄉,若被同安人知道,就會登門搶劫。 ”(《風雨江山·林金樹》)
由于國民黨當局在大陸忙于內戰,急需兵源和財源,頻繁的抓兵派款成了這時候金門的一個社會現象。“一九四五年保安隊地方軍首先來金門接收……保安隊每天收錢糧、抓壯丁……一九四六年起中原板蕩,國府開始向金門抽兵,連抽了三年。”“金門的菁英識時務者為俊杰,走為上策,紛紛下南洋——跑光光,只剩下莊稼漢苦撐……那時玩出一套機制,抽中頭簽的人如果不去,貼人四百斤油,二簽貼一百斤,三簽五十斤,普通的貼十斤、二十斤作為安家費。當年金融情勢混亂,都用油或美金折算,后來演變成職業賣壯丁——代人入伍,中途逃脫,一賣再賣。”(《風雨江山·黃蘇源》)不僅在地的金門人被抓去當兵,金門人外出也被抓去當兵。《風雨江山》有專文敘述金門人陳篤禧1947年到泉州做生意時遭抓兵的奇特經歷。
由于衛生條件和醫療措施都很差,金門時常爆發瘟疫。“一九四八年古寧頭戰役前夕,金門爆發鼠疫,父親蔡賜長不幸得病,就此辭世。”(《金色年代·蔡瑞炎》)
另外,這又是一個特殊的年代,抗戰剛剛結束,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因此金門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存在 “鋤奸”和 “抓諜”問題。“光復后求學時令她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卿仔’來自大嶝的許姓丈夫被以 ‘漢奸’罪名處決,學堂彌漫了不安,先是除 ‘漢奸’,再是抓 ‘匪諜’,這樣的恐怖氣氛延續到國、共內戰的一九四九年以后。”(《東渡之歌·陳燕治》)
1949年10月古寧頭戰役爆發前后,國民黨軍隊大量從大陸撤退駐守金門。由于沒有營房,部隊入住老百姓家里,給當百姓帶來很多不便,由此產生緊張的軍民關系。“金門鄉親又驚又怕。當時,家中的雞鴨、臉盆等,許多物品都被國軍私自拿去使用……薛明治家人也不敢向國軍要回這些被借用的東西,只好眼睜睜看著官兵取用這些物品……還是小姑娘的她們,連士兵都不敢正視,有些物品放在房間,因房間被軍隊占用,她們也不敢進去拿,怕惹來不必要的麻煩。”(《戰地阿嬤·薛明治》)林泡家 “老宅大廳被部隊軍官使用,神主牌被迫撤到廚房安放,一家人也只能搬到廚房或廂房睡,有時還會發生土豆油被搶,豬被士兵偷走的事,但時局混亂,大家都敢怒不敢言。”(《戰地阿嬤·林泡》)
不過,兵民相處一家,也有和諧的一面。如李知 “家里的官兵都很疼孩子,彼此相處頗為融洽……部隊看到李知的小孩,有的想起了遠在大陸的兒女,有的憶起自家弟妹,心里感到熟悉親切,都會搶著抱孩子去逗玩,或是塞個饅頭給孩子充饑。為表示感謝,逢年過節時,李知也會炊煮一些年糕紅粿,送給這群離鄉背井的部隊弟兄,聊慰思鄉之情,官兵們也會回贈軍用品,禮尚往來一番。”(《戰地阿嬤·李知》)
國民黨軍隊要構建防御工事,缺乏大量的建筑材料,很多從百姓家里拿現成的。“門戶都被部隊拆光,拿去做工事。”(《戰地阿嬤·洪吳罔飼》)甚至 “整棟房子硬生生地被國軍無償拆掉、移作碉堡工事建筑用。”(《東渡之歌·蔡能利》)而陳智景 “伯父陳清吉發南洋財,在后山蓋了一棟洋樓,雖免于被拆除的命運,但是屋內東西被搬一空,連門板也不剩一塊。”(《風雨江山·陳智景》)壯丁還被強迫幫忙構筑工事和抬傷員。 “戰前,臺灣來了洋灰,但是沒有碎石,壯丁每天都要到海邊撿碎石給國軍做防御工事……白天扛傷兵上山。”(《風雨江山·李清燦》)
隨著各類軍事防御設施的逐步完善,國民黨軍隊陸續搬出百姓家,這使本來有些緊張的兵民關系得到緩解。然而隨著防御措施的推進,國民黨軍隊在多處海岸埋下許多地雷,致使百姓誤觸地雷而傷亡的事件不斷發生,如今經常往來于兩岸的許燕先生,他的外婆和母親在1954年因誤踏地雷死亡,當時他才六歲。(《風雨江山·許燕》)
這時期百姓也有在炮戰中因為中彈死亡的,比如在1954年九三炮戰中,羅洪葉“養母在九三炮戰時不幸被炮彈打到,當時沒醫生,養母被炮彈打到后,感染破傷風往生。 ”(《戰地阿嬤·羅洪葉》)
1958年八二三炮戰給金門百姓帶來的影響最深刻,此次猛烈的炮戰持續44天,10月6日后開始停停打打,直到10月26日大陸宣布 “單打雙不打”,如此持續了20年。激烈的炮火下,金門百姓學會了各種辦法躲炮彈。有的 “由于家中沒有防空洞,只好踉蹌狼狽地抱著孩子,跑到別人家里躲防空洞……幾次之后……就不好意思再到別人家里躲防空洞,只能待在家里,就地找掩護。”(《戰地阿嬤·薛明治阿嬤》)“羅方快說,那時,家中天井、廳堂都被匪炮擊中,她嚇得躲進簡陋的土洞避炮火;長子羅清派剛好在田里耕種,顧不得井深,撲通便跳進井中;三子正要出海捕魚,也趕緊躲入船底逃過一劫。”(《戰地阿嬤·羅方快》)張淑賢則用 “一袋袋棄置的海蚵殼,在家里堆成避難的沙包,中共炮火一來,便領著兒女就地躲避,藏身在海蚵殼沙包下面。”(《戰地阿嬤·張淑賢》)林金樹 “告訴壯丁,炮彈來時怎么疏散、避難,派一個人站立山頭,一看到大陸那邊閃光,馬上吹哨子,然后趕緊臥倒。”(《風雨江山·林金樹》)
然而無情的炮火給金門百姓帶來巨大的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八二三炮戰,金門全境籠罩炮火,而東半島以田墩、西園與洋山等地中彈最多,洋山幾乎夷為平地。”(《風雨江山·黃蘇源》)八二三炮戰“古崗中彈甚多,鄉村幾乎夷為平地。”(《風雨江山·董清池》)“那時洋山駐軍都駐土洞,一中彈整個崩塌,悶死、打死很多,而牲口中彈死的也不少,他每常趁著晚上摸黑去扛死豬肉、死牛肉回來吃。他說,有一次還扛回來一條人的大腿。”(《金色年代·蔡允澄》)在單打雙不打的年代,林泡 “二姐正坐在房間里理家務,不幸被突來的宣傳炮打死。 ”(《戰地阿嬤·林泡》)
炮火紛飛的年代,壯丁們不僅要躲炮火,參加生產勞動養活一家人,更要參加搶灘、出操以及名目繁多的援軍任務,如出水鴨子 (搬運軍需物資等)。這個時期實行的是戰地政務,戰地單行法規規定祖籍金門男子不必服兵役,但16歲至55歲經體檢合格者必須編入民防隊,接受組訓并執行支援作戰的任務。在長達數十年的戰地政務體制下,金門男子過的是 “不必當兵,卻是當了半輩子兵”,“執行半輩子軍中任務,卻沒有享受過軍人優費”的日子。“陳榮田說他十六歲當葫蘆隊,下雨道路沖毀了他要去填平,父兄出操,他中午要用籃子挑糜粥去給他們,他說法令一改再改,他直到五十七歲才退役,比當兵還辛苦。”(見 《金色年代·陳榮田》)
這個時期金門駐國民黨軍隊最多時候達到十萬人,“都是大陸剛撤退過來的精壯漢子,荷爾蒙當盛,閑暇之時每天游蕩串門子。” (見 《風雨江山·陳智景》)金門男子白天忙農活、出操,晚上忙放哨、搶灘,在家陪妻子的時間少,如果軍人因走動頻繁與家中妻子有曖昧關系,很容易產生家變。
這種情況更容易在出洋客家中發生。李福井 《風雨江山·黃蘇源》中說:“這些出洋客多沒受過甚么教育,很多是青暝牛——文盲,連批信都很少寄回家,更談不上撫慰獨守空閨的妻子。”而這些出洋客的老婆,“空虛的心靈,生活的折磨,又有生理上自然的問題,在軍隊穿梭環繞的態勢下,加速催動了家變,很多婦人投到軍人的懷抱。”文中引黃蘇源的話說:“炮戰過后,女人嫁阿兵哥,行情大起……很多適婚金門男人娶不到老婆,演變成后來的 ‘三八制’——八千元、八石肉、八兩金子。”鄉下的農民 “為了娶老婆,大家只有咬緊牙關苦撐,打腫臉充胖子,遂在金子上動手腳。”因為 “嫁給阿兵哥 ‘煮火雞 (閩南語鍋的意思,即煤油爐)、配菜花’,比較快活,誰還要跟你歹命拖磨 (辛苦工作)”,于是 “有樣學樣,互相影響……連當阿嬤的也嫁。”娘家 “嫁女兒雖然海削了一頓,遂把苦難留給女兒、帶給婆家,那時女子二十歲就嫁人……拼死拼活,一切都為了早日還清債務。”“如果又笨手笨腳不得婆婆的歡心”,“日積月累就會產生婆媳問題”,丈夫 “通常站在媽媽這一邊,把壓力加給媳婦。因此,有苦無處訴——只有怨父親拿那么多聘禮,讓她那么辛苦,因此吃農藥尋短的所在多有,造成社會的悲劇。”
以上是國民黨軍隊大量進駐金門時給金門百姓生活帶來的負面影響。
十萬大軍的進駐也帶來巨大的市場、驚人的購買力,它刺激了金門服務業的發展,給基本上處于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狀態下的金門社會帶來蓬勃的生機和活力,百姓生活從此要起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沙美:“炮戰過后生意鼎盛,沙美街上都可看見人潮,冰果室、餐飲店、撞球場、五金店、化妝品店及雜貨店,甚么行業都有,多做阿兵哥的生意……尤其早市……清晨四時就解除宵禁,準許鄉下的農民來賣菜,沙美的菜都是農民自產自銷,菜價便宜,所以阿兵哥的采買車很多,都來買菜。”(見 《金色年代·施聯升》)
在陽翟:“陽翟駐了一個重裝師,有電影院、郵局、洗澡堂、撞球場、冰果室、餐廳與雜貨店、中藥鋪……這時的陽翟,是歷史上最風光的時代,整條街上都是兵,各行各業生意都很好做,常常看見阿兵哥在街上穿梭、吃飯、看電影、打彈子以及購物。”(見 《金色年代·鄭彩秀》)
在頂堡:作為金西師師部所在地 “的頂堡真是繁華,電影院的兩旁不久就蓋了商店,阿兵哥常來受訓或者看電影,如江山美人與梁祝,一時轟動,觀眾不絕于途,盛況更是空前了。”(《金色年代·蔡瑞炎》)
甚至連書報也非常好賣。金門著名作家陳長慶先生當時開了間書店,“他說那時生意很好做,一個月可以做一百多萬元,賣書至少賺兩成半,每月少說凈入二十五萬元,所以不到十年,他在山外復興路買一間瓦厝,光買地皮二百七十萬元,翻修搭建三樓,又花了快兩百萬,后來再花四百多萬元,把親戚租給他的店面買下,加蓋整修又花了一百多萬。”(《金色年代·陳長慶》)
以上是從1958年八二三炮戰前后數年到1992年解除戒嚴開放觀光的前后30多年間,國民黨軍隊帶動金門民間經濟發展乃至大繁榮的概況。
四、解嚴觀光時期
1992年金門結束戰地政務,開始開放旅游觀光的年代,國民黨軍隊駐軍逐年減少,原本依賴軍人消費的民間經濟來了個大轉彎。
在小徑:“一九九四年小徑首先撤軍,生意開始減退,二〇〇一年師部撤走了……小徑只剩下后山的戰車部隊,但是又不準他們下山,小徑變成一個兵都沒有了。二〇〇三年完全沒有生意,小徑的店幾乎全部關掉。”(《金色年代·李金鐘》)
在料羅:“駐軍大幅度的裁減,生意就一落千丈,不可同日而語了;現在店鋪十間關了九點九間,呈現盛極而衰的荒蕪、蒼涼與落寞。”(《金色年代·吳炯煒》)
在沙美:“街道見不到幾個人影,沒有生意,與以前繁盛的景況不可同日而語了。 ”(《金色年代·呂寶玉》)
雖然開放觀光也給金門經濟帶來機遇,但與十萬國民黨駐軍比較,是遠遠無法比擬的。陳允南數十年來一直在成功村開餐館,這里生意鼎盛時有九家餐館,如今只剩他一家。他說,“開放觀光之后,有人做觀光客的生意,十人一桌兩千元,他想別人在賣,我們也賣吧!后來有人要求一桌貼兩瓶汽水,他也比照;不久之后又說有人再貼一瓶高粱酒,高粱酒一瓶三百多元,沒辦法做,就不接觀光團。”他現在的主要顧客是本地的公教人員。(《金色年代·陳允南》)
未來金門經濟如何發展,金門不少有識之士正在思考。
楊樹清的 《東渡之歌》里可以清楚看到:八二三炮戰期間,臺灣當局鼓勵金門民眾遷往臺灣,每人補助3000元,很多金門人舉家遷臺,之后60、70乃至80年代還有很多金門人陸續前往臺灣發展,他們腳踏實地,奮力拼搏,出了將軍、科技界、政界精英、學界泰斗、藝術家,即使普通百姓也誠實做人,不忘金門人傳統質樸本性。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割舍不斷家鄉情結,時時不忘以各種形式回饋鄉里。同時有一些金門人或金門籍華人早期出洋到新加坡謀生,經過艱苦拼搏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他們同樣有一個帶有深深烙印的“唐山”情結:時時不忘自己是金門人,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回饋家鄉。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金門人出洋打拼的縮影。《獅城人語》里著名作家寒川有詳細描述。
五、結語
以上是筆者閱讀 《金門百年庶民列傳》所看到的百年金門庶民生活的軌跡。本套叢書的記錄,時間跨度長,覆蓋面廣,作者陣容強大,凝聚了作者們很多的心血,是一套不可多得的好書。金門縣文化局能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際出版這樣的一套叢書,是明智之舉。此外,作為一套回顧金門百年歷史的叢書,有些重要歷史事件或者典型事件,還可以再記錄其中。如1942年的西園慘案,它是日據期間的大事件,是金門人心頭永遠無法撫平的創傷;還有這期間復土救鄉團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屢屢打擊日偽并且多有斬獲,它是金門人的希望、金門人的驕傲。這類人和事,應該占有一定的筆墨。百年來金門人旅居世界各地,除新加坡外,其他地方也該有所書寫記錄。誠然,這和組織撰寫的時間倉促有關,相信讀者能夠理解。
總的說來,百年以來金門人的生活有痛苦,有歡樂,有徘徊,有希望。如果用“忠誠”、“堅韌”來形容金門人的總體性格,那么其中還多了幾分 “無奈”。回顧歷史,是為了總結經驗,展望未來。未來金門人如何駕駛汪洋中的這一條船,我們有理由對其充滿信心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