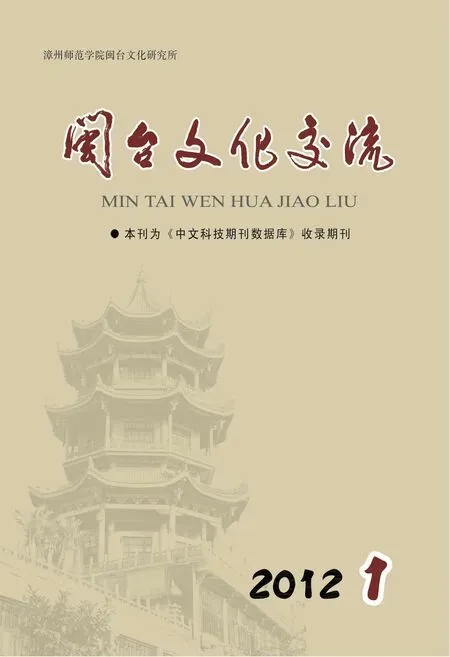藍鼎元社會性別意識及其現實價值
黃耀明
藍鼎元 (1680~1733) 字玉霖, 別字任庵,號鹿洲,福建漳浦縣長卿里人,出身拔貢,先后出任族兄藍廷珍平臺幕友、潮州知縣和廣州知府等職。藍鼎元一生恤民報國,志在經世實學,被譽為 “經濟之儒、文章之匠”和 “籌臺之宗匠”,是清初道南學派閩學的代表人物,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間一位較具影響力的政治家和學風純正的思想家。近幾年來,有關藍鼎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藍鼎元的哲學、教育、學術、治臺、農業、海洋、對外貿易、鄉治思想等方面和領域 (黃新憲,2004;許其端,1994;劉青泉,1996;林其泉,2000;鐘祥財,2000;陳躍,2006;王亞民,2011),但對于藍鼎元的社會性別意識尚未有學者關注。藍鼎元的社會性別意識在其 《女學》一書中有充分體現,而且藍氏還將其社會性別意識付諸行動,在其平臺治理實踐和潮州鄉治實施的社會政策中都可以窺視一斑。不可否認,藍氏的社會性別意識對于當時滿清社會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主流婦女觀壓制無疑是一種重生,對清末乃至近代女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蒙作用。但是,藍氏的社會性別意識依然局限在針對女性規訓的傳統男權意識主導下。研究藍氏的社會性別意識對于當今的社會性別與公共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一、重生:藍鼎元社會性別意識的主要理念
自從安·奧克利 (Ann Oakley) 的 《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 (Sex and Gender)一書于1971年問世以來,這個意義上的 “社會性別”概念已經在社會學和人類學得到廣泛使用。[1]蓋爾·魯賓 (Gayle Rubin) 在此基礎上,于1975年發表的 《走向婦女人類學》一書在對西方三大學術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和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反思批判與借鑒的基礎上,提出了 “社會性別制度”的概念,并指出這一制度是與經濟政治制度密切相關、有自身運作機制的一種人類社會制度,這套制度使女性從屬于男性。[2]也就是說,生理性別是人類生理上的事實,而社會性別不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作為男性或女性的經歷會因為文化的差異而帶有極大的變動性。社會性別概念一般被社會學家用來描述在一個特定社會中,由社會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體特征、角色、活動及責任。因為社會的組織方式,一定歷史時期政治文化維度的社會性別身份決定了社會如何看待作為男人和女人以及期待男人和女人如何去思考和行動。如此看來,社會性別關系就成了合作、聯系與相互支持的關系,也是沖突、分離與競爭的關系,更是差異與不平等的關系。社會性別關系特別關注兩性之間的權力分配,因為其制造并再生產了男人與女人在某一特定社會環境中地位上的系統差異,并且還規定了彼此的責任和權利分配方式以及賦予其價值的方式。社會性別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時間和空間維度,在不同的群體間也有所不同,并且因階級、種族、民族、殘障等元素而變異。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定時期的政治、文化制度決定了其社會性別制度,而社會性別制度就是導致社會性別差異的重要根源。中國的社會性別意識具有深刻傳統文化的印痕,儒家文化關乎 “禮義仁智信”的制度等級框架及男權中心的思維決定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性別分工及性別期待。“三從四德”和 “女子無才便是德”被奉為衡量女性行為規范及道德標準的重要坐標,“男尊女卑”和 “夫為妻綱”使得女人長期以來被置于男人的奴役和壓迫之下。告別原始時代之后,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就一直是一個男權主導的社會,或者說是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為了維護這樣一個社會秩序和統治模型,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倫理就建構一套讓男人覺得 “合理”和讓女人覺得 “應該”的男性壓迫女性規則。這套倫理規則大概是先從男女關系中抽象出兩個哲學范疇:陰與陽,由陰與陽再推導出陽的剛與動,陰的柔與靜。然后將陰陽這兩個哲學范疇進一步無限泛化,實際關聯到自然界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去,如天與地、日與月,這樣的關聯使得原本非常晦澀的哲學意涵變得很容易讓人們接受。更重要的是這種哲學設計最終轉化為約束人們行為規范和道德標準的倫理守則。就由 “天尊地卑”到 “男尊女卑”和 “男主外,女主內”。
藍鼎元出身于閩南農村的貧寒家庭,從小就浸染了閩南農村社會生活中文化風俗諸多習性。作為清代著名的政治家,難能可貴的是藍鼎元有很深的底層普通民眾社會生活意識。其社會性別意識對于父系氏族時期以來傳統中國禁錮女性的慣性思維無疑是一種重生。
(一)將 “閨門風化”提升到 “天下之治”的高度,意識到女性修養對于社會道德規范的影響力。藍鼎元主張,“天下之治在風俗,風俗之正在齊家,齊家之道當自婦人始。”[3]傳統中國文化的儒學思想非常重視閨門風化,漢儒就立下三從四德的倫理綱常作為標桿來約束女性的行為。這種約束經歷了歷史及社會變遷的洗禮已然成為了男權進行女性社會控制的合理性解釋,社會性別所規定的性別分工自然成為了社會倫理道德存在與施行的合法性依據。藍鼎元認為,女性的行為空間即使局限在閨門之中,但其影響力卻直抵天下治理,不容小視。早在 《女學》一書問世之后,即受到先王父的極度表揚:“五百年無此矣!不意吾孫能如是,此有關風教,為世道人心不可少之書,確乎可傳也。”[4]藍鼎元也確實重視婦女在整個家庭教育尤其是家庭倫理中的地位與作用,藍鼎元對于女性行為舉止影響力重視的論述無疑給當時清代的禁錮之風注入一針強心劑,開啟了人們重新審視女性風化與天下治理關系的先河。
(二)重視女性參與接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藍鼎元無論是在臺灣擔任幕友時期,還是歷任廣東普寧和潮陽知縣期間都十分重視地方教育,提出了許多富有真知灼見的教育觀,并興辦了一些鄉學和書院。[5]值得一提的是藍鼎元的教育覆蓋到女性,他強調女子的道德修行影響到子女教育和家庭倫理規范,而女子良好美德養成的唯一路徑就是教育。他堅稱:“婦女終老深閨,女紅之外,別無事業,然耳目見聞,不能及遠,則讀書明理,其大要矣。”[6]他十分強調教育對于中國古代杰出女性班昭、宣文君宋氏等人成長的影響,認為只有婦女接受了文化教育才能明白事理,婦女明白了事理才能檢討自己的修行與德行,婦女擁有良好的德行才能教育好優質的子女和確定合乎常理的家庭倫理,也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天下的大治。
(三)提出婦女對于家庭結構穩定和社會穩定的不可替代性。幾乎傳統中國的社會性別制度是將女性的性別角色定位在婦職、妻職和母職三大類的,而這三大類性別角色都被局限在家庭的小范疇之內,即“女正位于內”。問題是即使將婦女的整個人生歷程的各個階段都定位在家庭之中,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永遠被邊緣化和沒有話語權的。不管是婦職、妻職還是母職,她們的精神及法理主宰永遠是父親、丈夫和兒子,即所謂男權。在這種時代的主流觀念中,藍鼎元竟然發現了女性對于家庭結構穩定及社會穩定的不可替代性。在對待男女之欲這個中國傳統文化諱之莫深的領域,藍鼎元意識到滿足男女雙方性別和諧對于家庭結構穩定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如當時移民臺灣的大陸墾民幾乎都是單身男子,年輕的單身男子在臺灣根本沒法組建家庭,就是在大陸已有家眷的單身男子也會因為對家庭妻女的思念而無法安心扎根臺灣,這種狀況極大地影響了墾民家庭結構的穩定和臺灣移民社會的發展。藍鼎元主張應允許這些墾民返回大陸攜家眷前往,且今后組織墾民一定要攜家眷同去。[7]這種做法不僅確保了移臺墾民家庭機構的穩定性,而且促進了臺灣移民社會結構的和諧與發展。更重要的是藍鼎元的這個社會性別意識及舉措,使得那些在大陸仰望臺灣的婦女們能夠到臺灣與日夜思念的丈夫團聚并組建家庭,幾乎就是涅槃重生。
(四)對清末乃至近代時期的女學興起起到重要的啟蒙作用。大家知道,《女學》一書是藍鼎元出仕之前的一部著作,全書共分六卷,首三卷為 《婦德篇》,卷四為《婦言篇》,卷五為 《婦容篇》,卷六為 《婦功篇》。在這部書中,藍鼎元盡管針對婦女的道德教化做了大量闡述,但其中蘊含的女學思想及社會性別意識對清末乃至近代時期的女學興起是相當重要的。甚至可以斷言近代女學以賢妻良母式為核心的教育思想就發端于藍鼎元的女學思想。藍鼎元認為女性必須接受文化教育的思維意識萌芽最終到清末演變成1898年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學堂——中國女學堂。 《女學堂書塾開館章程》里明確提出: “其教育宗旨,以彝倫為本,所以啟其智慧,養其德性,健其身體,以造就其為賢母為賢婦之始基。”[8]這樣的辦學理念幾乎就是藍鼎元《女學》關于婦女必須接受文化教育和接受怎樣的文化教育內容闡述的發揮與延續。
藍鼎元對于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男婚女嫁 “婚娶論財”和部分婦女篤信鬼佛等惡習一樣提出尖銳批評。[9]藍鼎元指出:“世教下衰,婚娶論財。女子將嫁,或于母親需索無厭,必求資裝豐備,寡廉鮮恥,恬不知羞。 ”[10]藍鼎元還認為:“從來婦女, 多信鬼神,故巫覡尼僧,得肆簧口,為誑財物之階,原其心,不過欲求福耳。”[11]藍鼎元的社會性別意識無疑可以喚起人們對于遠古時代女性曾經主宰家庭與社會風光無限的歷史記憶,這樣的歷史記憶伴隨著幾千年的風化與變遷已然逐步被男權主導家庭與社會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所逐步淡化。從表面上看,淡化的直接原因就是文化在女性社會性別的建構中起了主要作用,實質上是通過文化被逐步建構的社會性別制度在女性社會性別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恰恰社會性別制度又構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藍鼎元的社會性別意識盡管在當時清代的主流文化體系中只是一粒遙遠星星式的微光,但它永遠不會被消失,一旦時機成熟就必然有其重生的一天。
二、規訓:藍鼎元社會性別意識的歷史局限
對于藍鼎元的研究,學者們的觀點主要還是正面評價的居多。對于他的一些不足,則歸因于當時歷史的局限性。藍鼎元的社會性別意識也不例外,盡管這方面的貢獻與突破具有重要的歷史及現實意義,但藍鼎元同樣難于擺脫自己所生活年代的社會及文化限制。這正好印證了藍鼎元歷史人物品格中歷史時代與人物個性的有機結合。藍鼎元的社會性別意識同樣停留在儒家文化體系里針對女性的規訓之中,將“閨門風化”提升到 “天下之治”高度的實質一樣將女性的性別角色與性別關系限制在從屬的和邊緣的地位之下;重視女性參與接受文化教育的核心內容是女性修養與德行的教育,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男權社會;積極推行女性家眷移臺的結果是復制又一批男權主導的家庭;《女學》中處處充滿了針對女性道德的教化與男權獨尊的傳統思維。
規訓之一:男權始終是藍鼎元社會性別意識的核心與出發點。有學者指出:“在艱辛而短暫的社會治理實踐中,藍鼎元不僅具有了一種雙重性品格,而且理想與現實、保守與先進的矛盾又構成了其矛盾性品格的兩個方面,這既是藍鼎元歷史品格的特殊表現,又是地域與時代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12]在藍鼎元社會性別意識里,男權始終就是其整個思維體系的核心與出發點。首先,藍鼎元依然堅守女子從一而終的男權主導觀念。認為:“婦道從一而終,豈以存亡改節?夫死不嫁,固其常也。不幸而遭強暴之變,惟有死耳。玉潔冰清,可殺不可辱,千載而下,有余榮焉。”[13]其次,藍鼎元認為男女之間有一定的界限和隔離是非常必要的,否則就像禽獸一樣出現亂倫。提出:“男女不雜坐,不同揓枷,不同中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男女之防,人獸之關,最宜謹慎,不可紊也。”[14]還有,藍鼎元還鼓吹男子擁有一妻多妾的合理性,同時要求女性必須依靠自律來做到不嫉不妒。強調:“君子為宗廟之主,奉神靈之統,宜蕃衍似續傳序無窮,故夫婦之道,世祀為大。……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為妻之道,使其眾妾皆得歡欣于其夫,謂之不嫉。”[15]男權主導婦女從屬的社會性別意識始終無法使藍鼎元跳出傳統的倫理思維。
規訓之二: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核心依然是修養與德行。藍鼎元主張女性必須接受文化教育,并且認為女性是否接受文化教育事關重大。但問題是藍鼎元在這里非常強調女性接受教育的內容必須是有選擇性的,要以女性道德的教化為核心,學習的基本內容及教育目標是要使女性明理和養德,不要去學習那些詩詞等浮華的東西。所謂:“女子讀書,但欲其明道理、養德性。詩詞浮華,多為吟詠無益也。必有功名教之書,乃許論著,不然,則寧習女紅而已矣。”[[16]藍鼎元的女性教育實際上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和狹隘性,目的性就是要提升女性的道德修養以達到國家與天下的大治,狹隘性就是其將女性學習的內容進行了明確的限制和規定。
規訓之三:“孝”是女性參與家庭倫理建構與社會實踐的主要命題。考察社會性別關系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性別角色與分工。不同歷史時期與文化對于性別角色與分工的規范與期待是不同的。在藍鼎元生活的社會里, “孝”是作為一個至高無上的生命終極命題只可遵循不可違背的,其甚至成為評判一個人是否 “善”與 “惡”的主要標準,并且從家庭倫理中的 “孝”推及到整個國家與民族的大 “孝”。藍鼎元認為女性參與家庭生活和社會實踐,其主要的行動踐行就是 “孝”,這是女性最重要的美德,也是維系家庭和諧與發展的基礎。女性應該遵從孝道,并與其他家庭成員保持和睦相處,尤其注重處理好與叔叔和姑姑的關系,同時女性還要勤儉節約,以身作則,認真負起培育下一代的重任。所謂:“人之少時,與母最親,舉動善惡,父或不能知,母則無不知之。故母教尤切,不可專事慈愛,釀成桀驁,以幾于敗也。”[17]
藍鼎元的一生亦學亦官,他學識淵博,有著常人難及的見識與膽略。從政期間,藍鼎元精心治理下的潮汕社會出現了難得一見的太平盛世景象,由此可見其政績之卓著。對此當時的皇帝與天下百姓都給與了極高的贊譽:“一時名噪輦下,卿貳慕之者,多躬先造訪。或內臣出膺封疆,輒詣府君,為條陳地方情形利病。天下士游京師者,皆爭一見為快。”[18]藍鼎元從閩南農村普通社會階層的孩子成長為驚動皇帝與天下的大師級人物并非偶然。其中有清初道南學派經世致用思想的內在驅動,也有藍鼎元個人生長于民間社會形成的草根情結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其面對現實視角的倫理思想對程朱理學 “空談心性”形成了重要挑戰。
三、藍鼎元社會性別意識的現實價值
藍鼎元的社會性別意識盡管充滿了男權主導話語下的婦女規訓,但其倡導的重視婦女教育、家庭結構和諧、女性必須注重修行與德行教化、婚嫁不能論財等社會性別意識無疑是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就是穿越時空放在當下的社會,藍氏的社會性別意識對于當今的社會性別與公共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一)為城市農民工提供一個穩定的家庭結構。中國近幾年的城市化進程與現代化建設帶來了農村人口的大規模遷移,這種遷移的結果直接導致了很多農村家庭的分離與破裂。如農村社會出現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妻子、留守丈夫等現象,城市出現的打工子弟無法上學現象等。盡管城市建設與發展離不開農村勞動力的支持,但城市卻未能提供給農民工們合適的身份與家庭。這與藍鼎元治臺時期的大陸移民何其相似?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藍鼎元社會性別意識,制定相應的社會政策,讓農民工們攜其家眷在城市也有一個穩定和溫暖的家庭。
(二)大力倡導女性的社會參與與性別平等。自從藍鼎元 《女學》發起的倡導女性接受文化教育到近代女學真正興起以來,中國女性在新中國成立后迎來了真正的重生與復興。女性極大程度地參與到家庭事務、社會建設與管理甚至國家政治事務中來。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由于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我國目前的女性社會參與與性別平等仍然存在很多問題。性別歧視、生育歧視在很多地方長期存在,女性在就業、參政、創業等領域長期遭受不平等待遇等。我們應學習藍鼎元站在時代制高點的文化自覺態勢,切實將女性的社會參與與性別平等落到實處,真正讓廣大女性感受到女性偉大背后的時代之偉大。
(三)在 “愛情”與 “物質”的博弈中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戀愛婚姻觀。近階段在戀愛與婚姻話語中最吸引大家眼球和注意力的就是關于最高法院關于夫妻離婚之后房產的分割歸屬問題。這個問題的核心直接考量著人們在 “愛情”與 “物質”博弈中的價值判斷與態度。日本法律規定,夫妻雙方離婚,妻子可以獲得至少70%以上的資產。這樣的規定無疑極大地保護了婦女的基本權益,也提高了男性的離婚成本。遠在清代時期的藍鼎元就非常痛恨“婚嫁論財”,今天的中國依然在討論 “婚嫁論房”,難道我們在對待女性的性別意識中比古人還不如嗎?
(四)繼續弘揚 “孝”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積極作用。中國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已經占全國總人口的13.26% (第六次人口普查統計數據),一個人口急劇老齡化和 “未富先老”的中國社會馬上甚至已經來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必將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與政治的穩定與發展。盡管家庭結構的變遷必須強調政府承擔更多養老的社會責任,但不可否認傳統家庭養老與“孝”文化仍將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因此,必須加強挖掘和發揮藍鼎元關于 “孝”文化的作用與功能,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來共同解決老齡化問題帶來的壓力與挑戰。
(五)注重女性修行德性對于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女性究竟該擁有怎樣的修行與德性才能稱得上合適的為人女、為人妻和為人母,不同的時代文化應該有不同的判斷。藍鼎元非常重視女性的道德教化,因為其影響著子女養成、家庭倫理及社會的穩定與規范。當代女性應該學習藍鼎元提出關于女性修行德性的一些積極理念,如 “孝道”、“勤儉”、“寬容”、“學習”、“和睦”等,這些中華民族女性傳統的優良特質現在在一些女性身上已蕩然無存。我們應該提煉藍鼎元的這些積極思想,內化我們的靈魂,讓藍鼎元的社會性別意識在當今社會依然能夠展現特有的現實價值。
注釋:
[1]坎迪達·馬奇等著:《社會性別分析框架指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8頁。
[2]張李璽:《婦女社會工作》,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1頁。
[3](清)藍鼎元:《女學·女學自序》。
[4](清)藍鼎元:《先王父逸先生暨王母陳孺人行狀》,《鹿洲初集》卷20,蔣炳釗、王鈿點校:《鹿州全集》上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55頁。
[5]黃新憲:《藍鼎元的教育觀探略》,《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第39頁。
[6]蔣炳釗、王鈿點校,(清)藍鼎元:《鹿州全集·婦功篇》,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98頁。
[7]許其端:《藍鼎元的哲學思想》,《漳州師院學報》,1994年第3期,第18頁。
[8]談社英:《中國婦女運動通史》,北京:婦女共鳴社,1936年,第85頁。
[9]陳支平、林楓:《略論藍鼎元的婦女觀》,《藍鼎元研究》,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87頁。
[10](清)藍鼎元:《婦德篇上》,第九章,《女學》卷 1。
[11](清)藍鼎元:《婦德篇下》,第一一 O 章,《女學》卷 3。
[12]王亞民:《知縣藍鼎元歷史品格的解讀》,《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第104頁。
[13][14](清)藍鼎元:《婦德篇下》,第七十一章,《女學》卷3。
[15](清)藍鼎元:《婦德篇》,第三五章、三六章、三七章,《女學》卷 3。
[16](清)藍鼎元:《婦功篇》,第五十一章,《女學》卷 6。
[17](清)藍鼎元:《婦功篇》,第四十二章,《女學》卷 6。
[18](清)朱軾:《行述》,藍鼎元:《鹿洲全集》,蔣炳釗、王鈿點校:《鹿洲全集》上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