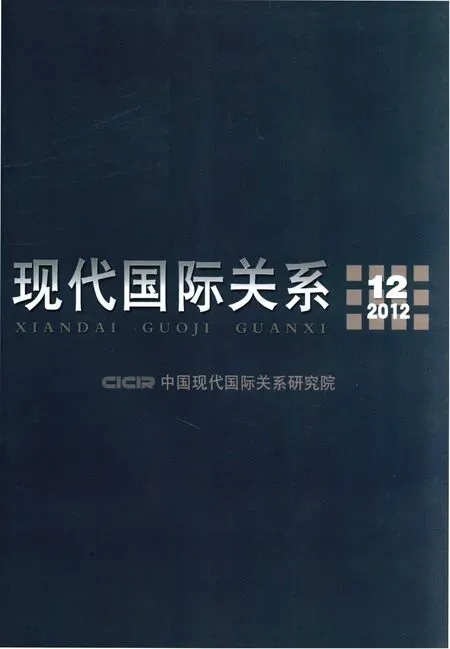歐盟力量格局變化與歐洲一體化前景
張 健
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三年來,歐盟成員國實力對比、歐洲南北方國家關系以及歐元區與非歐元區國家關系等均發生重要變化。歐盟這一力量格局變化將對成員國之間關系以及歐盟運作模式產生何種影響,未來歐洲一體化又將以何種方式演進等都是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
一
主權債務危機不僅深刻影響了歐盟經濟發展和政治生態,也導致歐盟內部格局出現了重大變化,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變化是德國“再次崛起”,成為歐盟實力最強、影響力最大的國家。德國地位的提升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德國成為歐盟內最大的債權國,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著部分成員國的“生殺大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等國先后接受了歐盟救助,其中德國提供的救助資金最多。在歐盟設立的各種救助工具中,無論是臨時性的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還是永久性的歐洲穩定機制(ESM),德國都是最大的資金貢獻國,出資占總額的比重達27%。①Andrew Walker,“Q&A: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October 8,2012,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9870747.(上網時間:2012年11月30日)德國也因此獲得了更大的發言權。例如,如果沒有德國首肯和參與,希臘等債務國就得不到援助款項,歐盟救助機制也將無法籌集到資金。
其二,德國模式的示范效應增大。作為歐盟內的經濟“老大”,德國經受住了債務危機的考驗:三年來經濟逆勢增長,2010年甚至再現“德國奇跡”,GDP增長率高達3.6%,②“German economy grew by 3.6% in 2010”,January 12,2011,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2170223.(上網時間:2012年11月30日)2011年繼續保持了3%的較快增長。③“German Budget Deficit Plunges to 1 Percent of GDP”,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business/obeying-eu-rules-german-budget-deficit-plunges-to-1-percent-of-gdp-a-817363.html.(上網時間:2012年11月30日)德國的出口也一再攀升,2011年外貿順差1500億歐元,而同期法國外貿逆差達700多億歐元。④Hugh Carnegy,“France:Reluctant to reform”,The 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2012.德國人一向重視財政紀律和經濟競爭力,這種管理模式使德國經濟獲益不淺,并在危機中有了良好表現。德國因此成為其他歐盟國家自覺或不自覺的效仿對象。如果說南歐一些重債國家是被迫效仿,采取緊縮政策,那么波蘭、捷克等中東歐國家則屬于主動學習,它們正在向德國模式靠攏。
其三,在歐盟應對債務危機的過程中,德國發揮了決策者和領導者的作用。觀察近三年歐盟處理債務危機的進程可以發現,歐債危機管理基本上是“一個套路走到底”:只要德國反對的措施,歐盟和歐元區就無法推行;相反,只要德國堅持的措施,最后都不同程度地得以實施。比如,歐盟委員會以及法國和南歐國家曾主張發行歐元區統一債券,但因德國反對而不了了之;而德國極力主張的財政緊縮和結構改革,盡管在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國都極不得人心,最終卻得到了持續推進。再比如,德國力主歐盟用更嚴厲的法律條文規范成員國的預算政策,并提出要修改歐盟條約,盡管曾遭到多數成員國的消極抵抗,但最終使之進入歐盟議事日程。在2011年12月8-9日的歐盟峰會上,除英國外的26個成員國同意起草一部新的條約,其核心內容是:各成員國必須將“黃金法則”納入本國憲法或使其成為具有同等地位的法律,明確規定結構性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0.5%,政府必須確保預算平衡;財政赤字超過GDP 3%的成員國將自動受到處罰。①Peter Spiegel,Quentin Peel,Alex Barker and Stanley Pignal,“Britain’s cold shoulder for Europe”,Financial Times,December 9,2011.2012年3月,歐盟25個成員國簽署了《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穩定、協調和治理公約》,即“財政契約”。目前,該條約在成員國內的批準進展較為順利,愛爾蘭已通過了全民公投,法國也在德國的壓力下批準了這一條約。總之,歐盟和歐元區近年來通過的一系列加強財政管理的措施,包括“歐洲學期”(European Semester)、“歐元附加條約”(Euro Plus Pact)、“六項規則”(The Six Pact Measures)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應德國要求而設立的。此外,歐洲中央銀行地位的提升也反映了德國的意愿。歐洲央行是按照德國央行模式建立的。債務危機期間,歐洲央行的舉措往往有立竿見影的作用,包括實施“長期再融資計劃”以及“直接貨幣計劃”等。
德國地位的上升帶來了歐盟格局的第二個重大變化,即歐盟力量重心近年來加快向北方國家傾斜,南方國家的地位和影響力大幅下降。歐盟內部南北地區差異和矛盾長期存在。法國處于歐洲南北分界線上,與意大利、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等地中海沿岸的南歐國家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并與以德國為首的北方國家荷蘭、芬蘭、瑞典等在政策取向和立場上形成了對峙和競爭。一直以來,盡管南北歐洲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差異較大,但雙方在歐盟內的力量對比大體相當,歐盟在內外政策上也基本照顧到了雙方的立場。比如,歐盟應法國要求建立了地中海聯盟,應瑞典和波蘭要求強化了與烏克蘭等東部鄰國的關系。然而,這種南北力量平衡格局隨著主權債務危機的持續惡化被打破,并出現了不利于南方國家的變化。從以下幾組對比中可以看出南北方經濟在危機中的不同處境。希臘自2008年以來經濟連年衰退,GDP萎縮了18%,②David Jolly,“Greek Economy Shrank 6.2%in Second Quarter”,http://www.nytimes.com/2012/08/14/business/global/greekeconomy-shrank-dramatically-in-2nd-quarter.html?_r=0.(上網時間:2012年12月5日)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經濟目前也陷入衰退,法國勉強維持了增長;而北方國家經濟形勢則好得多,德國、芬蘭、瑞典、奧地利等國在危機期間仍保持了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財政上,2011年意大利、葡萄牙、希臘等國的國債占GDP比重分別上升至120.1%、107.8%、165.3%,法國國債占比也超過90%;2011年希臘財政赤字達9.1%,西班牙8.5%,法國5.2%;而北方國家債務和財政赤字相對較低,處于可控狀態。③“Provision of deficit and debt data for 2011”,April 23,2012,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cache/ITY_PUBLIC/2-23042012-AP/EN/2-23042012-AP-EN.PDF.(上網時間:2012年12月5日)南歐國家以及法國近年來被國際三大評級機構連續下調信用評級,而德國、荷蘭、芬蘭等北方國家至今仍享有最高的AAA評級。在遭受危機重創之下,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等國不得不接受德國等北方國家的救助。在這種情況下,南歐國家在歐元區中的經濟話語權盡失,被迫按照北方國家的要求實施財政緊縮政策和結構改革,甚至被迫接受北方國家的監督,其經濟主權受到較大侵蝕,淪為歐元區和歐盟內的二等國家。法國雖然沒有陷入南歐國家那樣的被動,但經濟上面臨的風險在增大,④“Concern Spreads over Slow Pace of French Reform”,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french-credit-rating-downgraded-amid-doubts-over-reform-path-a-868203.html(上網時間:2012年12月5日);Hugh Carnegy,“Paris sends conflicting signals on reform”,Financial Times,November 26,2012.處于自顧不暇狀況。
歐盟內部格局的再一個變化反映在歐元區國家與非歐元區國家的關系上,權力重心正在向歐元區傾斜。目前,歐元區涵蓋了德、法等17個國家,非歐元區國家則包括英國、瑞典、丹麥等富裕的北歐國家以及部分中東歐國家。自債務危機爆發以來,非歐元區國家的分化呈加速之勢。一方面,危機期間,歐元區的問題基本上主導了歐盟事務,歐盟議事日程及歐盟委員會等超國家機構將工作重心和資源投入到了歐元區的危機應對方面。另一方面,隨著歐元區一體化進程加快,非歐元區國家被排斥、被邊緣化的焦慮感增加。因為歐元區作為一個整體,其決策很可能影響歐盟單一大市場以及諸多歐盟內外政策,留在歐元區之外即意味著決策權的喪失及影響力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非歐元區國家選擇了和歐元區一起行動,最典型的例子是非歐元區國家除英國、捷克之外都簽署了“財政契約”,并積極參與了歐元區建立銀行業單一監管機制的談判。英國選擇了與歐元區“劃清界限”的另一條道路。英國是一個重要的歐洲國家,但從來都不是歐洲一體化的積極支持者,也不像德、法等大陸國家那樣視歐盟為一項政治運動,而更多將歐盟看作一個單一大市場。自歐債危機以來,英國的“疑歐”情緒明顯抬頭,媒體及主要執政黨保守黨普遍看衰歐元區,英國與大陸國家多年潛滋暗長的矛盾開始凸顯。對于歐元區出臺的系列救助措施,英國明確表示,這是歐元區自己的事情,英國決不會參與其中。
二
歐盟力量格局的變化和調整實際上是成員國之間關系以及歐盟超國家機構與成員國之間關系的重塑,將不可避免地給歐洲一體化發展帶來重要影響。
首先,德法嫌隙將進一步增大,雙方關系面臨再平衡。德法兩國是歐盟的核心力量,也是歐洲一體化的啟動和推動者,雙方力量長期維持一種微妙的平衡。德國很大程度上愿意讓法國在政治上發揮主導性作用,也愿意在經濟上作出適當讓步,比如通過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向法國農業提供補貼;法國的政治大國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經濟上相對于德國的弱勢。即使在兩德統一后,德國雖然絕對實力增長,但由于吸收東部花費了大量資金和精力,經濟表現甚至一度不如法國,兩國力量對比并未發生明顯改變。但自2008年以來,主權債務危機徹底改變了德法兩國的力量對比。隨著兩國經濟實力差距拉大,雙方彼此猜疑開始潛滋暗長。德國對法國在結構性改革等問題上的拖延心有不滿,認為法國政府通過借錢維持龐大開支的做法無法持續,遲早會像希臘、西班牙一樣受到市場懲罰,擔心法國會拖累整個歐元區經濟。對于法國提出的發行歐元區統一債券、加快建立銀行聯盟等主張,德國懷疑是為了讓德國出更多的錢,為法國大手大腳花錢買單。①Gideon Rachman,“Welcome to Berlin,Europe’s new capital”,Financial Times,October 22,2012.而對法國來說,身為歐洲大國很難接受兩國地位出現不平等的事實。新總統奧朗德上臺后,想扭轉不利局面,提出“不要緊縮要增長”的口號,試圖與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國家聯合起來平衡德國的影響力,但這種做法反而導致兩國嫌隙增大,雙方在歐元區經濟治理改革、歐盟發展方向等問題上的矛盾和分歧凸顯。比如,法國向來在主權問題上較為敏感,對于德國提出的加強對歐元區國家預算監管的主張,有較強抵觸情緒。法國希望歐元區能盡快落實一些反危機措施,包括歐洲央行明確承諾充當“最后貸款人”角色、發行歐元區債券、建立銀行業聯盟等,但德國的反對態度導致這些措施遲遲得不到落實,法國的不滿增加。總體看,德國目前還沒有做好扮演歐盟領導者角色的心理準備,對如何正確運用本國新增的實力和影響力還沒有清晰的思路,也不明確應該如何調整處于變化中的德法關系。同樣,法國仍遠不能適應淪為德國小伙伴的現實。兩國要在相互猜疑中彼此適應,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在德法確立“新型伙伴關系”之前,兩國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的合作質量將大打折扣。
其次,英國與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矛盾加深,可能加快其“脫歐化”進程。隨著債務危機的升級和蔓延,歐元區的應對措施也在朝著更加一體化的方向發展。但英國卻將危機視為它調整與歐盟關系的機會和談判籌碼,試圖從歐盟獲得更多的例外權,甚至收回已經讓渡給歐盟的某些主權。換言之,英國想在某些領域擺脫歐盟“單干”。在2011年12月9日的歐盟峰會上,針對德國提出的修改歐盟條約、加強對成員國預算監管等主張,英國首相卡梅倫卻要求增加保護倫敦金融城利益的條款。由于英國擁有一票否決權,峰會最終只達成了26個成員國簽署的政府間協議,而不是全體一致通過的新歐盟條約。英國這種相當于“要挾”的做法引起了歐元區國家普遍不滿。在歐盟2014-2020年度中期預算談判中,英國的立場也格外強硬。卡梅倫放言,英國將不惜代價捍衛自己的利益。①James Kirkup,“David Cameron suffers stinging defeat over EU budget”,http://www.telegraph.co.uk/news/politics/9647205/David-Cameron-suffers-stinging-defeat-over-EU-budget.html.(上網時間:2012年12月5日)法國對英國一向游離于歐洲大陸、只注重英美特殊關系和英聯邦的做法早就心存不滿。20世紀60年代,法國戴高樂總統曾兩次否決英國加入歐共體的申請。英國入盟后,兩國矛盾并未減少,英國對法國力推的一些政策,如強化歐盟共同防務、農業保護、反傾銷政策等,始終持反對態度。因此,英國若要離開歐盟,法國不會特別在意。法國甚至刻意推動舉行沒有英國參加的歐元區例行首腦會議,借此進一步排擠英國。2012年5月,剛當選法國總統的奧朗德譴責英國政府“只關心倫敦金融城的利益,對歐元區的命運漠不關心”。②Tim Shipman, “New French PresidentHollandeattacks Britain's‘obsession with protecting the City of London’”,May 8,2012,http://www.thisismoney.co.uk/money/news/article-2141186/Hollande-attacks-Britains-obsession-protecting-City.html.(上網時間:2012年12月5日)英國的傳統盟友芬蘭、德國等北歐國家對英國的不滿也在增多,并開始認真考慮撇開英國推進歐洲一體化。芬蘭歐洲事務部部長斯塔鉑近期表示,英國自愿將其置于歐盟邊緣,正在遠離歐盟。③Honor Mahony,“Hague makes case for minimalist EU”,October 23,2012.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德國對英國的態度正發生重要變化,德政界一些精英甚至認為英國應盡早與歐盟做個了斷。④George Parker and Quentin Pee,l“UK and Germany:Exasperated allies”,Financial Times,November 6,2012.英國曾是德國平衡法國權勢的有力盟友,但隨著法國地位的相對衰弱和德國地位的走強,英國對于德國的可利用價值不再那么明顯,如果現在讓德國在歐元區/歐盟與英國二者之間做出選擇,德國肯定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德英在2011年底歐盟峰會上的針鋒相對就是很好的例證,德國總理默克爾針對英國要求保護倫敦金融城利益的態度明確表示,“無論哪個國家、哪個金融中心、哪種金融產品都將受到監管”。⑤Marco Evers,“Britain's Mounting Distrust of Germany”,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resentments-reawakenbritain-s-mounting-distrust-of-germany-a-804616.html.(上網時間:2012年12月5日)有跡象表明,由于英國在歐盟2014-2020年度中期預算談判中立場僵硬,其他26個成員國開始考慮撇開英國達成協議的可能性,⑥Editorial,“A high-stakes battle in Brussels”,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9,2012.而英國也似乎樂得如此。英國工作與養老金大臣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2012年11月初公開表示,英國在歐盟之外可以過得更好,并稱“英國公眾與執政黨對歐洲問題的態度都已發生了重大轉變”。⑦Kiran Stacey,“UK can thrive outside EU,says minister”,Financial Times,November 4,2012.近期一項民調顯示,超過一半的英國人支持英國脫離歐盟。⑧Gideon Rachman,“Europe would lose if Britain left the union”,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9,2012.
第三,歐盟傳統民主制度受沖擊,合法性降低。歐盟是一個由27個大小不同、貧富不均的國家組成的聯合體,多年來,歐盟一直在盡力維持成員國之間的平衡,以確保小國有足夠的安全感,相對貧弱的國家有足夠的發言權和自尊。但債務危機使歐盟一向標榜的平等、民主以及合法性不斷受到侵蝕。一方面,歐盟的“民主原則”不再普遍適用,“不民主”現象頻現。比如,在歐盟內,德國等大國和富裕的北歐債權國成為當前危機管理的主導者,而窮國和債務國成了被管理者;希臘、葡萄牙等國政府被迫實施緊縮政策,并受到“三駕馬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中央銀行和歐盟委員會)的監督,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財政和預算自主權;塞浦路斯的財政主權更是基本被“三駕馬車”所控制。⑨Christian Reiermann and Markus Dettmer,“Cyprus Makes Big Concessions for Bailout”,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cyprus-makes-big-concessions-for-bailout-a-871938.html.(上網時間:2012年12月11日)又如,在外部壓力下,希臘和意大利的民選政府被非民選的、受債權國和歐盟歡迎的“技術政府”所替換。這些“不民主”現象有違于西方傳統的民主原則。另一方面,歐盟“政府間合作”的趨強弱化了歐盟作為整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債務危機以來,歐元區及歐盟的決策更多通過政府間峰會做出,這種政府間決策的主要特征是,各國在利益妥協中達成最低程度的一致和共識,且處于強勢地位的國家利益和主張更受到重視和尊重。政府間決策往往不符合弱小成員國的利益,甚至也不符合歐盟的整體利益。這種現象長期存在必會挫傷弱小成員國的歐洲認同感,損害歐盟團結和信譽。除此之外,歐盟“民主赤字”問題可能越來越突出。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深入,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等超國家機構的權力也在不斷擴大,前者的行政行為和后者的立法行為已開始對成員國民眾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于是“民主赤字”問題出現了:作為歐盟“政府”的歐盟委員會究竟對誰負責?歐洲議會代表的是成員國還是民眾?事實上,歐洲民眾對于歐洲事務感到越來越疏遠。為應對債務危機,成員國正準備賦予歐盟委員會更多權力,包括對成員國預算的監管。根據歐盟新近通過的“財政契約”第16條規定,5年內該契約將納入歐盟法律框架,屆時,歐盟委員會的決策參與權將進一步擴大,歐盟的“民主赤字”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
三
歐盟力量格局的變化不是一種突發現象,而是成員國實力差距逐年拉大以及歐元區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主權債務危機只起到了催化劑作用。因此,歐盟力量格局的變化將成為一種長期趨勢,它給歐洲一體化帶來的影響也將是長期的。在這一背景下,討論歐洲一體化的未來走向,需要考慮各種變量,包括德法等國的政策選擇,歐元區危機的發展程度以及英國與大陸歐洲國家的互動效果等等。
綜合而言,從中短期來看,歐洲一體化將大體維持現狀,并可能會有小幅進展。理由主要有三。其一,德法作為歐盟發動機雖然功效減弱,但仍起到帶動作用。德法兩國對歐洲一體化進程賦予了極高的政治含義,歐洲聯合是兩國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這一點,歐洲之外的國家甚至像英國這樣的歐洲國家往往估計不夠。德法之間雖然存在較強的競爭性,但合作仍是主要方面,特別是在歐洲事務方面。應該注意到,德國并沒有像有些分析家所言追求“德國的歐洲”,而是試圖在堅持原則的同時注意妥協,維護歐盟的完整性。德國默許歐洲央行干預成員國債券市場、實施變相量化寬松政策說明,德國的立場有所松動,正在向法國和南歐國家的訴求靠攏。德國還響應法國總統奧朗德的呼吁,同意簽署了“增長條約”。①Carsten Volkery,“The Empty Promise of Europe's‘Growth Pact’”,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the-eu-snew-growth-pact-a-841243.html.(上網時間:2012年 12月5日)法國雖然嘴上對德國強調緊縮表示不滿,但行動上已采取措施削減財政赤字。這些都表明,為維護歐洲一體化事業,德法兩國相互妥協、尋求合作的意愿較強。
其二,英國在三五年內還不大可能脫離歐盟,因為它還沒有做好離開的準備。英國商品及服務貿易出口額的一半在歐盟統一大市場完成;②Departmen for Business Innovations and Skills,“The UK and the single market”, http://www.bis.gov.uk/feeds/~ /media/568CC723188C40DFBB02E868353B40B9.ashx,p.2.(上網時間:2012年12月5日)依托歐盟共同外交及共同貿易政策,英國能在全球發揮重要影響力;美國需要作為歐盟一員的英國來實現對歐盟決策施加影響。英國首相卡梅倫雖然近年對歐態度強硬,但聲稱無意在“脫離歐盟”與“留在歐盟”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歐盟國家特別是德國目前也沒有下決心要拋棄英國。因此,英國與歐洲大陸國家間存在著妥協空間。
其三,持續的債務危機壓力將迫使歐盟特別是歐元區國家不斷采取行動,即所謂“倒逼效應”。目前,歐盟正就歐元區銀行業設立單一監管機制問題進行談判,按歐盟計劃,2012年底前應就此出臺法律框架性文件,2013年監管機制開始運作,這將是歐盟邁向銀行業聯盟的重要一步。市場壓力在客觀上推動著歐洲一體化小步前行。此外,歐盟成員國關系,特別是北方債權國與南方債務國之間關系雖然趨于緊張,但并未達到對立程度,雙方妥協的意愿和空間都還存在。最近,歐盟相繼放寬了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希臘的赤字達標期限。德國的態度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也變得較為緩和,德政界很少再談論“希臘退出”問題,總理默克爾還在10月份和11月份先后出訪希臘和葡萄牙兩個重債國,以表達對它們愿意改革和繼續留在歐元區的歡迎態度。
從長期看,歐元區“一統歐盟”的步伐可能加快,尤其在經濟與貨幣領域,歐洲一體化可能由“雙速”重回“單速”。目前,歐元區已度過最艱難時段,解體的可能性基本排除,向好的趨勢開始增多。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重災國的結構改革正在深化,且已初見成效。一份最新研究報告顯示,自2010年以來,希臘單位勞動成本下降了15%;從2008年到2011年,希臘經常賬戶赤字減少了54%;同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經常賬戶赤字也分別下降了50%和40%;意大利2012年上半年貿易赤字接近零。這些數字表明,南歐國家的經濟競爭力有了較明顯提升,2013年后經濟有望恢復增長。①“Hope in the Euro Zone”,August 29,2012,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german-report-crisis-hit-countries-have-become-more-competitive-a-852813.html.(上網時間:2012年12月5日)與此同時,歐元區的機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進展,如實現了歐元區首腦會議的機制化,設立了永久性救助機制“歐洲穩定機制”,簽署了“財政契約”,創設了歐元區銀行業單一監管機制,等等。隨著經濟恢復增長、機制不斷完善,未來歐元區將對非歐元區國家更具吸引力。目前,歐盟有10個非歐元區國家,7個是中東歐國家,另3個是英國、丹麥和瑞典。按照歐盟法律,除英國和丹麥已獲得明確的例外權外,其他國家有義務加入歐元區。這些國家現在還在觀望,等待歐元區情況轉好。雖然它們還未交出貨幣主權,但絕大多數國家已開始加入歐元區的某些機制,如“財政契約”,并參加了歐元區關于建立銀行業聯盟的談判。未來,歐元區外的國家會越來越少,最終可能只剩下英國等極少數國家。問題最大的是英國。英國加入歐元區的可能性很小,當它有朝一日淪為真正意義的歐盟“邊緣國”、無緣全權參與歐盟決策的時候,作為一個曾經“驕傲的”大國,是“走”還是“留”?這對英國和歐盟都是一個重大挑戰。
應當指出,歐元區的擴張甚至“一統歐盟”并不意味著歐洲一體化使命的完成,歐盟的財政聯盟和政治聯盟仍將遙遙無期。一方面,作為一體化“機車頭”的德法兩國很難在短期內調適好彼此的關系,它們在歐洲一體化的遠景目標上差異較大。德國想推動歐盟“聯邦化”。默克爾總理2012年11月7日在歐洲議會的演講中提出,未來歐盟最終將聯邦化,歐盟委員會演變為歐盟政府,歐盟理事會演變為上議院,歐洲議會作為下議院也將獲得更大的權力。②Valentina Pop,“EU to be federalised in the long run,Merkel says”,EUobserver,November 7,2012.法國向來對“聯邦歐洲”缺乏興趣,執政的社會黨內更是存在強烈的反聯邦化情緒。2005年法國就歐盟憲法條約舉行公投,社會黨陷入分裂,最終導致公投失敗。當前,在自身處于弱勢的情況下,法國更不大可能接受德國主導的歐洲秩序。另一方面,“民主赤字”擴大將弱化民眾對歐盟的支持,他們的反對態度將通過各成員國議會或公投的形式表現出來,并對一體化進程構成障礙。事實上,隨著歐盟治理債務危機進程的深化,歐洲民眾尋求本國保護的情緒越來越強烈,歐洲民族主義思潮上升就是很好的證明。此外,要建立真正的財政聯盟、政治聯盟,成員國就必須修改歐盟條約,制訂新的歐盟憲章,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鑒于歐盟內部南方與北方之間、小國與大國之間、窮國與富國之間在利益訴求上分歧與矛盾長期存在,修憲談判將曠日持久。這方面歐盟已有前車之鑒。歐盟從2001年起開始“制憲”,2005年法國和荷蘭先后在全民公決中否決歐盟憲法條約,直到2009年簡化版的歐盟憲法條約即《里斯本條約》才得以生效,歷經8年時間。建立真正的財政和政治聯盟意味著向歐盟讓渡更多的主權,屆時包括從未就歐盟條約舉行過公投的德國在內的大多數歐盟國家都將就此舉行公投,③Florian Gathmann and Philipp Wittrock,“Germany Considers Holding EU Referendum”,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germany-considers-holding-eu-referendum-a-849441.html.(上網時間:2012年12月5日)鑒于當前形勢及歐盟的演變趨勢,新條約幾乎沒有通過的可能。
綜而言之,歐洲一體化中短期內將繼續維持“雙速”發展,長期看,隨著歐元區發展加速,最終兩種速度可能合二為一,歐洲一體化重回“單速”狀態。但即使到那時,歐洲一體化仍將無法明確最終目標。歐盟能否演變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合眾國”?沒有確定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