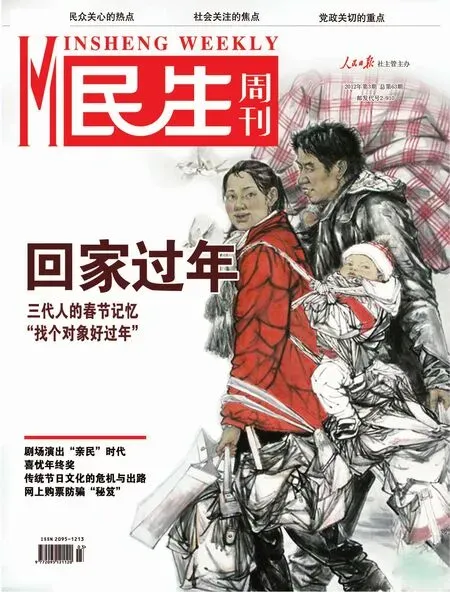中國成功的代價是收入差距擴大
□ 林毅夫
中國成功的代價是收入差距擴大
□ 林毅夫
在 18世紀前的1000年,中國創造了先進和燦爛的文明,但卻在之后的150年淪落為非常貧困的國家。如今,在1979年實行市場經濟轉型后,中國再次崛起,成為世界最有活力的經濟體。是什么推動了這些重大的改變?
在我的近著《解密中國經濟》(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中,我指出,不論哪個國家、哪個時代,持續增長的基石都是技術創新。在工業革命前,工匠和農民是創新的主要源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擁有最多的工匠和農民。因此,在其歷史上的多數時候,都是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領導者。
工業革命通過以由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實驗室進行的可控制實驗取代了基于經驗的技術革命,加速了西方國家發展的步伐。這一“范式轉移”(paradigm shift)標志著現代經濟增長的到來,也造成了全球經濟的“大分化”(Great Divergence)。
中國沒有出現類似的變遷,科舉制度是主要原因。這個制度強調對儒家經典的記憶,精英階層因此缺乏學習數學和科學知識的誘因。
大分化也帶來了希望: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轉移,實現比工業革命先驅更快的經濟增長。但中國一直沒能利用這一后發優勢,直到它認真開始改變其計劃經濟體制。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和其他政治領導人希望盡快扭轉中國落后的局面,采取了大躍進的政策,試圖建立先進的資本密集型工業。這一戰略讓中國能夠在20世紀60年代試爆核彈,并在70年代發射衛星。
但中國仍然是個貧困的農業經濟;在資本密集型工業上不占有比較優勢。這些領域的企業沒有在開放的競爭性市場中生存的能力。它們的生存需要靠政府提供保護、補貼和行政指導。這些措施幫助中國建立了現代和先進的工業,但資源卻分配不當,激勵也被扭曲。經濟表現很差,正所謂欲速則不達。
當中國的市場轉型于1979年開始時,鄧小平采取了實用的雙軌制政策,而不是“華盛頓共識”(W ashingtonConsensus)所提出的快速私有化和貿易自由化公式。一方面,政府繼續對重點領域提供暫時性的保護;另一方面,政府也向私人企業和外國直接投資開放勞動密集型領域——這是中國具有比較優勢但過去一直被抑制的領域。
這一政策讓中國得以同時實現穩定和快速增長。事實上,后發優勢是驚人的:在過去32年給中國帶來了9.9%的年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和16.3%的年均貿易增長。這是了不起的成就,足以作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寶貴的學習經驗。如今,中國已是世界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6億人口脫離了貧窮。
但中國的成功并不是沒有代價的。收入差距擴大了,部分原因是不少領域的扭曲性政策一直沒有取消——包括四大國有銀行的主導地位、接近于零的采礦權費用、主要產業(包括通訊、電力和金融服務)的壟斷等。因為這些扭曲(雙軌制遺留下來的問題)造成了收入不平等,它們最終抑制了國內消費和導致中國的貿易失衡。失衡會一直存在,直到中國完成其市場轉型。
我有信心,盡管面對歐元區危機和世界需求萎縮的逆風,中國能夠繼續其強有力的增長。中國2008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以購買力平價衡量),與日本在1951年、韓國在1977年、及臺灣在1975年的水平相當。日本1951-1971年的年均GDP增長是9.2%,韓國1977-1997年的年均GDP增長為7.6%,臺灣1975-1995年的年均GDP增長則是8.3%。考慮到這些經濟體的類似經驗和中國1979年以來的發展戰略,中國很有可能在未來20年里保持8%的增長速度。
一些人也許會認為,有13億人口的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其表現是不可復制的。我不贊同這看法。只要能夠善用后發優勢,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并提升國內企業,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可以有持續幾十年的快速增長,同時大幅減少貧困的類似機會。簡單地說,沒有什么可以替代對比較優勢的理解。
(原載于中國新聞周刊網,2012年1月6日)
□ 編輯 劉文婷 □ 美編 王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