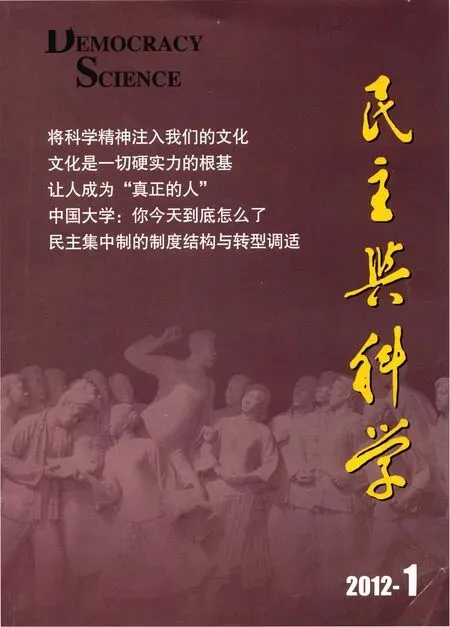科學:一條通向自由的隱秘之路
■李 俠
科學:一條通向自由的隱秘之路
■李 俠
短短三十余年的改革,經濟上去了,文化衰落了,這是一個很違反常規的奇異現象。這期間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以見證者的身份,我們目睹了與經濟起飛同樣震撼的整個社會大范圍失范現象的蔓延,痛定思痛,舉國上下都意識到了文化建設的重要性。但是,文化建設要比經濟建設困難得多,也緩慢得多,對此,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由經濟強國到文化強國的道路還很漫長,遠不是搞幾次大的文化戰役可以解決的。當下我們遭遇到的文化認同危機與疏離感開始逐漸從隱性轉變為顯性,在經濟上,我國已名列世界第二,可謂是一片繁榮,但在文化上卻出現了大范圍的荒蕪與貧瘠跡象,文化,作為社會黏合劑已經開始失靈,時時涌現的撕裂感正在威脅著社會秩序的有序運行,此時此刻,尋找重建文化的合適切入點就是當務之急。
當下的中國,由于整個社會公平維度的過早失落與沉沒,導致利益分配格局的長期扭曲,造成社會群體分層與流動呈現出非競爭性的特點,中國的群體心理呈現為高度的異質性。究其原因,拋開主流意識形態與傳統文化因素的掣肘外,至少還存在三種影響越來越明顯的文化思潮:犬儒主義、頹廢主義與虛無主義,這些群體思潮展現出的高度異質性,使群體很難形成一個有普遍共識的價值體系,這種狀況引發的后果就是在社會多個層面出現斷裂。從這個意義上講,重建文化共識是修補社會斷裂的一項基礎性工作。縱觀當下中國的各文化要素,只有科學文化才具有這種高度共識,因此,從科學文化入手,才是重建文化的最佳切入點。
科學文化與中國文化在內在結構上的契合性
科學作為舶來品,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扎下根來,其原因無非兩點,其一,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的現代科技給當代社會帶來了實實在在的進步,每個人都在獲得了科技進步帶來的額外收益的前提下,由功利主義價值觀導引開始信奉科學,這是一種信念投資。這種轉變從最可見的層面為科學的傳播做了一個有形的廣告;其次,科學作為一種嶄新的文化,它在結構上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某種程度上的契合與同構。基于對科學知識從功能角度的考察,我們可以把西方對科學知識功能演化的路徑梳理出一條完整的認知鏈條:知識、美德、幸福、力量再到權力。從獲得知識開始,這個鏈條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知識、美德到幸福的環節,這是古希臘從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延續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功能觀。它揭示出我們獲得知識所具有的功能性作用。具體來說就是,一個人擁有了知識也就同時擁有了美德,而美德對于幸福來說是充分的。這個階段對應著人類發展的童年階段,當把知識與美德、幸福這樣一些人生目標結合起來的時候,它提供的指向作用非常明確,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人類歷經千年的曲折歷史卻一直沒有把對于知識的熱愛拋棄。第二個階段,即力量到權力階段。自17世紀以降,隨著宗教改革運動的完成,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快速興起,一個新的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這個時代的代言人非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莫屬,而培根最著名的一句名言就是:知識就是力量。把知識與力量直接掛起鉤來,培根以他敏銳的洞察力看到了未來世紀發展的動力之源。在一個勃興的時代,這句箴言,也在向所有近代人布道:知識是讓我們獲得解放的一種力量。這個觀念一直延續至今,隨著19世紀末社會分工與專業化的充分發展,到20世紀70年代,人們再一次感覺到知識的功能又悄然地發生了改變,沒有人可以躲得過去。為此,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另辟蹊徑,他在對規訓與懲罰的技術變革的研究中,石破天驚地指出:知識就是權力。換句話說,擁有了知識不但提升了自己的力量感,更為重要的是,擁有了知識,也就同時獲得了相應的權力。眾所周知,在社會生活中,權力是生產性的,它時刻再生產權力自身。通俗地講,表面看來,權力的實現主要通過支配與控制來完成,而知識恰恰提供了支配與控制的技術基礎。所以,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曾說,在一個脫域的社會(主體可以不在場的社會),維持社會秩序有序運行需要兩套系統:象征標志與專家系統。這兩類系統之所以能夠存在與運行,是因為其背后隱含的知識與權力二重性的辯證法在起作用。然而,這里卻出現一個悖論:隨著高度分工與專業化社會的來臨,表面看起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疏遠了,其實,恰恰相反,今天社會里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聯系都要緊密:我們一刻也離不開別人的工作,從衣食住行的所有方面都離不開象征標志提供的質量保證與責任背書,也離不開那些未曾謀面的專家系統里的各類專家提供的服務,相應地,這些機構與專家也就具有了無可替代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社會是一個依靠信任機制來運轉的社會,由于其中諸多環節之間的縱橫交錯以及無法切割的特性,導致我們今天所生活的社會也被稱作風險社會。為了防范可能出現的風險,我們需要多元化的監督體系來監督由知識帶來的各類權力的衍生品,以此捍衛脆弱的信任機制。
科學之所以能在中國獲得了廣泛的認同,是因為它與中國文化的內在功能結構相匹配。以當下國情為出發點,這種選擇能以極小的阻力推動科學文化發展,并能快速展現文化變革的成效。從功能結構上說,中國儒家文化講究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禮記.大學》)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個功能結構的八要素中,前六項是指知識對于個人內在修養的鍛煉,這與西方對于知識功能界定的第一個階段幾乎完全一樣。中國文化中的治平功能與西方知識功能結構中的第二階段有些差異,這反映出我們對于知識的體認仍然是粗線條的,而西方對于知識作用的揭示則要精細得多。畢竟治平理想只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其運作的內在機制并不明確;相反,西方自近代以來把知識等同于力量與權力,則更好地體現了知識向外擴展的具體機制與路徑。正是因為中西對于以科學為代表的知識體系在內在功能結構上的高度趨同,才促成了外來的科學在中國扎根與站穩腳跟的過程并不很曲折,這也是在中國推動科學文化建設帶動文化復興的有利條件。
科學文化:手段、目的與個體的內在自由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的,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但自由也是有邊界的,正如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然而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對于自由可以有很多分類,比如英國哲學家以賽亞·柏林從主體能動性的角度給出所謂的“積極的自由”與“消極的自由”的分別,其要義在于消極自由是“免于……的自由”,而積極自由則是“去做……的自由”。因此,那些浪漫的并顯得有些華麗的所謂積極自由,其實往往是不自由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而已。如果我們把自由按照行動范圍來分,那么自由可以分為兩種:外在自由與內在自由。外在自由的實現需要一個民主機制來保證。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高度集權下的封建等級制,以此來劃定社會秩序;而民主機制則要求分權背景下的公平、平等原則,這種本質性的差異決定了外在自由在當下的中國實行起來比較困難;而內在自由的實現相對來說約束條件比較少,只要你具有一個健全的理智與自由意志即可。從事科學恰恰是個體通過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實現的通向內在自由的一條阻力較小的隱秘路徑。既然如此,為何科學精神在中國還如此孱弱呢?從理論上講,當外在自由實現的阻力比較大的時候,群體轉向內在自由的熱情會比較高漲,這實在是一件很詭異的事情。在筆者看來,造成中國人科學精神孱弱的原因在于傳統文化又一次以黑暗之子的方式改變了科學精神的發展路徑,這主要反映在對于科學的認知模式的誤構上,回到中國語境就是,對科學的定位根據庸俗實用主義的理念改變其自然的發展路徑,在實踐層面就是手段與目的的倒置。換言之,科學,對于中國人來講其第一要義是一種手段還是一種目的?這個問題決定了中國人的科學精神孱弱的深層原因。
筆者以前曾撰文指出,以科學作為職業的三種境界,即生計、事業與志業。秉持前兩種境界的從業者大多把科學作為謀生與換得世俗目的的一種手段,包括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學而優則仕”也是這種類型。一旦科學淪落為片面的謀生手段,科學精神將不復存在,從業者僅僅是科學的奴仆。如果將科學定位為一種神圣的高貴志業,它所追求的目標將不再局限于世俗目標,而是響應內在召喚的探索真理行為,那么,在尋找真理的過程中,科學精神將源源不斷地溢出,這個時候個體將會發現那個久違了的內在自由。其實這里有一個問題,很多人還沒有搞明白,即真理與個人存在的關系問題。換言之,我們為何追求真理?如果追求真理不能給我們一種可以感知的回報(有形的或無形的),那么把科學定位為追求真理不是很愚蠢嗎?坦率地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哲學問題,即真理與存在者的關系問題。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對此有很好的剖析,他的結論簡潔地說就是:真理的本質就是存在者的自由。獲得真理的過程,也就是存在者獲得自由的過程。尋找真理的過程是一個去蔽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它讓存在者從被遮蔽狀態中綻放出來,以此獲得內心的愉悅。從這個意義上說,真理對于個體的幸福也是充分的。
既然在探索科學秘密的征途上所呈現出的真理、自由、公平等具有普世性的價值要素是所有人都渴望的,為何在相同的需求背景下會出現如此大的后果差異:西方具有比較濃厚的科學精神氣質,而中國的科學精神氣質一直比較孱弱呢?這也是思想史上比較有趣的話題,它的表層顯現就是早些年議論很多的所謂的“李約瑟難題”。筆者認為,這里涉及到文化傳統問題,西方自16世紀以來完成了宗教改革,新教確立,資本主義萌生,由此逐步確立了科學不可動搖的地位。按照清教主義的基本宗旨:上帝是通過自然向我們傳道。換言之,通過科學研究揭示自然的奧秘,這種行動是對上帝創世奇跡的真誠贊美,同時,也通過個體智力上的成就,彰顯上帝的榮耀。可以說從事科學是響應上帝的召喚。中國傳統文化的宗旨是實用主義的,這種實用主義觀念里缺少一種形而上的追求,因而超越感在中國文化中一直是一種虛擬的可疑擺設。久而久之,我們的文化形成一種認知定勢:從事科學就是為了獲得具體的用,所謂“經世致用”被奉為儒家的不二法則,在入世與出世的首鼠兩端中,科學精神被實用主義的剃刀定點清除了:凡是不能顯現的一概不值得追求,意義,在中國文化里總是缺少意義的,這是傳統文化短視的經典表征。
基于上述分析,中國文化建設的主要突破口應該定位于科學文化的建設。這種路徑選擇有三個好處:其一,在當下中國思想斷裂的年代,整個社會對于科學文化具有高度的認同感,推廣起來社會運行阻力最小,這是復興文化的基礎準備條件;其二,在推進科學文化的過程中,一些自啟蒙以降得到整個世界廣泛接受的基本價值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從而有利于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結構的改造與重建;其三,在倡導科學文化的過程中,個體通過內在自由的實現,緩解了社會在遭遇文化危機時的群體茫然無措現象,為文化從蕭條、重建再到復興預留出寶貴的建設時間。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